贺麟先生是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的老师。他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的学生陈修斋、张世英,为我们讲授西方哲学史和黑格尔哲学的课程。那时候,老教师们和学生接触不多。
我退休后,在为研究生讲“中西哲学比较”课程时,重读了贺先生的学术著作和他翻译的书。当《贺麟全集》陆续出版,有机会看到他的学生张祥龙写的“出版说明”,感慨良多。张祥龙说,他一直觉得,贺先生“对于现代中国哲学事业的贡献,还没有为学界充分认识和估计”。我深有同感。实际上,人们比较熟悉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而对作为现代中国重要的哲学家、翻译家、哲学史家的贺先生,虽知其作为翻译家的贡献,但对于他作为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成就,对于他的“新心学”,却知之不多,对于他的代表作《近代唯心论简释》甚至有所误读。
国学根底、留学经历和“新心学”代表作
贺先生于1902年11月3日生于四川金堂县五凤镇,从小得益于祖父和父亲在国学方面对他的教育。父亲教他读《朱子语类》和《传习录》等宋明理学的经典。小学、中学时,他又广泛涉猎各种新学书籍。1919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校后,受梁启超、吴宓的亲自指导,先后在《晨报》副刊和《东方杂志》上发表《戴东原研究指南》《论严复的翻译》等文章。
1926~1930年,他先后在美国奥柏林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及其研究院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史。伦理学教师耶顿夫人(Mrs.Yea⁃ton)对他影响极大,是他接触黑格尔、斯宾诺莎的开始。著名哲学家格林(T.H.Green)、怀特海(Whitehead)、鲁一士(J.Royce)等人的讲课和著作,对他从原来的新机械主义向新黑格尔主义的思想转型,起着引领作用。尤其是鲁一士融合东西哲学的特征,给他后来中西哲学融会贯通的研究方向的形成,以关键性的导向。 1930~1931年,他到德国柏林大学直接学习德国古典哲学,深刻认识到:要深入研究黑格尔哲学,非要先研究康德和斯宾诺莎不可。
留学期间,他接受了西方学术训练。德国古典哲学、英美新黑格尔主义和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是他融会贯通后逐步创立的“新心学”的思想养料。他的“新心学”有三本标志性的代表作:《近代唯心论简释》(1942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当代中国哲学》(1945年由胜利出版公司印行)和《文化与人生》(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近代唯心论简释》侧重哲学理论的创造与阐发,《文化与人生》侧重于哲学理论在文化与人生的应用,两书体用结合,形成姐妹篇。《当代中国哲学》是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文的基础上扩充、汇集而成,内容涉及中西哲学与时代思潮的演变,以及对知行问题的讨论与发挥。
《近代唯心论简释》的基本观点与主要内容
《近代唯心论简释》是贺先生的第一本论文集,共有论文15篇。首篇论文《近代唯心论简释》1934年3月发表在天津《大公报》的《现代思潮》周刊上。它的发表标志着“新心学”哲学思想的开始。有人称它为贺麟“哲学思想的宣言”,说“以后的许多文章都是此文所阐述的基本思想的扩充与引申”(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商务印书馆,2011,第369页。以下引用此书,只注书名及页数)。由于这篇论文提纲挈领地统领全书的其他论文,作者便以之作为书名。
该文开宗明义写道:“心有二义:(1)心理意义的心;(2)逻辑意义的心。逻辑的心即理,所谓‘心即理也’。心理的心是物,如心理经验中的感觉、幻想、梦呓、思虑、营为,以及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情皆是物,皆是可以用几何方法当作点线面积一样去研究的实物。”
贺先生认为,心与物是不可分的整体,但由于“唯心论”这个名词容易被误解,所以,贺先生认为,也可称唯心论为“唯性论”。这个“性(es⁃sence)”为物之精华,为理性所决定的自由意志,应付环境而产生的行为、所养成的人格,就是一个人的“性格”。唯心论又可以称为“理想论”或“理想主义”,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称谓:“就知识之起源与限度言,为唯心论;就认识之对象与自我发展的本则言,为唯性论;就行为之指针与归宿言,为理想主义。”贺先生上述关于“心”的界说,显然吸取了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关于理性的见解,把心与理性、理想融合起来了。
《时空与超时空》的上篇,发挥康德的时空观点,认为“时空是理”;下篇论超时空,认为道体超时空,体道之境界也超时空。关于“时空是理”的观点有力的支持了理性主义,并与《论意志自由》《论道德进化》两篇文连接起来。
《知行合一新论》曾在西南联大哲学讨论会上讲演过,编入《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是全书中“最关重要的一篇文字”。文章开始就指出,“知行合一与王阳明的名字,可以说是分不开的。”接着对“知”“行”和“合一”三个概念,分别作出透彻的解释,并用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衡论”和西方现代心理学来解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
《宋儒的思想方法》着重讨论了直觉方法,提出独特的见解。他说:“直觉是一种经验,复是一种方法。所谓直觉是一种经验,广义言之,生活的态度、精神的境界、神契的经验、灵感的启示、知识方面突然的当下的顿悟或触机,均包括在内。所谓直觉是一种方法,意思是谓直觉是一种帮助我们认识真理,把握实在的功能或技术。”(《近代唯心论简释》,第82页)直觉方法不同于抽象的理智方法,但绝不能认为它是无理性或反理性的。如果用直觉方法去分析朱熹和陆象山的思想方法,陆是“先理智的直觉”,“注重向内反省,回复本心”表现为反省式;朱是“后理智的直觉”,“注重向外体认物性,读书穷理”表现为透视式。两者殊途而同归(《近代唯心论简释》,第88页)。
《怎样研究逻辑》和《辩证法与辩证观》两篇文章对于深入理解他讲的逻辑之心与直觉方法紧密相关。作者指出,“辩证法自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辩证法既是方法,又“不是方法,而是一种直观”。真正作辩证法的思考是非常之难的,“这需要天才的慧眼、逻辑的严密和纯思辨的训练”(《近代唯心论简释》,第117页)。
《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虽然是讲中国的事情,但作者在“旧礼教核心的三纲说”中,发现了与西洋正宗的伦理思想与西洋近代精神相符合的地方。在《文化的体与用》中明确指出,“文化是道的显现”,“文化之体不仅是道,亦不仅是心,而乃是心与道的契合,意识与真理打成一片的精神”。
《近代唯心论简释》一书还收集了《斯宾诺莎的平生及其学说大旨》《康德名词的解释和学说的大旨》《西洋机械人生观最近之论战》《评赵懋华〈叔本华学派的伦理学〉》《与友人辩宋儒太极说之转变》等。全书涉及贺先生哲学思想中的本体论、辩证法、知识论、知行观、文化观。贺先生的“新心学”是用黑格尔的辩证观融合中与西、沟通理与心。这就不难理解,贺先生为什么既接着陆王心学,又对黑格尔客观唯心论哲学情有独钟。
《近代唯心论简释》出版后引起的评论
《近代唯心论简释》于1942年出版后,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学术界的评论。后来这些评论文章作为附录收入该书。
胡绳以《一个唯心论者的文化观——评贺麟先生著〈近代唯心论简释〉》为题,在1942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批评文章。胡文一开始就批评贺著是“直觉论的神秘主义”,断言:“这种(直觉)方法不能引导我们到真理,而只能引我们到混沌”;还批评贺著是“超历史的范畴”(《近代唯心论简释》,第316页)。
徐梵澄写的以《〈近代唯心论简释〉述评》为题的书评,于1942年发表于当时中央图书馆编印的《图书馆月报》上。指出贺著中有一二细微处不甚同意,但整个地看,“其努力求融会贯通中西哲学,显而易见。无论有没有偏颇的地方,却处处能见其大,得到平正通达的理解。”(《近代唯心论简释》,第321页)
谢幼伟是贺麟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同学,他写了《何谓唯心论?》的评论文章。该文肯定贺著是“今日中国哲学上不可多得之著作”,并提出三个问题。贺麟于1943年4月14日以书信形式对这三个问题作了回答。谢文说:“何谓唯心论?此为不易回答之问题。唯心论一辞,最为人所知,亦最为人误解。数十年来,国人之谈哲学者,于唯心论一辞,虽多提及,然为唯心论下一正确之解释者,则不多觏。若进而主张唯心论,为唯心论辩护,及根据唯心论之说以谈道德文化诸问题,则更绝无仅有。有之,吾惟于贺麟著《近代唯心论简释》一书见之。”(《近代唯心论简释》,第322页)
陈康曾在德国住了近10年,专攻希腊哲学。他与贺麟是在德国柏林大学时的同学。他看到贺麟1934年在天津《大公报》的《现代思溯》副刊上首次发表的《近代唯心论简释》的文章后,就写了评论文章,发表于1936年《文哲月刊》第6期。陈康指出,“‘唯心论’是个不幸的名词,因为如若中国人不丢弃那不研究内容专听口号的习惯,唯心论的哲学即因为它的标题为唯心论,已是遭人误解了。‘心即理也’中的‘心’也将和唯心论中的‘心’一样为人误解。”(《近代唯心论简释》,第342页)
从以上评论看来,徐梵澄、谢幼伟、陈康三位学者对贺先生的基本观点,对于贺先生在中西文化、哲学的交流、融合与会通,特别是试图沟通西方哲学与宋明理学方面的努力,是认同的。
坚持“唯心主义中有好东西”
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贺先生和他的学生陈修斋联名写了题为《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的文章,发表在《哲学研究》1956年第3期上。1957年1月22~26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贺先生在会上作了题为《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的系统发言。他认为,哲学史虽然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但这种斗争与“宗教上的斗争,政治上的斗争却有很大的区别”。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的关系,“有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关系,不是红与白的关系”。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既有“互相斗争的一面,也有互相吸收利用凭借的一面”,“唯物主义也有被较晚、较发展的唯心主义代替的时候,唯心主义也有被较晚的唯物主义代替的时候。”(《哲学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86~191页)
贺先生上述观点遭到了批评。贺先生针对批评作了反批评。1957年4月24日,贺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的文章(贺麟:《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人民日报》1957年4月24日)。5月10日~14日,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史教研室在北京大学临湖轩联合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上,贺先生又发言指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是学术上的论争。贺先生对优秀的文化遗产,包括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大师怀有深厚感情。他说:“我对好的唯心主义是有感情的,这是对优秀文化遗产有感情。”(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28页)之后,贺先生对哲学问题保持缄默,埋头于纯学术的研究,专门从事翻译和讲授西方哲学。
贺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将近30年,他的论文和论文集《近代唯心论简释》发表、出版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他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一个是关于中西哲学思想内容与思想方法的沟通与融合,以及“新心学”的创立;另一个是关于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哲学的翻译和阐发。他对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思想的精湛的研究和翻译,使“西人精神深处的宝藏”传入中国,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和创造性地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在哲学史的思想渊源的发掘与进一步的研究方面,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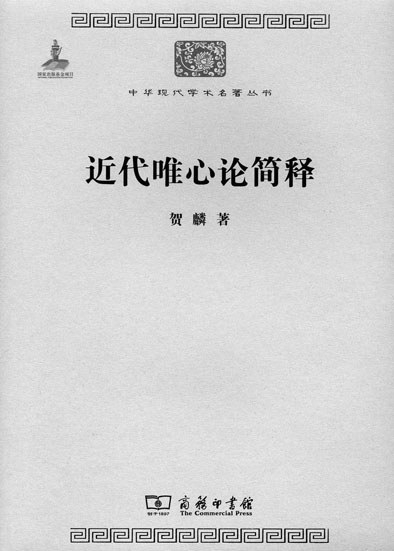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