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记忆,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天安门(也许是新华门)前,不知是秋还是冬,寒风萧萧,荒草离离,我只有两三岁,抱在保姆手上,跟着母亲从那里走过。忽然我哭着闹着要“何何”。那是指外祖父家的厨子何二,他会逗小孩子玩,我喜欢他,但是我话还说不清,就只会叫他“何何”。保姆大约说了不少解释的话,例如说“何何”不在这里,或者还说了不少推延的话,例如说回家去再找“何何”之类吧,仍然止不住我的哭闹,于是她一面抱着我走着,一面慢声帮我呼唤着:“何何,何何,快来哟!小毛毛要你哟!何何快来哟!”听了她这几声呼唤,我忽然感到一种彻骨的伤心,我忽然清醒地懂得了:“何何”是不会来的,保姆的呼唤是骗我的,我的哭闹是无用的。母亲和保姆大约高兴我停止了哭闹,她们哪里会知道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孩子,竟会有这样难以言说的彻骨的伤心呢!长大以后,曾经问过她们二位:那次是从哪里到哪里去?为什么会在寒风萧萧之中步行过天安门(也许是新华门)前?她们一点也记不得了。我却是终生难忘,至今不愿听安慰的话,也不会安慰别人,总觉得安慰里面多少含有欺骗的成分,这还不是指虚伪的安慰而言,倒是真诚的好心的安慰,往往反而欺骗得更残酷。
我的籍贯是安徽桐城,出生也在桐城,可是一岁时母亲就带我来到北京,住到七岁。我一直没有问清楚,所谓一岁,究竟是一周岁已满,还是未满。就算是满了周岁吧,桐城当然也不会给我留下任何最初的记忆。只听母亲说,我生后几个月,一场急性肺炎(当时谓之抽风),几乎断送了小生命。县里几位名医都请来了,都不肯开药方了。小棺材也买下了。最后请了一位医道声誉很不高的小周四先生来,“死马权当活马医”。不料他的一剂药灌下去,我立刻有了转机;再接着吃他的药,很快便痊愈了。母亲将我许给他做义子,以报救命之恩。他一时之间,声誉顿起,门前求医者日多。可是他的医道似乎毕竟不高明,医好我以后据说再也没有什么好成绩,他的门前不久又萧条下去了。有人说他是歪打正着,偶然碰巧。有人说我是命不该绝,必然有救。总之这是我生命史上第一个事件,可是完全得之于母亲的传述,我自己头脑里并无任何感性的影子。就连我的那位有救命之恩的义父小周四先生,我也至今不知他是什么样子。我七岁自北京回桐城以后,不知他是否已不在人间,反正没有人带我去拜见一次。
这样,我七岁以前的全部童年的回忆,就都是同北京相联系的了。那是北洋政府统治的末期(约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我的外祖父马通伯(其昶)先生以桐城派大师的身份,住在北京,头衔不少,有清史馆总纂、参政院参政等等。以他为中心,他的几个儿子几个女婿,也就是我的几个舅父几个姨父以及我的父亲,先后集中到北京,有的在机关学校有个中等职务,有的似乎只是闲住。还有我的两位伯父、三位姑丈这时也在北京。我的父亲从日本留学回来,任教于北京大学预科,在北京同我的母亲结婚。据说因为是新式婚礼,来宾中又有陈独秀、胡适这两个新派领袖人物,惹得外祖父不痛快,不肯参加婚礼,派了我的一位舅父即我母亲的弟弟,代作女方家长。我的父亲其实也并非新派人物,他和陈独秀、胡适只是私交的关系。在文言与白话的论争中,他是赞成白话而并不积极的。一九一七年他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的《读者论坛》中发表一篇《我之改良文学观》,一方面赞成“白话文学为将来文学正宗”,一方面又不赞成“今日即以白话为各种文学”,主张“姑缓其行”,主张今日只要“作极通俗易解之文字,不必全用俗字俗语”。郑振铎先生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编《文学论争集》,选了我父亲这篇论文,并在《导言》里举出它来作为“折中派的言论”的代表。就文论文似乎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是,《新青年》编者陈独秀在文后所加按语中并不是这样看,相反的,他说:白话文学的推行,要待有比较统一的国语,要有一部国语文典,要有许多著名人物用白话著书立说,必须先有这三个条件,所以“兹事匪易,本未可一蹴而几者”。可见他当时也并未主张“今日即以白话为各种文学”。原来当时陈独秀、胡适等先进人物,一面倡导白话,一面并没有下决心立即促其实现,后来是运动的客观进程反转来推动先进人物向前走。《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第二卷第六号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但是这两篇名文本身仍是文言文,以后《新青年》各期也仍然是以文言文为主,只偶尔有一点白话翻译的小说剧本,几首白话诗。直到第三卷第三号,才有读者来信建议“即白话论文亦当采用”。第三卷第五号发表了陈独秀的《近代西洋教育》,才第一次发表了白话的论文。至于《新青年》上以白话文章为主,则更在以后,大致是从第五卷起的。这样看来,发表在第三卷第二号上的我父亲那种主张,在当时又未必能算很典型的“折中派”了。(附带说一下,郑振铎先生在这篇《导言》里,不知怎么把我父亲的名字方孝岳错成方“宗”岳,而正文和目录此篇题下明明都署的方孝岳,并没有错。后来又有人说到我父亲的一部著作《中国文学批评》时,也把作者的名字错成了方“宗”岳,实在巧得很。)由于当时家族的重心是在北京,所以我母亲回桐城分娩,生了我,到我一岁时又带我到了北京。等到我七岁时,以外祖父为中心的几房人忽然同时离京,有的回桐城,有的到南方其他城市;其时我的父母已经分居,我母亲也就带着我结伴回乡了。那一阵纷纷离京,显然同蒋介石建立了南京政府,北洋政府统治的结束带来了北京政治地位的改变有密切关系。
上述背景当然都是长大以后逐渐了解到的。至于后来能够直接回忆的,实在都是极其零星,不成片段的。甚至在北京时的外祖父,记忆里也毫无印象,记得的只是他在桐城家中坐在书桌前的模样了。大概是我到他书桌前玩,看见桌上有一片玉制的藕片,表示出欲得之意,外祖父就把那片玉藕给了我,我也知道这是比较珍贵的东西,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说我们在北京不止住过一处,我有些记得的只是最后一处:府右街。一个晴朗的下午,一位长辈到我们府右街寓宅来,送我一个小皮球。我不会拍,他拍给我看,我看得着迷,觉得小皮球不是自己跳上来的,简直是拍球的人手上有什么吸力,吸着小皮球跟着手上来的。这是我关于府右街寓宅的第一个记忆。那穿窗斜照的晴午的阳光,那张比我高的吃饭用的方桌,不吃饭时靠墙放,一边一把椅子,那位长辈就坐在桌旁拍皮球的样子,至今都还历历在目;当时印象自然更加深刻,以致后来再看别人拍皮球,总觉得没有那位长辈拍得好。我自己学拍皮球,也总想学到那样好,不止一次认真地向人求教:“怎样才能叫皮球粘着手起来?”每次别人都说不知道,使我一再地失望。
府右街北口路西,有一所培根小学(五十年代还是这个名字,不知何年起改为府右街小学,迄至现在,校门的样子大致未改),我六岁至七岁——按周岁算就是五岁至六岁时,在那里读了小学一年级。语文第一课是:“狗,大狗,小狗,大狗叫,小狗跳……”每天下午放学,排好队,唱着歌回家,唱的是:“功课完毕太阳西,收拾书包回家去。见了父母行个礼,父母见我笑嘻嘻。”小小的队伍在府右街路西人行道上由北而南地行进,看着斜照在对面路东人行道那边的夕阳,还真能领略歌词里“功课完毕太阳西”那一句的那么一点欢快而稍有阑珊之感的意境。表兄马茂炯和我同班,每天同来同去。同班同学中至今我还记得两个名字:黄森林、王玉同,大约是比较要好的吧,模样却是完全忘掉了。级任是一位女教师,来我们家访问过,当时印象比在教室里看见她深,现在眼前还有一个朦胧的影子。
与府右街寓所、培根小学有关的回忆,就是这么两件,此外的更零碎了。有的背景是北京的不知什么街头,有民间艺人在玩木偶戏,当时我跟着大人叫它“扁担戏”。因为他是一个人用扁担挑着戏箱和“戏台”走街串巷,找好地点表演时,用扁担撑起小小的“戏台”,围以简陋的帷幕,人躲在里面,手举木偶露在帷幕的上沿,做出种种戏文,人在幕中替木偶说话,做音响效果。那时北京街头常能见到,我最爱看,每次遇着便不肯放过,怎么也舍不得走。我自幼不是贪玩的孩子,为什么这样酷爱“扁担戏”,母亲同别人谈起时常常奇怪。其实小孩子总会喜欢什么热闹,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我后来是个戏剧家,是个演员,这当然能说成我自幼就有这方面的兴趣的“萌芽”,可惜拉扯不上,到底无非是小孩子爱热闹罢了。
有的回忆的背景则是北海。从府右街到北海那么近,母亲总该带我去过不止一次吧,可是我后来有印象的只有一次。那是在小艇上,不记得哪几位大人带着我,也不记得是谁在划。将近五龙亭时,我这小艇上的大人和对面来的一个小艇招呼起来。我一看,那个艇上划桨的正是我最怕的人——姑丈邓仲纯先生。他是医生,给我打过一次什么注射针,大约很有些痛吧,从此我就把他当作最可怕的人。保姆也常常拿他要来给我打针威胁我做什么不愿做的事,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恐怖之感。我看见他以熟练的姿势优雅地划着双桨,笑嘻嘻地大声同我这边船上的大人搭话,不像会跳过来给我打针的样子,稍微安心一点,仍然紧张地盯住他的一举一动,听见他说他们是从五龙亭划过来的,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那五龙亭的名字。长大以后,逐渐知道,我这位姑丈清朝末年就到日本学医,回国后一直以医为业,是中国西医界的老前辈。当时他在北京的职务,我不知道。一九三四年他在青岛山东大学担任校医,郁达夫这年游青岛,作《青岛杂事诗十首》,其中第五、第六两首就是送给邓仲纯先生的。第五首云:“京尘回首十年余,尺五城南隔巷居。记否皖公由下别,故人张禄入关初。”自注云:“遇邓君仲纯,十年前北京邻舍也。安庆之难,蒙君事前告知,得脱。”《郁达夫诗词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编者按云:“一九二四年作者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与邓邻居。一九二九年秋,作者应安徽大学之聘,赴安庆任教。到校后不久,为当时安徽省教育厅长程天放所不容,被列入赤化分子名单,企图陷害,幸邓及时通知,得脱。”我还知道邓仲纯姑丈在安庆时冒着危险掩护过另一个重要的地下党工作者,可见他是同情革命人士的。我最后见他是一九三九年在四川江津。新中国成立初期,听说他在青岛一个市立医院当院长,约于一九五九年在青岛逝世,追悼会在北京嘉兴寺殡仪馆举行。我接获通知时有特别的感动,其时我已是“右派”,不复齿于人类,这个通知表明还有人以正常的亲戚之礼相待,于是我带着这一点“人的价值”的自我感觉,赶到嘉兴寺去向姑丈的遗像做了最后的敬礼。三鞠躬以后,转过身来,我暗吃一惊:怎么一个活生生的姑丈就站在我的身后?但马上冷静过来,知道这是姑丈的弟弟——前辈美学家邓叔存(以蛰)教授,虽然从未见过,但此时此地,长得和姑丈那么相像的人,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邓仲纯姑丈当时在北京与郁达夫“尺五城南隔巷居”的寓所,我肯定曾由大人带去过,但已经毫无印象了。另一位姑丈姚农卿先生当时的寓所,在西城辟才胡同四条,却成了我关于当时同在北京的亲戚寓所的仅有的记忆。其实也朦胧得很,只记得是一个大四合院,有抄手游廊,一次在他家正遇下雨,小孩子们绕着游廊跑来跑去,总淋不着雨,大家都高兴极了。至于“辟才胡同四条”这个地址之所以能记得如此清楚,则是后来的事。因为姚农卿姑丈家一直留在北京,辟才胡同四条的寓所比较宽敞,姑丈忠厚诚笃,姑母方孝姞在她兄妹中是受人尊敬的长姊,对于我这一辈更是德高望重的长姑母,家族中常有人到北京去,总住在辟才胡同四条,甚至有住上半年一年的,所以常常听到这个地址,十分耳熟,姚农卿姑丈清末留学英国学采矿,民国初年学成回国,前后七年,但在旧中国似乎很少有真正用其所学的机会。沦陷期间,姑丈仍留住北京,拒绝了各种引诱,不到敌伪机关学校任职,宁可开私塾口,再也住不起辟才胡同四条的房子,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到屯绢胡同拜谒,看见他们只住了两小间简陋的南房,萧条得很了。新中国成立后,姑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与姑母都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在“文革”中逝世。遗憾的是姑丈逝世时,我还在“牛棚”,行动没有自由,相距咫尺,竟未得参加丧礼。
话说回来,儿时关于北京的记忆,就是上面这么几个片段,除了培根小学的一段外,大概都是很小很小时候的,所以都只限于同小孩子的喜爱和害怕密切相关的。这些片段其实都很平凡,并没有什么特别美好特别幸福的。可是,它们就紧紧地系住我的心,使我总是特别关心一切有关北京的事。长大以后,更是不断从鲁迅的一切北京时期的和以北京为背景为题材的作品中,从鲁迅北京时期的师友的回忆中,从周作人一切与北京有关的作品中,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从俞平伯的《陶然亭的雪》中,从“五四”时期一切住公寓的青年写出来的和描写住公寓的青年的作品中,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直到齐同的《新生代》和杨沫的《青春之歌》中,从老舍的几乎全部的小说中,从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的《汉园集》和林庚的《北京情歌》中,又追溯上去,从《孽海花》《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书关于北京官场、名士、妓院的描写中,从徐凌霄、徐一士、瞿兑之等所谈的北京掌故中,从各种有关北京历史风土的考证、笔记、竹枝词中,从张之洞、盛昱、宝廷的诗篇中,乃至从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之类的著作中,从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之类的小说中……总之从一切可能的途径,也包括抗战期间听一些从北京逃难到四川的朋友闲话北京的途径,最广泛地搜集和积累一切有关北京的知识。从七岁离开北京,到一九五三年移家北京,中间虽然隔了二十多年,可是这样积累起来的知识,不妨说简直可以填补这二十多年的空白,我觉得对北京熟悉极了。借用术语来说,大概就是把大量的“信息”附着在我心目中的北京之上了。
从一九五三年移家北京,至今已三十年。近几年,有些外省友人劝我设法调到外省去工作,保证可以改善我的宿舍条件。我感谢他们的好意,相信他们的保证,但是举出种种理由谢绝了,例如说北京有哪些优点,而且宿舍不久也可以调整,等等。其实,这理由,那理由,都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只是一句话:北京是我“歌于斯,哭于斯”的地方,于我有故乡的情分,我不想离开它罢了。
(本文写于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九日,摘自《家学杂忆》,舒芜/著 方竹/编,北京出版社2020年3月第一版,定价: 48.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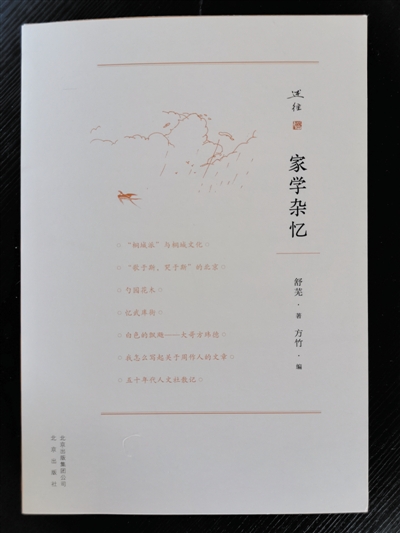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