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戏剧家到侦探小说家
瑞士著名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1921—1990)凭借《老妇还乡》《物理学家》和《流星》等戏剧作品享誉世界。其怪诞的表现手段、对现实社会的“表演”以及认识论方面的哲学探究,构成了迪氏喜剧独树一帜的风格。除戏剧作品之外,迪伦马特还一再涉足通俗文学中最受欢迎的类型——侦探小说,并因此收获极高知名度。侦探小说这一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大放异彩的特殊题材及其“变动不居的色调”,令迪伦马特的影响力不仅超出德语文学范围,更在犯罪研究和公安文学领域引起超越国别的关注和喜爱。与此同时,他的侦探小说因独特的叙事手法,看似迂回又绝非简单重复的主题呈现,出人意表又令人折服的结局,展现出高于传统侦探题材本身的文学水准和思想底蕴。
迪伦马特的侦探小说写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略迟于他的戏剧创作。1950—1951年,瑞士《观察家报》(DerBeobachter)连载了他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1951—1952年又连载了《嫌疑》。这两部作品分别于1952和1953年以图书形式出版。另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诺言》(1958),原是作者为电影《在光天化日之下》创作的剧本,重新加工之后于同年以小说形式问世。70年代宣布对戏剧彻底失望之后,他依然没有中断小说写作,又出版了《司法》(1985)和《退休探长》(1979)。尽管迪伦马特本人称最初的两部作品《法官和他的刽子手》和《嫌疑》为“传统侦探小说”,并将其创作动机归因于经济困境,是“为了体面地养活家人”,但作家在《戏剧问题》中的一段论述似乎又在暗示,对文学评论的不满与回避才是其选择侦探小说的真正原因。
无论如何,贯穿迪伦马特所有作品的两大主题——对“正义与司法”的解读以及人对世界的认知——在侦探小说中找到了绝佳载体。“正义与司法”的主题无疑是其侦探小说永恒的主旋律,迄今已被多次解读。而从谱写了“传统侦探小说安魂曲”的《诺言》——这部小说也被称作反侦探小说——开始,在迪伦马特戏剧作品中一再体现、日臻完善的“迷宫”隐喻,开始在其叙事作品中若隐若现,呼之欲出。“人对世界的认知”这一哲学问题从中凸显,推动迪伦马特的侦探小说在反传统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代达罗斯视角”与框架叙事
古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的弥诺斯请求海神波塞冬赐给自己一头白色公牛以帮助自己取得王位。得偿所愿的弥诺斯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在事成之后将这头牛献祭给波塞冬,因而遭到了海神的惩罚:他的妻子爱上了这头公牛,与之生下了半人半牛的怪物弥诺陶洛斯。弥诺斯请逃亡至此的能工巧匠代达罗斯在岛上修建迷宫,以囚禁怪物;而于克里特战争失利的雅典人则定期送出童男童女以献祭给迷宫中的弥诺陶洛斯。代达罗斯所建的迷宫曲折复杂,岔路繁多,没有人能够认清道路,从中逃脱。后来,英雄忒修斯来到克里特岛,在弥诺斯女儿的帮助下,深入迷宫,杀死了弥诺陶洛斯,借助于绑在手上的红线离开了迷宫。而迷宫的建造者代达罗斯则凭借巧手制出一双翅膀,飞上天空,离开了克里特岛。
这个幼年从父亲那里反复听到的代达罗斯的故事,在迪伦马特心中种下了“迷宫”的种子;后来,他随家人从科诺尔丰根搬到大城市伯尔尼,这颗种子开始萌发,“迷宫”投影到他身处的环境之上。二战之后,世界格局发生巨变,纷繁复杂的形势构造了更为广大的政治“迷宫”,关于集体罪责的公开讨论以及个人良知的沉默,总是并行不悖,法律与公正的不对等问题日益凸显。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作为个体的人无法在每个领域成为专家,只能迷失在庞大的知识“迷宫”中。“看不透的自己、看不透的政治、看不透的科技和看不透的宇宙,最终构成了这个看不透的迷宫。”因此,世界是个“迷宫”这一认知,伴随迪伦马特的个人经历尤其是他对周遭环境的感受不断深化。
迪伦马特将“迷宫”认知付诸笔端,还是他在科学与哲学方面不懈研习的必然结果。人类似乎永远也无法为身处的“迷宫”绘制一幅精确的地图。“我设计出一个镜像世界,与我所经历的世界相对照。”这或许是英雄忒修斯手中最后的红线,而这根红线显然来自于对迪伦马特影响至深的康德:既然人受到认知能力所限,无法真正认识“物自体”的世界,那么我们就只能通过现象世界——即所有可能性经验去推论“物自体”的世界。
迪伦马特的父亲身为新教牧师,讲述“迷宫”神话的本意或许在于强调人类的“罪与罚”;然而康德“无论纯粹理性还是实践理性都无法验证上帝存在”的论断,却深深动摇了迪伦马特的宗教信仰,使他转而追求自然科学。如何认识自己身处的“迷宫”?如何走出“迷宫”?迪伦马特不断地进行探寻。青年时代,他在伯尔尼和苏黎世学习哲学,更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一直保持兴趣。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于1927年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表明:精确测量宇宙当前所处状态是不可能的。而费英格的仿佛哲学则帮助他找到人类追求知识的路径:把不可靠的认知当成工具去追求、去接近真相。从努力飞上天空来认知世界,继而认识到永远无法认知真相,从而借助建构镜像世界反映真实世界,以达到接近真相的目的——这正是迷宫认知对迪伦马特文学创作的塑造过程。
选择框架叙事来展现“迷宫”并非偶然。迪伦马特的侦探小说创作对这种“嵌入其他叙述的叙述”尤为钟情,在创作生涯的中后期,写了三本在结构上如同一个套系的侦探小说。框架叙事的结构在西方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侦探系列小说在20世纪也早非新鲜事,侦探小说能够成为系列的前提是,作为主人公的核心人物经过各种曲折惊险破解了谜题,伸张了正义,故事因此获得传承的价值。但也早有侦探小说理论家如埃德蒙·威尔逊指出,侦探小说中光明的结局乃是其简单肤浅的标志。在迪伦马特笔下,我们完全看不到这种乐观而肤浅的简化。作品中的核心人物往往无法伸张正义或忍受病痛折磨行将就木,作者要表现的并不是善恶终有时的大快人心和酣畅淋漓,而是人在不可控命运前的无奈与无力感,是人在探究世界可知性过程中的真实遭遇。
《诺言》《司法》和《退休探长》三部小说在叙事模式和人物设定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所有故事几乎都是以乡村或小城为背景,相对封闭而固定的场域恰恰符合“迷宫”意象对空间的要求。而其中“作家”的角色境遇却在不断变化。这不变之中的变化,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迪伦马特“迷宫”隐喻中的自我定位,其实是一种自我移位——早期,迪伦马特将自己视为迷宫中的童男童女,他们迷失在无尽的岔路之中,被弥诺陶洛斯吃掉,或是由于恐惧而被彼此杀害;后来,他将自己视为代达罗斯,试图通过飞上天空——创造“间离”,而看清迷宫;最后,他意识到人类认知的局限使他永远无法达到代达罗斯的位置,永远无法俯瞰全景,转而通过创造“镜像的世界”,展示各种可能性而去塑造真正的世界。
三部小说的核心情节都嵌套在一个“作家”的故事里。这个“作家”显然就是迪伦马特的化身:《诺言》中的侦探小说家“我”不正是之前创作了两部“传统侦探小说”的迪伦马特吗?作家的第二自我化身H博士,对于传统提出异议,正是这种认知催生了这部传统侦探小说的安魂曲。《司法》中的作家“我”在聚会中被女主人错认为“马克斯”,这一情节包含了幽默以及对迪伦马特同时代作家也是他的友人马克斯·弗里施的致敬。这难道不也是从侧面提醒读者“我”即是迪伦马特吗?《退休探长》中,广播节目评论到的那位年近60、盛名已逝、灵感枯竭又再度创作侦探小说的作家,无论是年龄还是经历,都完全是迪伦马特本人的写照。当代叙事理论与文学研究的发展变化告诉我们,即便是面对自传性质的作品,也不可贸然将叙事者与作者等同。我们要证明主导这些框架叙事中的“作家”与迪伦马特本人的关联,也并不意在辨析故事的自传性质究竟有几分,而是为了说明迪伦马特作品的现实相关性。这位扎根于生活本身又从不浮于现象的作家,是借助框架的叙事,以最直观的方式——通过一个身份与自己相同的人物——干预故事,表达他对这个世界不变的关注与变动的认知。
迷宫的初现:飞翔的代达罗斯
“迷宫”的认知催生了迪伦马特笔下诸多人物,他们都可以从古老的“迷宫”中找到原型。弥诺陶洛斯是“罪恶”的化身,它吞食被献祭的童男童女,在迷宫中掀起混乱;而《诺言》中,在树林用剃须刀杀掉小女孩的智力低下的大块头阿尔伯特·施罗德,几乎就是一个活脱脱的牛头怪物。忒修斯是代表正义的英雄,他凭借勇气与智慧杀死怪物又全身而退;在迪伦马特的侦探小说之中,忒修斯化身各种角色,只不过慢慢从英雄沦落为悲剧人物。代达罗斯虽然是迷宫的缔造者,可迷宫的复杂程度使得他也几乎不能找到出口,只有凭借翅膀翱翔于迷宫之上,从这一视角将错综复杂的迷宫一览无遗;而迪伦马特则经常乔装打扮,出现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有时是《诺言》当中的侦探小说家“我”,有时是《司法》中收到手稿、决意一探究竟并最终将之出版的作家“我”,有时又是《退休探长》中盛名不再的作家。这种穿梭,勾勒出“作家”迪伦马特迷宫视角的改变:这位代达罗斯从翱翔于迷宫之上俯视一切,到渐渐堕入迷宫。
《诺言》中的核心情节为:小女孩格里特丽在树林中遇害,报案者——有强奸罪前科的小贩贡腾——被村民一致认定为凶手,探长马泰伊承诺要找到真凶,这既是对遇害少女格里特丽的双亲的许诺,同时也是对小贩贡腾和对村民的许诺。贡腾在警官亨齐的刑讯逼供下“招认”了自己未曾犯下的罪行,随后自杀。此间已经得到擢升的马泰伊,在飞机起飞前改变了前往安曼就职的计划,决心履行自己的诺言,开始精心布局捉拿真凶。然而造化弄人,凶手在落网之前丧命于车祸,而马泰伊却对此一无所知,始终苦苦等待,最后酗酒成瘾、精神失常。
格里特丽画笔下的凶手是个“巨人”。从后文我们得知,他先天智力低下,长期受到大大年长于他、地位高于他的妻子的压迫,由此而产生的变态心理使之做出引诱并残杀小女孩的行为。可见,这位施罗德先生在外形与内心都与牛头怪弥诺陶洛斯如出一辙。“它不是一个有着牛头的人,而是一只有着人身的牛”,道破了其智力上的低劣;其“罪恶”同样是与生俱来——弥诺斯欺骗神的后果;弥诺斯用迷宫困住牛头怪也和施罗德被其妻子禁锢在不对等的婚姻/家庭关系中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格里特丽、两个被凶手残杀的女孩、被马泰伊用作诱饵吸引凶手的玛丽安妮和小贩贡腾都是迷宫中的被猎杀者。贡腾并非死于“牛头怪”之手,而是因为被村民和警察认定为凶手、遭到逼供而自杀,这一情节恰恰与迪伦马特对“迷宫”故事的进一步思考相契合:既然没有人知道“迷宫”的路径,那么弥诺陶洛斯是怎么找到迷宫中的人并吃掉他们的呢?所以多数人并非是被弥诺陶洛斯吃掉,而是他们在恐惧中互相猜疑,互相残杀。探长马泰伊虽然对案件进行了(事后证明是)精准的分析,却也没能抓住凶手,因为“偶然事件”——车祸的发生使其得到了命运的审判。这位闯入“迷宫”的忒修斯,最终没能找到弥诺陶洛斯,他手中的红线——人类的逻辑推理显然无法带他走出“迷宫”。
迪伦马特将这个已臻完美的“迷宫”故事,巧妙地嵌套在侦探小说作家“我”巧遇前任警察局长H博士并结伴同行的故事之中。H博士对于“我”关于侦探小说的讲座不以为然,为了证明侦探小说的情节过于重视逻辑推理而忽视了现实,忽视了偶发事件的重要性,他向“我”讲述了马泰伊的故事。凶手的妻子施罗德太太在临终忏悔时向H博士透露了马泰伊推理中缺失的一环——车祸导致的死亡。这样,作为事件讲述者的H博士和倾听者、再创作者“我”就得以凌驾于迷宫之上,以代达罗斯的视角审视迷宫。
迷宫的延展:下落中的代达罗斯
《司法》的创作开始于《诺言》出版之后不久,与《诺言》的关系极为紧密,这不仅体现在其框架故事中的“我”和前警察局长H博士与《诺言》的框架故事人物相同,也体现在英雄忒修斯最后相似的命运上——马泰伊和斯派特都借助酒精逃避到自己想象的世界之中。
《司法》的核心情节是老谋深算的州议员伊萨克·科勒在众目睽睽之下射杀了温特教授,被法庭判为谋杀罪而入狱。他假借科学之名——探索现实之外的其它可能性,重金利诱初出茅庐的律师斯派特展开调查。斯派特的调查最终导致事件反转,没有杀人的贝诺因恐惧而自杀,被民意及法庭认定为凶手,而真正的杀人犯柯勒却无罪释放。斯派特无法接受正义被颠倒、自己被利用而成帮凶的事实,决意射杀柯勒并自杀,却最终未遂心愿。
从叙事层面看,《司法》相比前作则要复杂得多,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分为四个部分:(1)作家“我”在聚会上偶遇一名身份显赫的老人及其女儿,老人向众人讲述了他因为康采恩的内部权力之争与某人产生矛盾,临时起意,在饭店当众犯下了谋杀罪。然而由于证人证词矛盾,无法找到凶器以及他本人缺乏作为凶手的动机——“对检察官来说,一个康采恩是看不透的”,他最终被陪审法庭判为无罪。(2)数月后,“我”因为购买乡村别墅而来到史提西山谷遇见“说情人”。酗酒成性的“说情人”向村民炫耀,因为他的辩护,一个有罪之人被无罪释放,他为了匡扶正义,在机场射杀了这个人,并且他本人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3)乡村别墅购买失败,“我”整理故纸堆时发现了H博士寄来的手稿,是律师斯派特对自己被卷入科勒案件的过程及所涉全部人物的讲述。(4)“我”意识到聚会上遇到的老人、女儿以及乡村的“说情人”正是手稿中的科勒、海伦娜和斯派特,决意进行调查。“我”将手稿寄给科勒,接到邀请到他家拜访。海伦娜向“我”讲述了最后的版本——康采恩的所有者莫妮卡·施台尔曼指使温特、贝诺及达芙妮强奸了海伦娜,海伦娜向柯勒提出报仇,经过精密策划,柯勒射杀了温特,并利用斯派特的调查除掉了贝诺及达芙妮,最后也杀死了莫妮卡。
小说在安排上打乱了时间顺序,先是斯派特的手稿,手稿记述的内容到斯派特赴机场射杀柯勒之前几个小时戛然而止;之后是小说的后记,分别补叙了聚会事件,柯勒的版本、购买乡村别墅事件,斯派特版本的后续和造访柯勒的庄园,海伦娜的版本等内容。柯勒的版本中没有提到斯派特,按照海伦娜的说法,父亲忘记了斯派特这个人,因为他并不重要;而斯派特的版本中,柯勒最后被他杀死了,可柯勒事实上依然活着。海伦娜的版本中,柯勒杀死温特是他们二人精心策划,凶器被她扔入泰晤士河;而柯勒的版本中,他杀死温特是临时起意,他盗用了同行的英国部长的手枪,事发后又还了回去。斯派特认为柯勒杀人是因为他将自己等同于上帝,乐于摆布他人命运;柯勒将谋杀看成是维护康采恩利益的手段;海伦娜认为复仇是父亲杀人的直接原因,但是又怀疑他本来就乐于促成强奸事件以便借此实施谋杀以达到某个不为人所知的目的,他的背后有更大的力量推动他的行为。
这里依然是混乱的“迷宫”景象,却在侧重点上与前作《诺言》有所不同。《诺言》完美地演绎了忒修斯追杀弥诺陶洛斯的故事,“迷宫”中的各色人物纷纷登场;作家“我”以凌驾于故事之上的视角揭示了人类的理性在混乱的世界中落败的真相。在《司法》中,迪伦马特显然更着力于展现“迷宫”中的各色人物对于环境的认知。人只能由自己所见去推想世界的本来面目;然而人的认知是有局限的,这不仅仅体现在人无法翱翔于迷宫之上纵观全局,更是因为人的感知往往掺杂主观感受。《诺言》中,村民们纷纷指认无罪的小贩贡腾,证词自然站不住脚;然而《司法》中,有很多人明明亲眼见证了柯勒开枪杀死温特,证言却依然漏洞百出——每个人对于“迷宫”的认知其实又再度构建了新的“迷宫”。不同于《诺言》当中能够纵览全局的“我”,《司法》中,“我”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也迷失了。在柯勒究竟是不是凶手这一点上,聚会上“我”几乎和众人一样持否定态度,而和海伦娜交谈中,海伦娜证实了放在英国部长口袋里的那把由她亲手上了子弹的枪确实开过,所以确实是柯勒杀死了温特。然而柯勒杀人的背后真实原因,“我”就和海伦娜一样无从得知了。所以在《司法》中,框架故事中本该像代达罗斯一样掌握全景的“我”最终败下阵来,作家失去了对他所创造的作品的掌控力。
终曲:置身迷宫的代达罗斯
《退休探长》是迪伦马特尚未完成的一部作品。其核心情节是即将退休的探长赫希施泰特勒为了给其职业生涯中未了结的案件画上句号而逐个探访涉案人物。探长在开车途中收听广播,其中对一个作家进行了评论。“作家”情节与“退休探长”的情节融于一场暴风雪之中:作家在名声衰退之后创作侦探小说,称其灵感来源于一场暴雪;探长希施泰特勒在开车途中经历了一场暴雪,并希望这场雪不要像作家梦中的雪一样大。
按照迪伦马特的前两部侦探小说《诺言》和《司法》,“作家”情节本应是嵌套在“退休探长探访未完结案件主人公”这一核心情节之外,以更高一层的视角对核心情节进行补充、解读,核心情节与框架故事就像是一个纸环的内侧和外侧。然而本作之中,读者就像是莫比乌斯环上的蚂蚁,从内侧不知不觉地爬到外侧,又再度回到内侧。“作家”视角与作品中的人物视角融合到一个层次之内。
核心情节中的探长赫希施泰特勒,让人不由想到《法官和他的刽子手》以及《嫌疑》中的探长贝尔拉赫。然而细细分析,迪伦马特侦探小说中的忒修斯早已今非昔比:贝尔拉赫阶段,忒修斯英勇奋战,无论是靠自己的力量还是借助机遇、旁人的援手总能战胜弥诺陶洛斯;马泰伊和斯派特阶段,一腔热血的忒修斯在追求正义的途中迷失,无力走出“迷宫”;而赫希施泰特勒阶段,忒修斯似乎已经摆脱了“杀死弥诺陶洛斯,追求正义”这一束缚,对于走出“迷宫”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对于迪伦马特而言,经历留下的诸多“印象”最终构成了文学作品,从60年代开始进行的“素材”的创作正是对这些“印象”的处理,尤其是那些迄今为止没能形成文学作品的素材,写作是作家走出“印象”迷宫的途径。“探长”对于未完结案件的处理与“作家”对于未形成作品的素材的处理何其相似!
《退休探长》的创作晚于《司法》。有人认为,此时的迪伦马特对于代达罗斯视角或许有了新的设想,然而在创作中最终无法实现新的突破,导致这部小说始终未能完结;通过这次试验,他意识到了将框架故事与核心情节相融合的可能性,但必须小心谨慎地操作,否则将导致失败。然而笔者认为,框架故事与核心情节视角的融合恰恰反映了迪伦马特后期对于“迷宫”的深层次思考。如果说《诺言》中的“我”是飞上天空的代达罗斯,《司法》中的“我”是虽然飞上天空,但仍然无法纵观全局的代达罗斯,那么《退休探长》中的“作家”就是身在迷宫的代达罗斯——每一次对世界进行理解的尝试都是一个新的“迷宫”的构建,人将永远处于“迷宫”之中。
迪伦马特一生作品众多,展现各种观念、风格和结构的方式也异常丰富,其中诸多主题暗含循环反复与重新组合。偶然事件对人类命运的左右、司法公正的难以控制、人类的求索热情与宇宙的岿然冷漠莫名其妙的交织,形成了一幅幅看似混乱却并非毫无头绪的世界图景,“迷宫”隐喻从中诞生,这对于理解迪伦马特的作品至关重要。《诺言》《司法》和《退休探长》创作间隔很长,统统采用框架叙事结构,不得不说作者是有意而为之。在三部作品中,叙事者视角经历了从纵观全局到落入迷宫的转变,这不仅是为迎合叙事技巧,也是作者本人对一些宏大问题从被动识别转为主动表达所致。换言之,作者经历了创作思维和认识论的转变,即,从将世界视为“迷宫”,到采用“迷宫”作为表现世界的手段。
任何宏大问题的认知和表达,无论是道德、正义等伦理问题,还是政治、社会、宗教问题,归根结底都以人对世界的认知、人对知识的追求为前提。侦探小说虽然从体裁上来看属于通俗文学,然而迪伦马特在创作侦探小说时并没有落入传统窠臼,并不单纯追求情节的悬疑。无论侦探小说还是戏剧作品,都是他对世界的认识、反映及构造。渗透于中后期作品中的“迷宫”隐喻,在其侦探小说得到了充分的演绎。通过框架故事当中的“作者”视角,对小说人物所处的“迷宫”进行观察,这正是迪伦马特所谓的“退后一步”要创造的间离效果。而作家的最终目的,无非是换一种角度和方式,更好地看清自己所处的世界。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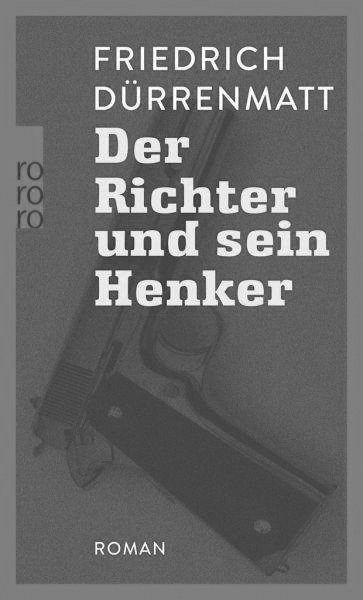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