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是中国历史的“大时代”,始于陈桥兵变,终于南宋王室与臣子的崖山蹈海,历经十八帝和三百余年。陈寅恪认为,华夏文化绵延数千年,“造极”于赵宋一朝。中国封建王朝的吏治权术、朋党之争、士人悲欢、外族入侵、山河沦丧、王朝更替这些帝制元素或历史悲歌都可以在赵宋时代得到清晰的再现。正因为此,宋朝成为后人不断回望、凭吊、想象和书写的对象。
赵允芳的这部《可惜风流总闲却——宋十家读札》(以下简称《宋十家》)以赵宋时期执牛耳于文坛或影响政坛走向的历史人物为书写对象,如欧阳修、赵抃、王安石、两苏、赵佶、岳飞、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以人物的生平行踪和精神人格为经,以两宋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这些社稷肌理和历史演进为纬,纵横切入,入史探幽,复活出一幅立体多面、有血有肉的大宋王朝和士林彩绘。其语言生动秀美,叙述亦简亦繁,虽只论及十家,但每家既是独立成章的精致专论,合在一起又构成关于两宋王朝及其士林文人的通史研究。
我更关注的是,《宋十家》用什么方法叙述历史,以及切入历史后聚焦哪些命题。当下的历史散文或通俗读物,在处理历史时,有的采用“闲话”或“戏说”的方式,将历史粗鄙化;有的采用小视角、小断片、小瞬间呈现历史,从历史中搜奇觅趣。这两类写作往往将历史奇观化、碎片化,通常历史感不足,经不起学术性推敲。《宋十家》切入历史的方法明显有别于这两类。看书名,或会以为这部作品是轻逸型散文,实则不然。纵若在美学上和部分章节里有文人风流、闲云野鹤和遁隐山林这些轻逸之气,但总体上,这是一部探究大历史真相、勾勒文人心灵史的凝重之作。尤其是作者进入历史的方式,是笨重而直接的“正面强攻”型。所谓正面强攻,是她没有讨巧地把大时代隐居幕后,进而对历史脉络或人物心灵进行断片式或想象性的叙写,而是忠实地细叙关于大时代的历史版图,并在历史坐标中评判人物功过、探求历史规律。《宋十家》的写作,用的是“笨功夫”,作者几乎是在用生产学术著作的方式进行着历史散文的创作。
赵允芳曾做过11年的文化记者,又是现当代文学博士。她的博士毕业论文当年便入选了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评选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成为国内以博士论文入选该丛书的首例。但她很快从顺风顺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媒体行业一线中抽身而出,一头扎进两宋历史,与古为徒,一写就是五年。这种跨界无疑是一次冒险,更是一次没有功利的自我放逐。
多年的记者职业生涯,又使她善于捕捉每个历史对象的最佳切入点,从层累、繁冗的历史叙述中找到自己的兴奋点和着力点。比如南宋岳飞之“怒”是人们熟知却未必真正理解的一种强情绪和大美学,赵允芳通过对中国文学史的勘察,既讲述了岳飞豪迈、血性的一面,梳理出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怨而不怒”、以司马迁为代表的“虽愤不怒”和岳飞的“亦敢亦怒”这一重要美学流变;同时,她还有意突显了岳飞以《小重山》为代表的悲情、诗性的一面,使历史人物以一种更趋饱满、真实的精神面目再现于世。又如,在李清照的诗酒人生中,作者抓住其在艺术上的焦灼、婚姻中的孤独,还原了她当年所遭遇的“尬”与“憾”,别具新意地重现了女词人的跌宕人生。
伍尔夫在评价历史学家吉本的巨著《古罗马帝国衰亡史》时这样说:他孤独地沉醉于远古的事件、错综复杂的章节安排和已故者的心灵与身体。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描述赵允芳写作《宋十家》时的情态。如同吉本一样,为了达到对历史的准确理解,赵允芳细细打量每一个历史碎片,考辨既往历史叙述的真伪,试图尽可能复呈历史的真实史迹。正是这种务实求真的治史风范,赵宋王朝的江山轮廓、经脉纹路逐渐清晰,那些各具韵致的古人得以灵性复活。读书中人物,你不觉得是隔着千年的历史人物,而宛如隔壁邻居般亲切、鲜活。
赵允芳深谙人物塑造上的“心灵辩证法”,注重写出历史深处人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立体性,尤其倾力勾勒那些易被曲解和遮蔽之处。她写大家、名家,毫不回避对其人格弱点、思想局限的批评,客观坦言“大家之小”和“强者之弱”。比如王安石一章,一方面浓墨铺写他的济世抱负和推行变法的艰难实践,同时,更把笔触投向他在这场悲剧性政治实验中的个人局限,由此,一个“强狠傲诞”而又缺少气度的权力人物便跃然纸上。但随之,她抓住王安石的晚年孤独来写,又将一个强者的弱处坦现无遗。
梁启超认为,治史者,不能于人外求史,惟在认取此“人格者”与其周遭情状之相互因果关系而加以说明。确实,以史立人,以及在“历史化”的语境里塑造人,这是面对历史应有的正确姿态。可以说,《宋十家》借助于史料研探和文本细读上的“死力”,以及写作上的耐力、叙事和语言的魔力,真切复活了赵宋王朝的风云与景致,还原了文人仕宦的人生百相和精神图谱。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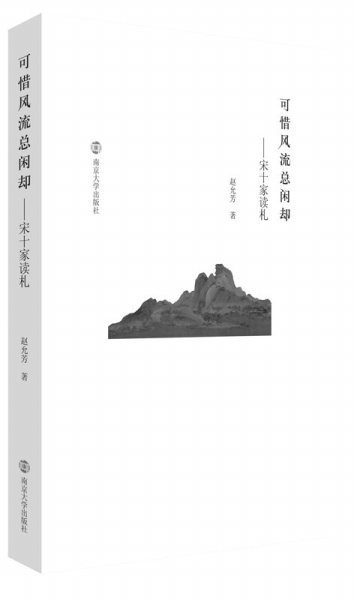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