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起来或许叫人难以接受,当我国学者蜂起而且群情激昂地讨论什么是“中国古典学”时,“古典学”这一范畴大概已经被定义两百年了。客观上说,我们的讨论不能不从这一事实开始。
110年前,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雷特编撰出版了《牛津六讲:人类学与古典学》一书。他在前言中指出,“荷马,赫西俄德,希罗多德——把这些归于古典学不会遭到任何质疑”;紧接着他基于罗马文化“习得”的特性,解释了将关于罗马的课题(比如巫术、净化等)归于古典学的合理性。德国学者尤里奇·冯·维拉莫威兹-莫仑道夫在《古典学的历史》中指出:“古典学术的本质……可以根据古典学的主旨来定义:从本质上看,从存在的每一个方面看都是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维拉莫威兹在定义古典学的任务时,说:“该学科的任务就是利用科学的方法来复活那已逝的世界。”正如休·劳埃德-琼斯在回顾古典学的历史时所说的,“希腊艺术和文学的巨大影响甚至最终必定会弥漫在各个大学和它们所提供的教育之中。……最终古典学在中学和大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到19世纪末期,当英国的各个大学为古典学术设立了学位考试之后,古典学术的地位在课程中的位置凸显了”(《古典学的历史·导言》)。
由此足可见出,在西方,古典学是相当古老而成熟、稳定的学科。这种历史事实造成的一个结果是,要么我们自己重立名目以求安全,要么我们甘冒以下的风险:所有重新定义“古典学”的努力,都可能被斥责为不懂“古典学”的人别有用心地吆喝“古典学”。现在看来,我国学界尚无抛却这一名号、改弦更张的明确有力的动作,笔者还是得冒险谈一谈“古典学”,特别是要谈一谈“中国古典学”,——我们完全拥有这种言说的权力。
二
我们显然不能将中国古典学等同于所有关于古代中国的研究;具体说来,就是不能将它等同于对中国古代文学或文献或语言的研究,不能将它等同于对中国古代历史或哲学的研究,也不能将它等同于这些学科的机械相加,等等。所有这些简单化的思考和处理都会使中国古典学丧失独立或被给予特别重视的理据。
古典学的成立其实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考虑,即它的研究对象不仅是古代的,而且是从整个历史来说最具有本源性质和典范意义的。古典学成立而且被世世代代推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核心对象具有垂范千古的启发和本源作用。把握了这一基本点,中国古典学的核心对象就十分清楚了,即其要务应该是研究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典籍、思想学说或文明。吕思勉极深刻冷静地指出:“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先秦学术概论》)他所谓“先秦之学”主要是指先秦诸子百家之学。罗根泽谈自己作《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计划,“拟先将中国学术思想分为四个时期”,其中第一个时期是从上古至东汉之末,他称之为“纯中国学时期”(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四册自序)。这些判断都十分精确和直截。被后人归到经、史、子、集各部的先秦两汉典籍是我国古代名副其实的“元典”,是我国古代悠久传统的根和魂。后代的典籍固然浩如烟海,可在古代主流传统中,其中绝大多数著作都立足于承袭和弘扬元典的核心思想和价值。中国历史上的主流传统以及反主流传统,前者如儒学,后者如道家、墨家学说等,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和定型的,两者均贯穿千百年历史,延续不衰。
从另外一些角度考察,可以得出同样的认知。先秦两汉时期的语言文字具有本源意义,毋庸赘言。至于文学,中国文学最本质的东西,比如言志抒情等,此时已被强有力地奠定了。关于中国文学,我们必须同时强调,先秦两汉典籍垂范后代文学的价值并非仅仅来自《诗》《骚》一类“纯文学”作品,逸出现代人文学视野、通常被归于哲学的诸子或经书,以及通常被归于史学的史传,也都是不可忽视的。
将中国古典学的核心研究对象限定在先秦两汉时期不仅不背离古典学成立的基本意旨,而且契合中国文明发展的实际,具有充足的现实和逻辑依据。
三
其实,就本质而言,中国传统原本就是古典学的传统。
文献记载,在孔子生前大约半个世纪,楚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士亹向贤大夫申叔时请教教学事宜。申叔时列举了“春秋”“世”“诗”“礼”等教育科目,并阐发了各科的宗旨。申叔时所举殆均为古代篇什之类名,所以不能将相关书籍直接等同于后人熟知的儒家经典。然而这些科目都有周代礼乐文化的鲜明特征,它们即便不能等同于后世的儒典,也必定导夫先路,跟儒典有十分密切的关联。如此以一批典籍为传统价值的本源,基于阐释、发明来授受传播,最终在现实社会各层面上达成它们的规范作用,这从本质上说就是古典学的。
不过,局限于贵族子弟的教育,跟面向社会大众的教育有天壤之别。孔子推动私学成立和发展,才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他将传统典籍《易》《诗》《书》《礼》《乐》,以及基于鲁国史自作的《春秋》,建构为核心典籍(六者即通常所说的六经,古人亦称之为六艺),奉行“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之教育宗旨,“自行束脩以上,……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其“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由此缔造了成为战国显学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主要骨干”的儒学。孔子建构并确立了儒家核心典籍,在阐释与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形式,自觉向广大社会授受传播,在一定范围内真正将经典负载的价值落实到普遍的个人行为、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等方面,久久为功,形成一个有基底、有方向、有发展空间、有生命活力、稳定而且有序的文明。贯穿于孔子教育及其思想学术活动内部、作为儒家立派根基的恰恰是古典学的本质。
儒学和儒家经学是中国古典学的主干,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诸子学说,其成立与发展都具体古典学的特质。吕思勉说,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乃中国历代学术中“纯为我所自创者”。而依《庄子·杂篇·天下》——“一个时代的学术的结论”(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老子、墨子、庄子、惠子等人的学说无不本源于“古之道术”,简言之即本乎古学。历史上真正称得上是原创、作为中国历代学术之源与根的诸子百家之学,其成立都有古典学的意义。而汉代以下直到今天,人们对先秦诸子各家典籍学说、价值规范的研探与诠释、追随与弘扬,更凸显了古典学的立场和宗旨。
诸如此类显示中国传统具有古典学特质的例子,通敏兼人的读者自可触类旁通。
四
中国古典学建立范式的时期是先秦两汉时期,这些范式并不限于典籍,虽然典籍居于核心位置;这些范式对整个中国古代具有“元典”意义,围绕它们形成的主干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流衍至当今。中国古典学的核心对象,亦即中国古典学赖以成立的根基,无疑就是一系列传统赖以生成的先秦两汉时期的“元典”,但后人对“元典”的整理以及再整理、阐释以及再阐释、研究以及再研究等,也都应该纳入中国古典学的视野,尽管它们说到底是捧月之众星。
对中国古典学来说,做好古籍整理及其文献学研究是前提,可更重要、更高一级的追求,是基于古籍整理及其文献学研究,透彻理解古籍的“实质性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定位“我们同那个(古典)世界的关系”。
古典学元典(典籍)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具备一般的文献学价值,而且在于它们承载着无尽的精神财富,包括对社会人生以及天人关系的洞见、哲思和智慧,对情感及精神世界的挖掘与表现,价值关怀与担当,文化、历史认知与经验,对个人外部行为及内部思维、情感的规范和协调,对人际关系与社群秩序的规范和协调,对民族文化身分的塑型和认同,安身立命之道,为文学出言谈之道,等等。
我想,不会有人否认具备读懂古典学元典的能力是从事古典学研究的基础。连古典学元典都读不懂,中国古典学是不可想象,也无法达成的。但这仅仅是起点,而非目的地。有鉴于此,西方古典学涵盖哲学、文学、艺术、科技、历史等范域的研究,作为一般模式是不可动摇的,中国古典学也必须如此。只不过无论是中国古典学,还是西方古典学,都必须同时拒斥“让这种独立的东西窒息了整体意识”。相对于传统的文、史、哲等学科,中国古典学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应该是“全息的”,至少需要在各个层面上实现融通。比如,不能从主观或客观上将诸子哲理层面拱手让给哲学研究者,将诸子言说艺术层面拱手让给文学研究者;不能从主观或客观上将《诗经》经学层面抛给哲学研究者,将其言志抒情层面抛给文学研究者。唯有如此,中国古典学才能跟传统的文学,或者文献学,或者史学,或者哲学等学科,清晰地区隔开来,具备独立的充足理由。
五
正是在古典学意义上,我国新出简帛的价值得到了有力的凸显。《诗论》《五行》等新出秦汉以前的文献(从时间上说,它们大约关联着从孔子到孔门七十子以及子思子的时代),是照亮先秦学术思想史一系列巨大黑洞的光。很多极为重要的学术思想关联和轨迹在失踪千百年后,因它们而重现人间,中国古典学本体及其研究和认知被刷新被改写,令人既惊且喜。中国古典学不得不重新开始,而简帛古书的价值则仍将得到持续不断的发掘。
对中国古典学而言,古书的整理和研究,包括对其文本的校注,是必须迈过的门坎,而对简帛古书的校注尤其如此。要使简帛古书在各领域得到广泛有效的利用,高质量的校注必不可少。所以裘锡圭指出:“要进行古典学的重建,必须更快、更好地开展新出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新出文献,有些尚未正式发表,有些还未发表完毕。已经发表的新出文献,有不少还需要重新整理。”(《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
毫无疑问,并非有了出土文献,就自然而然可以获得对中国古典学本体和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新认知。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进行积极的建构。这意味着既要因应千百年传统知识、想象和思维定势的影响,廓清层累的历史障蔽,又要在简帛古书和传世文献之间实现有效的贯通,其困难可想而知。就是说,研究传世文献不能单单就这些传世文献下工夫,研究新出古书也不能单单就这些新出古书下工夫,对于这两方面的研究来说,发掘二者间的历史关联都是不可偏离的重要基础。中国古典学必须从这里再出发,中国古典学的重大突破也必将在这里出现。
遗憾的是,学术界对新出简帛古书还弥漫着一股不分青红皂白的怀疑。说简帛古书不存在任何作伪的事实无疑是武断,可大多数简帛古书恐怕是想作伪都做不出来的,——如果把简帛古书等同于在一批古简或几片旧帛上写一些文字,就完全偏离了事实的根本。对于严肃的学者来说,认真研读这些古书是第一位的,如此可以避免这样一种可能,即你还在怀疑或游移,历史却已经被大幅度改写了。
(本文节选自《简帛〈诗论〉〈五行〉疏证》序言,内容有删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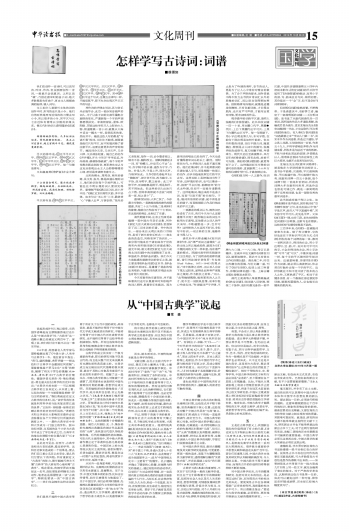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