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云彬先生,跟我以前所待的人教社,有很近的关系。他在1950年10月19日的日记里写道,“两月来有数事可记者……(二)出版总署编审局分化为人民出版社及人民教育出版社。余被推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筹备委员。大约下月即可正式成立矣”。成立人教社前后,宋云彬为叶圣陶所重,为初创元老;而他欲去京南下到杭州主持民盟时,叶圣陶也极为不舍。
叶圣陶如此看重宋云彬,跟他是“教育出版社”的中坚有关。一个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对教材建设有这么重要作用的人物,不须说,身上肯定是有些个故事的。而这些故事的最佳讲述者,在我看来无疑就是宋云彬和他的日记。以往大学者日记多,读他们的日记,当然是可以了解学术史或者看看几十、百年前的旧日烟云,不过像宋云彬那样,让编课本与寻常生活活色生香地纷呈于一处,且能在天命之年保有赤子般的率性与童真的,也许更能让我们这些七十年后的年轻人,更能对课本往事有个“历历在目”的真切感受。
一
1949年年初,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了。这时候,宋云彬跟当时许多民主人士一起北上了。北上的那一天,是1949年2月28日,一块儿走的有27人,其中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俞寰澄、张絧伯等自不必言,文化教育界比较有名的尚有叶圣陶、郑振铎、曹禺、傅彬然等人。叶圣陶和他主持过的开明书店,就如同“开明”这两个字一样,在当时绝对是进步的。于是围绕着叶圣陶,形成了一个文化教育领域的大码头。因为本身就在出版圈,短不了过从较密的不同作者,不过在叶先生身边来来往往的朋友里,让人印象深刻的还得说是编课本的人。透过宋云彬的眼睛,可以看看叶圣陶的“粉丝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与影响,以及他们参与新中国课本建设的情况。
1949年3月18日,走了20天的叶圣陶等人,七时从天津上车,“十时许即抵北平东站”。从香港北上的人是27位,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来迎接他们的,几乎是对等的人数,“约二十余人均在车站相候”,更不平常的是,来迎候的人里,有“叶市长及李维汉、郭沫若、马夷初、沈衡山等”,由此可见规格之高了。规格之高并未随接站而结束,19日“晚,叶剑英、齐燕铭、连贯等设宴为余等洗尘”,22日“今日董老(必武)来,至各房间殷勤一番而去”,23日“上午十时许,张闻天来”。在断断续续地跟友人往还和学习、开会几日之后的4月5日,关于教材的事儿开始提上日程了,那天民盟在来今雨轩招待盟员,“适胡绳来,谈编审教本事”,而宋云彬则在当天的日记里感慨,“余当……专心致志,为人民政府编纂中学教本,庶几不背‘为人民服务’之原则也”。其实不管是前面的叶剑英、董必武,还是这里的胡绳,都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即将新生的国家,对于人才的重视,当然,对于叶圣陶等人来说,他们在人才方面的重要性还有另一层,那就是他们是进步的可以编写课本的特殊人才。
叶圣陶等人到北京后,前后参加了很多饭局,其中影响了七十年的对今天教材至关重要的是1949年4月8日的一餐晚饭。宋云彬先生的可爱之处,其中的一个是细腻而敏感。比如对于吃饭,宋先生有时喜欢记录是在哪里吃的,和谁吃的,更重要的是,有时他要写上食物的名字,并不忘加上两句评说。比如那年3月17号在沧州,宋先生写道,“晨八时与铸成、芸生、尊棋至车站附近食白粥、油条,至佳”;22日“中午许昂若来,与之对酌,下酒物仅花生米,昂若则谓此乐不可多得也”;29日“到‘都一处’吃面食,饮白酒四两”;4月30日“下午六时应芷芬约,吃砂锅居。砂锅居为北平著名菜馆,专以猪肉做菜,名目繁多,然味殊不佳”。不过这一回饭局,宋先生的记录却不太一样,“晚六时陆定一、周扬、晁哲甫请客,在北京饭店。余准时至,则圣陶、彬然等已先在座矣。陆等请客,为商谈如何组织教科书编审机构事,故凡准备参加此机构者皆被邀,除余等外,有胡绳、孟超、孙起孟、叶蠖生、金灿然诸人,而华北政府正副主席及范文澜等均到。商定机构名称为‘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中央政府未成立前,暂隶华北人民政府。叶圣陶为主任委员,周建人、胡绳副之”。这天的日记就这样结束了,人们已经无法得知席间上了多少饭菜,每款饭菜的色味如何,不过可以知晓的是,这次来到饭桌的人,组建了一个著名的机构,网罗了核心的人员,从此奠定了新中国教材建设的基础。而这,可能是甜酸咸辣之外的,更为悠远醇厚的意义。
4月8日这餐饭后恰好一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很快在15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出席者有叶圣陶、傅彬然、胡绳、周建人、王子野、孙起孟、叶蠖生、金灿然、孟超;会议决定委员会分国文、史地、自然三组,其中的国文组有叶圣陶(兼)、孙起孟、孟超和宋云彬四人,每周开会一次,宋云彬为召集人。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旧不失为高规格的典范,其成员既为学科编写专家,同时又有卓越的组织管理经验,跟大家崇尚的大学里“教授治校”颇有神似之处。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有了这么精良的一个领导班子当然好,可是事多、杂而难,好的领导班子后面得跟着精干的人才能成事儿。人,特别是人才,七十年前真是珍贵难得。陈叔通(叔老)8月22日曾同宋云彬讲,“联合政府即将成立,而人才殊感缺乏,不仅各民主党派中少人才,即中共干部,亦刻苦耐劳有余,学问经验不足也”。而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刻,叶圣陶不可取代的作用就难能可贵了。叶先生的饭局同样不少,不过他的饭局跟别人不一样的,是吃完后还能一起来做事儿,一起做正能量、于国于民有意义的大事。1949年6月15日“蒋仲仁自香港来”;7月13日“朱文叔、叶至美自上海来。文叔参加本会工作”;8月29日“丁晓先携眷来平,将在本会工作,亦住八条胡同”;1950年4月3日“马祖武今日到职……马祖武(《初中语文》)第四册”;1950年9月19日“薰宇来谈,明日将迁入署中住,愈之请其暂在编审局看稿”,此后又有多人相继加入。蒋仲仁、朱文叔、丁晓先、刘薰宇诸人,翻过民国时期老课本的都知道,这些人早年在商务、中华、开明都呆过,可说是一块儿编写课本的老朋友。“举贤不避亲”,叶圣陶的眼光,从当年那些课本上所写的编纂者的名字,就可见一斑了。
这些人当然不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学者,但永远无法否认,他们在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知识构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这是他们的“厉害”之处。其实这不过是厉害的一个方面,更为厉害的是,他们虽不居科研前沿,却可以招致各领域最顶尖的人才来参与课本编写。1949年5月6日,“魏建功来”;5月8日,“三时半,夏康农、沈志远、楚图南先后来”;5月24日,“魏建功约定明天来,商讨高小国语课本”;8月27日,“下午一时半顾颉刚来”;8月30日,“北大教师赵西陆、清华教师王瑶,上午来会,商讨‘大一国文’编纂事”;1950年2月8日,“下午二时半魏建功、游国恩、赵世陆、刘禹昌(字建俞)、周祖谟(字燕孙)来,共同商讨高中国文编辑事,至五时半方散”;1950年3月20日,“《初中语文》课本课文十五课,复写后分送罗辛田、魏建功、吕叔湘校阅”;6月10日,“王了一来东总布胡同总署”……这些人中,魏建功、吕叔湘、周祖谟、罗常培、王力几乎囊括了当时最为顶尖的语言研究学者,顾颉刚为史学,游国恩为古典文学,王瑶属现当代文学,对于语文这样的一个学科编纂而言,后来的多少套教材,都很难有这样强大的顾问团队了。在对于图书装帧远未像今天这样重视的时代,人们却可以在课本上看到“装帧者”的名字,1951年第三次修订原版的《初级小学国语课本〔春季始业用〕》第一册封底,上写“装帧者:古元”。古元是著名画家,建国后担任过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央美院院长,他是将美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最具代表性画家之一,尤擅版画,兼长水彩,作品朴素、简练、自然、清新。邀请艺术水准如此超拔的画家来专为小学课本做装帧,这在各方面条件都是当年无法想象和比拟的今天,有了更多思索和感叹的空间。
二
云彬先生博雅多识,从其遗墨来看文人气质深浓,而如魏晋名士般品藻人物,则在他留下的文字里多有所见。宋先生敏感细腻,所记人物三教九流,有些感受颇能广人见闻。四九年初入都门,有时晚间看戏。3月19日看京戏,“谭富英演《空城计》,殊平平”;3月26日又看京剧,“梁小鸾演《得意缘》,谭富英演《捉放曹》。梁近被推为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思想当甚进步,然艺实平平”;4月9日再看京戏,“尚小云演《汾河湾》,跳踉不堪入目”;他还写了一段掌故,5月15日中午“赴中原公司六楼吃饭馆。饭馆主为侯喜瑞。侯本平剧名角,今改业饭馆,且亲自下厨作菜。菜肴甚佳,尤以甜品为最”;6月2日,“偕伯宁赴戏园看平剧,小翠花演《挑帘裁衣》,甚佳”。这年7月份,宋先生看了几场好戏,集中提到了好几个人,5日“晚文代会有曲艺晚会,与阿龙同去。侯宝林之相声,新岚云之平韵大鼓,王贞禄、胡宝钧、白凤岐、白奉霖、于少章之五音联弹,皆佳。连阔如为北平曲艺界出席文代之代表,然其‘评书’表演殊平平也。冀鲁豫民间艺术联合会说唱组演唱落子、坠子,纯粹土音,不易听懂”;28日到长安大戏院看招待文代会代表的晚会,“李桂云演《蝴蝶杯》,秦腔,高唱入云,闭目听之,殊觉回肠荡气也。李桂云年已四十有六,而表演小儿女态惟妙惟肖,惜配角不佳,满脸荒伧气,未免减色耳。周信芳主演《四进士》,饰宋士杰,配角皆一时之选:小翠花饰宋妻,叶盛兰饰田伦,张春元饰毛朋,袁世海饰顾读。周为‘海派’袖领,自成一家。如此好戏,今后恐不易看到,特详记之”。对艺与人的评说,宋先生往往有自己看法,他记了人名却不为名所囿,比如4月4日赴俞平伯家唱昆剧,“某女士干唱《寻梦》,带道白,甚好”,连那女士的名儿都没记住,可他觉着演得好。
读宋云彬品藻人物,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事儿,也能看到很多我们听说未听说的想法,而其中的一部分以当年亲历者的眼睛看到并以口说到,读来颇让人如怅如思。1949年3月25日,“微闻平津解放后,毛泽东戒其党人,须忘其前功,而努力于建设……初不知毛氏此言系对其党人而发,若夫一般知识分子,正惟恐其忘却过去之光荣历史,而自甘堕落耳”,能洞见毛泽东之明;9月27日下午赴怀仁堂出席政协全体会议,“争辩数小时,幸周恩来作主席,能控制,居然逐案通过,然散会时已十点多矣”,能明查周恩来之能。如同品评艺人一般,宋先生真纯无忌,颇有直率坦诚断语。9月21日赴怀仁堂出席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宋庆龄等人先后发言,云彬先生写到,“讲演词以宋庆龄的最为生辣,毫无八股气,可惜她不会说国语,用一口道地上海话念出来,就没有劲了。陈毅的最简单,也很得体。黄炎培的油腔滑调,既不庄严,又不松动,令人生厌。程潜之讲词文句不通,意思也平常,应考末一名矣”。宋先生当年的感触鲜活生动,可是并不另类,另一个著名的见证者是叶圣陶,他9月21日那天的日记写了同样的事,“以内容言,自以毛氏之言为充实,次之则刘少奇、宋庆龄二人亦有意义”;7月28日,周恩来在全体教代筹备委员茶会上作报告,叶圣陶的感觉是“周君统筹全局,语重心长,深可钦佩”。
从宋云彬的日记里读他品藻人物,一方面是看看历史烟云下的人情世相,另一方面则是从近乎琐碎的细节中,寻绎当年编写新中国课本这样宏大事件下的具体脉络。宋先生作为一个在场者,并不只是一个见证,因为品藻人物也并非简单的事儿。就如同《三国演义》里的青梅煮酒论英雄,“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能够品评英雄的,没有眼光、胸怀、底气那是准不了的。宋云彬日记里的话,带有自然高度。
宋云彬尊重叶圣陶,是把他作为老师来拥戴的。工作、生活中的大事小情,一般都要和叶商量,宋云彬的日记里往往也有“圣陶亦赞同”“圣陶亦称快”“圣陶可谓同志矣”一类的记载。即使是很个人化的东西,宋云彬也往往要和叶圣陶对比,如1949年5月21日“看辩证法四十余页,圣陶已看六十余页矣”,其可爱情状溢出纸笺。另有一个很小的细节不得不提,那就是对于叶先生夫人胡墨林的指称。除了圣陶夫人、墨林的说法之外,他还多次提到“叶师母”,1949年7月23日“二时半,偕同叶师母、叶至美赴八条胡同看房子”,8月8日“叶师母煮火腿冬瓜汤,甚佳”,1950年5月30日“天雨,而总署之大汽车已坏,开小汽车来,叶师母冒雨坐三轮往”。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让编写课本工作合作得十分融洽而有质量。五十岁的宋云彬,写了文章之后还是要请六十岁的叶圣陶看的,1949年4月18日,宋云彬续写《读〈闻一多全集〉》,下午写毕,交叶先生审看,“圣陶详读一过,谓文句有小疵,如‘有着特别的意义’,多一‘着’字。并谓近人犯此病者甚多”;6月24日,“上午为《进步青年》写卷头言,成一千字,殊不佳,以示圣陶,圣陶亦谓不佳”;转过年后的1月27日,“赶编《大学国文》古典文之部,殊紧张。选《四库提要》一则,标点竟有错误,为圣陶发觉,学殖荒落,殊可惧也”。可以想象,“殊可惧也”恐怕不只是对自己学问荒疏的担心,其背后或许隐含着对老师、对学问多多少少的一些敬畏吧。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编审课本既是宋云彬等人的工作,同时也是生活,而对于文字的敬畏和率真的性情,则完整地体现在了教科书编审里。范文澜为历史学家而且具有很高地位,但对于他所领衔编写的在解放区使用过的《中国通史简编》,宋云彬仍持不少异见。1949年5月18日日记写到,“范文澜等所编之《中国通史简编》,经叶蠖生重加删改,备作高中教本。第一册删改完毕,交余审阅。此书观点尚正确,而文句多别扭。费一日之功,将第一册阅览一遍,并加标号。提出意见八项,说明以此书作高中教本,实在勉强之至”。就范文澜的书,宋云彬下了很多功夫,1949年7月27日,“范文澜主编之《中国通史简编》,经叶蠖生重加删改,权作高中本国史课本,交余作最后之校阅。范著叙述无次序,文字亦‘别扭’,再加删节,愈不成话。叙述明代与南洋交通情况,所举沙瑶、文郎马神、苏禄诸国,直钞《明史》,不注明今为何地,教员讲解时必感困难”,他还提了一个“尤可笑者”,即编者将蒋平阶《东林始末》中“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里“反之”,“译为‘反对’,遂成笑柄”,这个错未必是范文澜的,所以后面又说“范氏颇读古书,不至有此误会,可知此书实未经范氏细心校阅也”。为慎重起见,宋先生还于次日“致范文澜函,举《通史简编》种种错误与缺点告之”。
宋云彬审范文澜书,再四提出问题,当然并不是跟他过不去。宋氏于古史精研,指摘之处绝非无中生有。1950年11月3日,陶大镛送来《新建设》第二期,里面有他熟识的侯外庐论文《魏晋玄学的社会意义——党性》,他也同样不客气地指出,“从题目到文章全部不通,真所谓不知所云。然亦浪得大名,俨然学者,真令人气破肚皮矣”。当时审读的来自解放区的课本,若以叶圣陶、宋云彬等人的眼光来看,真正过得去的恐怕不多。1949年8月18日,“看宣传部所编之《初中中国近代史》下册稿,不特辞句不通,且凌乱无次序,原欲稍加修改,用作教本,今若此,只得敬谢不敏矣”;而第二天,“审阅新华书店出版之《中等国文》第三册,选有徐特立文章两篇,均不知所云,非特文句不通,语意亦不连贯”;1950年2月11日,“审阅新华书店《初中国文》第六册,谬误百出,简直不成东西,非常愤慨”。叶圣陶和宋云彬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生气之余,“圣陶拟订中学课程标准,其中有一项说明:‘一个词儿用得合适不合适,一个虚字该补上还是该删掉,都是内容问题,不是“文字”问题。表达内容既然以语言为工具,惟有语言运用得的当,才能表达得的当。’”叶圣陶的话确有道理,以至于宋云彬大加感叹,“至哉言乎!圣陶殆有为而发欤?”
叶、宋等人如此要求自己,同样也如此要求后来参加的一些新人。1950年2月22日日记,“编课本实大难事,人手少,仅一蒋仲仁可帮忙,余均大小庸才,奈何奈何”;3月13日的日记又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一组里能真正作编辑工作者,除余外只仲仁、文叔,而文叔兼第四处工作,不能专心修改课文,杜子劲等皆庸才耳,奈何奈何”;他在6月21日甚至向叶圣陶建言,“看田世英地理稿本,文字多‘别扭’。我处宜添聘一文字通顺,能专事修改原稿者。以此意告之圣陶,圣陶亦以为然,其奈不易物色何”。这里面说到的杜子劲,在后来还被屡次提及,1950年6月12日日记,“《语文课本》第三册编辑工作进行极迟缓,杜子劲尤懈怠,殊为可恨”;6月15日日记,“注释《语文课本》,发见杜子劲修改《撞车》一课,反将原文改坏了,点金成铁,此之谓也”;7月22日,“《语文课本》第二册快编完,杜子劲、马祖武等皆不会注释,每篇非亲自动手修改不可,令人气闷”。在7月18日那天,宋云彬终至“忍无可忍”,“上午处务会议,余提出杜子劲工作懈怠,请予批评。会散后,杜表示接受批评”。宋先生与杜子劲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他对杜子劲的批评完全源于具体的工作,这背后隐含有传统知识分子的严谨与真诚,但更多的其实是来自课本编写的责任和压力。1950年10月第一次修订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的封底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杜子劲”三个字,他就署在“宋云彬”下面。
过去的课本传统在课本审读上是问题,新人的培养和成长在课本审读上也是问题,除此而外,来自身边领导或朋友的相互理解当然也是问题。胡愈之与宋云彬老早就是朋友了,1949年时一起到了出版总署,不太一样的是胡做了署长,而宋云彬却成了下级,不过这没有影响他对署长发表不同的看法。1949年8月23日下午,宋云彬和叶圣陶等人到东总布胡同出席座谈会,商量出版一个像开明《月报》那样的综合性刊物《新华月报》,宋云彬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愈之长于计画,短于甄别文章好坏,所约请之编辑人员,大抵皆八股青年,余敢预言,决编不出像样的刊物来也”。讲一个和课本编写关系不大的刊物时如此,当谈到课本编写时,宋先生就表现得不那么客气了。1950年2月7日“下午二时赴总署出席局务会议。愈之以编辑中学教本为极简单容易之事,余反唇相讥,谓编教科书与编《东方杂志》不同,君但知编杂志耳,对于编教科书固不了了也”。5月23日那天,宋云彬接到了总署的会报,里面“愈之谓‘编教科书时间迫促,何以不各人带回去,晚上在家里继续工作’”,宋氏对此颇不以为然,“此公愈来愈颟顸,闻其语如见其人也。一笑”。关于加班的事儿,1950年1月31日傅彬然也曾提倡,“彬然谓他所领导之第四处,工作不够紧张,以视东北各工厂,有增加工作至每日十数小时者,颇感惭愧云云。呜呼,此果由衷之言邪?编辑工作万万不能与体力劳动者比。每日七小时,并所谓学习一小时,谁不感疲惫者!他日彼如再发此种妄言,余必请其躬自一试,以作表率也”。
宋先生当然不只是批评别人,除了他一直敬仰的叶圣陶之外,新加入的课本编审者也不乏敬佩的人,其中最有名者为王泗原。宋云彬为学眼界颇高,然而对王泗原却始终青眼有加。他在1950年5月16日、7月25日、8月9日数次提到王泗原,并在8月9日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教育部王泗原送还《语文课本》第二册原稿,校阅极仔细,可佩可佩”。即使是课本编写之外的事,宋云彬也不吝赞美,11月4日第一处“讨论抗美援朝事”,“语文组王泗原发言甚精彩”;宋于1951年1月4日的日记中更写道,“王君于语文学颇有根柢,余不及也”。不只是宋云彬赏识王泗原,叶圣陶先生也屡次表达过招致之意。1950年5月20日是星期六,王泗原来见叶圣陶,“告以所提对于初中语文课本之意见,甚周至”,王泗原本想到编审局任事,可是教育部先谈妥了而未成,叶圣陶“今见其能力颇强,深感失之交臂。然彼此固可经常联络也”,其惋惜之情溢于言表;王泗原于古典文献特别是楚辞研究颇深,叶圣陶于此也敬佩有加,1950年12月19日日记“灯下,观王泗原君之《离骚的语文》原稿。此君于形声义均钻研至深,所得结论皆确切,甚可佩”。不过叶先生失之交臂的遗憾持续不到一年,很快他与王泗原一起合作共事的契机便出现了——王泗原调入了人教社。
宋云彬品评教科书编审人物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隆重正式的一次,那是1950年11月30日的事儿了。此前为了编写教科书,宋云彬得了严重的腰痛。这一天,“腰痛已愈十之七八,准时到社办公。与圣陶商定编审、编辑、助理编辑及练习编辑名单”,给人定个位置,那当然少不得品评讲论的功夫。这里的说道,宋先生的日记里没有提。不过,它一定不是李白说的那种“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拿他本人来说,一周后的12月7日,“《初中语文》课本第六册稿今日发排”,课本终于阶段性地完成了。而上边那个名单的确定,既是对编审课本人的功劳总结,也是新的成长基础和未来空间的定位。
1949年2月28日,叶圣陶、宋云彬一行27人北上,只是在启程的次日,叶圣陶即有感而赋诗曰:“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两天后,宋云彬和诗已成,言曰“蒙叟寓言知北游,纵无风雨亦同舟。大军应作渡江计,国是岂容筑室谋。好向人民勤学习,更将真理细追求。此行合有新收获,顽钝如余只自羞。”叶、宋等人,无论是“篑土为山、涓泉归海”,还是“真理细追求”,都在此后的课本编审工作里得到了生动、完美的诠释。1949年10月5日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说,“截至8月底止,出版了小学教科书7种29册,中学教科书9种16册,还在排印的中学教科书11种,其中有一部分现在业已出版”。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编审新中国教科书的开始,在经历了2年多国营和民营教材暂时共同流通的局面后,1952年5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出版总署联合下发《关于1952年秋季中小学教科书的决定》,所附中小学教科用书表中的45种95册教材均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教科书最终实现了国家统一编审、印行和发售。
翻开那些泛黄的几十年前的老课本,上面“宋云彬、朱文叔、蒋仲仁、胡墨林……”等一个个已经远去了的名字依然清晰可辨。而打开宋云彬的日记,他们的形象则仍是那么生动鲜活,是他们,让教材,与新中国一起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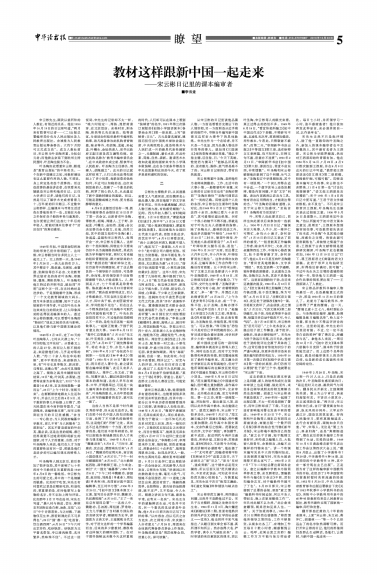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