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雄主义被放逐的消费时代,张品成的长篇小说《我的军团我的兵》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通向儿童战争小说叙事的内在性,展示了儿童文学红色书写的另一种可能。
在作品中,张品成自觉地承继了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传统。这一点集中体现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的如下三个特质:对英雄主义主题思想的选取、对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崇高美学的追求。不过,张品成显然不是一味地继承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传统,而是试图在新世纪的历史语境下对其进行新解。因此,这部长篇虽然意在讲述红军的长征故事,不可避免地萦绕着死伤气息,但它打动读者且极具震撼力的则是今日世界上严重丧失的东西——庄严、大爱、友谊。特别是这部长篇小说意在以继承革命历史叙事的方式提醒今日儿童珍惜那些已被视为习以为常的东西——饱食、安居、生命、和平,进而以文学的形式应对今日儿童精神缺钙的现象,并助力于塑造儿童坚硬的骨骼、顽强的性格、大爱的心灵。
然而,在《我的军团我的兵》中,张品成对革命历史叙事传统的自觉继承与新解并不必然获得意义的内在性,因为,只有意义内在化于叙事世界,意义的内在性才会实现。这样一来,战争故事的别致的讲述方式、庄谐杂糅的叙述语调、饱满的“少年红军”形象的塑造、少年心理的成长过程和战争本性之间的内在关系,一并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战争叙事的内在性。
的确,在故事讲述方式上,这部长篇一如既往地选取少年视角来讲述红军的革命历史故事。但在少年视角下,以往革命历史小说中重点渲染的正面战场的残酷死伤情景被放置在小说背后,借用小说的叙述者所说:“樊天九和欧前响他们是普通士兵,当然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这部长篇小说的开篇一句——“过了泸定桥,交火的事就少了”——自始就确立了它的战争叙事的“非战争性”。即便这部小说不得不描写战争的死伤,也是以或隐蔽或节制的方式进行侧面描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小说紧紧围绕少年主人公樊天九在在战争中的所见所感来展开情节。这些情节符合少年的心理,传递了少年独有的童真童趣。
与讲述方式密切相关的是叙述语调。如果读者足够细心,还会发现这部长篇小说中的庄谐杂糅的叙事语调,由此确证了张品成的儿童战争小说的独特叙事美学。“庄”意指作家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讲述正面事物时的庄严语调,即对革命历史叙事传统的一种历史性接受;“谐”意指作家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讲述中间事物时的诙谐语调,即对革命历史叙事传统的一种现实性新解。如果说庄严的语调是对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崇高美学的回归,那么诙谐的语调则是对革命历史小说中的观念的新解。
当然,不管讲述方式多么富有新意,叙述语调如何特别,儿童战争小说的成功叙事都不能缺失对饱满的少年人物形象的塑造。回望以往讲述少年红军的成长故事的革命历史小说,不难发现,“少年红军”形象常常被单面化,仿佛生来就是一个因苦难而负有某种神圣使命的、意志非凡的英雄形象。而在《我的军团我的兵》中,少年主人公樊天九虽然生来就携带一部父母双亡的苦难史,但这部长篇小说非但未重复以往革命历史小说的复仇史,反而似乎隐去了这一点,而始终将樊天九当作一位成长中的少年来对待。于是,樊天九自成为“少年红军”后,始终保有了少年形象的丰富性:既有红军战士的精神气质,也有天下少年共有的儿童天性,还有这个少年本身的个性特征。而且,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樊天九不是一个人在成长,而是被适时地“配备”了另一位同伴——性格迥异的少年欧前响,与其形成既对照、又互补的关系。与此同时,这部长篇小说还打破了少年的专职导师制,为天九设计了成长路途上的不同出身、身份的精神导师们。尽管导师的背后都有一个光辉形象,但无不是有弱点的肉身化的人。
不过,这部长篇小说如果只是将“少年红军”的塑造放置于红军的“后方”,而不呈现战争对儿童的身心伤害,就不能说有根本性的突破。其实,儿童战争小说叙事的内在性最终取决于能否在战争本性中塑造人物形象。所以,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除了上述文学性探索,张品成将“少年红军”的成长心理与战争本性结合起来,进而塑造出处于变化中的“少年红军”的成长心理。这一点,特别令人叫绝。为了体味红军长征的艰难险阻而多次重走长征路的张品成认为,战争“不仅有肉体的伤亡,还有常人不可能经历的精神磨难。那些经历,比死亡还要痛苦”。所以,《我的军团我的兵》的特别之处在于呈现那些看不见的心理煎熬,以及表现战争如何带给“少年红军”生命考验和精神磨难。特别是,这部长篇小说重点讲述看不见的战争的心理煎熬如何参与并构成儿童成长的心路历程。这样,如果说这部长篇小说的前半部分主要将儿童性和红军精神融合在一起,那么它的后半部分则将战争的本性和儿童的人性相结合而带出这部小说的高潮。
至此,这部长篇小说产生了“少年红军”和红军精神以及战争本性缠绕在一起的神奇、微妙和变化莫测的景象——这种景象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独特的儿童战争叙事的内在性,也使儿童文学红色书写实现了另一种可能。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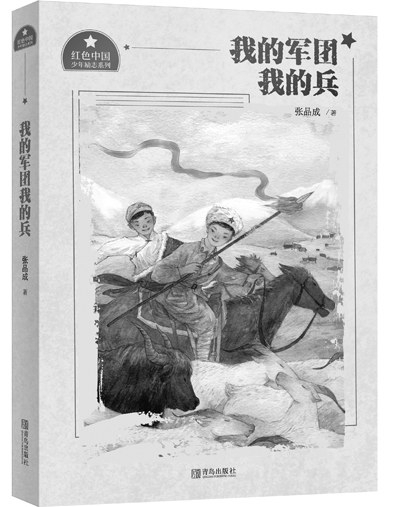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