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丁美洲的精神》里,霍华德·威亚尔达断言,独立后的拉丁美洲罹患了“精神分裂症”。的确,它是大病难愈之人,一只手握着独立自由的新生,另一只手却被旧日枷锁牢牢铐住。
1815年,委内瑞拉独立运动受挫,日后被尊为“解放者”的玻利瓦尔逃亡加勒比海岛。他反思美洲的历史与现实,寻觅革命失败的症结。在那一年发表的《牙买加来信》里,玻利瓦尔犀利地将矛头指向了宗主国。
霍华德·威亚尔达笔下,伊比利亚史和拉丁美洲史是不可分割的,前者无缝融入后者。正因如此,玻利瓦尔的声音振聋发聩。《牙买加来信》不仅是一篇反抗殖民的檄文,也是一本剖析美洲的报告。伊比利亚困住拉丁美洲的第一道枷锁,就是经济剥削。哥伦布远航之后,征服者与殖民者怀揣着一夜暴富的梦想,前往美洲寻找“黄金国”。他们没能发现传说中的宝藏,却意外觅得不少银矿。无数印第安人被皮鞭驱使着,加入繁重的采矿劳动。他们在黑暗巷道的血泪,化作了一船又一船驶往西班牙的白银。三个世纪里,超过一亿公斤白银跨过大西洋,抵达了伊比利亚半岛的港口。有人说,西班牙就像一张嘴,填进食物加以咀嚼,仅为把它送到别的器官,除了经过的气味和偶尔粘在牙齿上的碎屑,什么都没有留下。的确,坐拥财富的西班牙将白银挥霍一空,养肥了欧洲,但西班牙人至少尝到了金银的味道,美洲人却只能望之兴叹。不止如此,正像玻利瓦尔所说,西班牙人还垄断了殖民地贸易,各地只能向宗主国高价购买制成品,而不能私下互通有无。食盐、火药、纸张、墨水都在专卖清单之列,足见控制之细密。
单一的出口模式与粗暴的垂直管理相伴而生,葡萄牙人在巴西的统治可谓典型案例,红木、蔗糖、黄金、咖啡周期里,殖民地往往集中产出某一种物资,缺乏经济活力。在全球扩张进程中,由于没有财力与精力大肆征伐,葡萄牙人倾向于在沿海建立商站,而非侵入内地。在腹地广阔的巴西,尽管殖民者一度向亚马逊挺进,但绝大多数时间满足于在海岸线上搭设居民点,转运红木和黄金。对于殖民地的建设,统治者漠不关心。拉丁美洲丰富的资源,在伊比利亚的剥削模式之下,无法转化为商业繁荣,借用前辈学者索飒的书名,这正是“丰饶的苦难”。直至20世纪中叶,单一产品出口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仍困扰着拉丁美洲,劳尔·普雷维什称之为“依附性”,而它的始作俑者正是伊比利亚模式。
制造苦难的,不惟严苛管理,还有移植自伊比利亚半岛的社会阶层。历史上,西班牙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斗争的前沿阵地。在收复失地运动里,立下功勋的将领和士兵获得大片土地,成为国内新贵。征服美洲之际,统治者沿用此法,吸引游民和穷人远渡重洋。在阿兹特克和印加故土,许多双手沾满鲜血的“先遣官”,凭借军功一跃成为大地主。他们及后代经营着大庄园和大种植园,终日以斗鸡、比武和举办奢华宴会为乐。宗主国派往殖民地的总督和大小官员是庄园的座上宾。在遥远之地,总督对国王命令奉行“服从但不执行”的原则,过着土皇帝的生活。耕种和采矿的重压,通过劳役派遣制,施加在印第安人身上。当大量印第安人死于繁重劳作和欧洲疫病,官员和庄园主引入了非洲奴隶。奴隶生产的财富,先由殖民地的掌权者层层盘剥,继而运往旧大陆。与宗主国风气如出一辙,美洲的上流社会贪图享乐,迅速将财富换成了奢侈品,民众常年生活在贫困之中。时至今日,贫富悬殊仍是拉丁美洲的关键词,良田千里的庄园与脏水横流的贫民窟同在一城,形成鲜明对比。
无论在西属美洲或巴西,天主教都是殖民者的一大遗产。对天主教的倚重,源于伊比利亚独特的历史进程,在与穆斯林王朝长达几个世纪的斗争里,宗教被用作笼络人心的精神武器。征服美洲,是用剑与十字架完成的。传播福音是大航海的最初动力和说辞,印第安人的原始信仰被禁止,天主教会渗入社会的每个角落。在殖民地,从生老病死到赋税教育,教会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教亲关系则是串联社会的关键纽带,大庄园主和官员互为对方子女的教父教母,构成了更牢固的统治阶层。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教会是一副无形枷锁,裙带关系盛行,阻断了穷人的上升通道,它宣扬的神学限制了知识传播和思想交融,使得独立以前的拉丁美洲文盲率奇高,在一些小市镇,甚至找不出十个能够识文断字的人。不容忽视的是,教会拥有令人咋舌的财富。在独立运动之前,它占据了拉丁美洲三分之一的土地,一边收取庄园和牧场的捐赠,一边借助放贷生财。在墨西哥,教会在独立后的半个世纪仍是凌驾于世俗之上的权威,共和国不得不打响一场战争来摆脱它的束缚。
墨西哥的教会顽疾,只是独立后拉丁美洲困境的一个缩影。抛开经济、社会与宗教的桎梏,单是如何统治国家,就曾让“解放者”玻利瓦尔忧心不已。手握大庄园和大种植园的克里奥尔人,对锦衣玉食并不陌生,对治国理政却无甚经验。宗主国放任他们穷奢极欲,却紧紧掌控着总督等高级职位的任免权。玻利瓦尔说道:“美洲人突然站了起来,事先一无所知。最成问题的是,他们没有掌管公共事务的实践,难以在世界舞台上掌握立法者、律师、司库、外交官、将军等以及其他高级或次一级的官职,而这些官职是一个有组织的国家通常必设的……一个刚刚挣脱锁链的人民在进入自由的领域时,不会像伊卡洛斯那样,翅膀烧坏、堕入深渊吗?”果然,拉丁美洲没有逃过伊卡洛斯的命运,在奔向自由的旅程里,伊比利亚枷锁牵绊了它的脚步。新生国家不能填补宗主国遗留的政治真空,也无力对抗虎视眈眈的英美法诸强,更没有办法敉平国内多如牛毛的派系。在许多国家,独立与共和成了一出你争我夺的闹剧,人们只得求助于某个强权人物来稳定局面,“考迪罗”应运而生。
“考迪罗”原意是“领袖、头目”,在拉丁美洲成为一个特殊的政治名词,他们在独立战争登上历史舞台,独揽一方大权,引领了过渡时代的社会走向。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太过激烈的社会变革会带来不可预测的危险。故而,欠缺政治经验的拉丁美洲选择妥协,将国家蓝图交给保守的权威。大庄园主与天主教会是“考迪罗”的坚实后盾,他们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底层民众也不乏“考迪罗”的拥护者,他们希望强权人物革除弊病、换来新生。在风靡全球的文学作品里,“考迪罗”往往是墨西哥圣塔·安纳那样的乱世枭雄,或是阿根廷罗萨斯那样的暴虐屠夫,事实并非如此。戴着现代化面具的“考迪罗”不在少数,他们修建铁路、兴办教育,引入外资、奠基工业,确实掀起了新风气。进入20世纪,与“考迪罗”一脉相承的军政府唱起了主角,成为新旧之间的调解者,一面推进着自由贸易,一面镇压着进步人士,在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的现代化事业了烙下了深刻痕迹。
美墨边境以南的广袤土地上,独立降临已近二百年。然而,曾经物产丰饶的拉丁美洲,依旧在穷困与动荡里苦苦挣扎。西班牙与葡萄牙统治时代早已远去,但它们留下了有形和无形的枷锁,仍在桎梏着昔日殖民地。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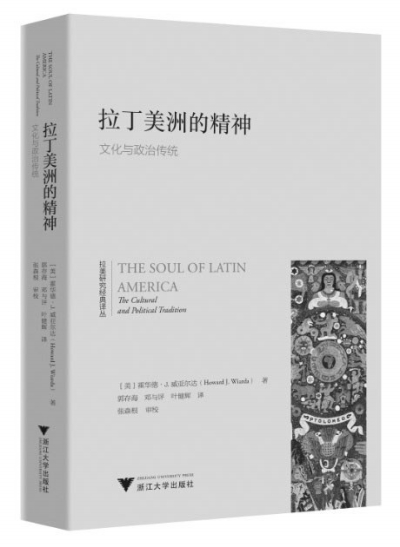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