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一个消费主义盛行乃至猖獗的时代,饮水思源便显得有些难能可贵了。纯粹的消费是不问源头的,重要的是快乐和享受;而文化则不同,它总是有传统的,有传统就有源头。饮水思源既有感恩的意思,又有探寻揭秘的意思,这与消费主义背道而驰。设若文化与消费合二为一,文化的作用与意义也就几乎消失殆尽了。因此,文化与消费不同,所谓消费文化或文化消费终究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
我从事西方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三十余年了,在心头一直有一个萦绕不去的问题:西方文学的源头在哪里?追根究底或者就是学者的本性。现当代西方文学愈蔚为大观,追溯其源头的意义也就愈为重要;寻本探源,对源头的探究也更有利于认识当今西方文学的特质和精神。所谓“源”和“流”总是裹挟在一起、彼此难分的,没有“源”就没有“流”,而有“流”就必有“源”。
因此,便有了“西方文学源头考辨”的说法。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就是将文学的发生发展比作江河的源头和流变。二者的可比性似乎是无可置疑的:任何文学现象无论多么繁荣复杂均有其源头,正如任何江河湖海无论多么汹涌宽阔必有其发源地一样。然而,考察文学的源头正如考察江河湖海的源头一样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到源头去饮水”,就是去饮用最纯正的水,最洁净的水,最没有杂质的水,而饮用源头的水的前提是,我们必须首先寻找到源头。
说到江河大川,对于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江河就是长江黄河了。它们都属于中国的母亲河,世世代代孕育着江河两岸成千上万的人民。长江黄河的源头在哪里?现在人们通常认为,长江的发源地在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格拉丹冬峰西南侧。黄河的源头则在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这里所说的源头均只是大体位置而已,并没有确切的源头发生点。长江黄河的第一滴水出现在哪里?什么时间出现的?这类问题其实是很难考察的,甚至是根本没法考察的。我们从“流”追溯“源”,最后会不知所终;我们从“源”顺“流”而下,而“源”却只能有大体的位置。大江大河如此,小江支流就更是如此了。
我们具体来说说汾河吧。汾河为黄河在山西境内的支流,亦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是山西最大的河流,被山西人称为母亲河,对山西省的历史文化影响深远。汾河全长713公里,流域面积39721平方公里。然而,它的源头在哪里?有关汾河源头的最早记载出自《山海经》:“管涔之山,汾水出焉。”以后《水经注》亦云:“汾水出太原汾阳北管涔山。”不过,汾河源头具体在管涔山什么位置,史书的记载语焉不详。1995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标明了汾河的具体发源地:山西省宁武县东寨镇西雷鸣寺泉。此处竖有“汾源灵沼”石碑一尊,被视为汾河之正源。不过,《山西河流》一书对汾河源头的界定应该更为完整:“汾河发源于宁武县东寨镇管涔山脉楼子山下水母洞,和周围的龙眼泉、象顶石支流汇流成河。”如此一来,汾河的源头就不只是在一个点上,而是由多点汇合而成,汾河的源头也就变得复杂起来。稍后出版的《汾河志》并不认同这种“正源”的说法:“其实汾河真正的源头还应从正源雷鸣寺泉向北向西上溯16公里,至岔山乡宋家崖村之西北与五寨县交界处。”果然,现代的科技手段似乎证实了这一点。2011年山西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经过勘查,最后确定从神池县延伸过来的一条沟道为汾河源头,该地处于神池县太平庄乡西岭村,位于雷鸣寺泉上游。“一条沟道”有多长?沟道如何可以成为源头?沟道里的水又从何而来?这些笼统而模糊的说法似乎离汾河源头的说法相去甚远。总之,有关汾河源头的诸种说法大抵如此。
二
现在我们来说说西方(欧洲)文学或文化的源头。关于这个源头,我们都知道所谓“两希说”,即希腊和希伯来文学是西方文学的源头。由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在导论中写道:“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学是欧洲文学的两大源头,文学史上称之为‘两希’的传统。它们在欧洲文学漫长的历史流变过程中呈矛盾冲突与互补融合之势,欧洲近代文学的人文观念和艺术精神的基本内核,主要来自于这两大传统。”“两希说”已经成为外国文学史中的一种传统了。这种说法相当于说汾河的源头在“山西省宁武县东寨镇西雷鸣寺泉”,属于“正源”说。然而,这个“说法”的源头在哪里?这也是需要梳理和考证的。
茅盾在1930年出版的《西洋文学通论》中提及西方文艺思潮发生和发展的“两个H”之说。所谓“两个H”指的是Hebrism(希伯来主义)和Helenism(希腊主义)。“尤其是‘二希’,很被重视为欧洲文艺史的两大动脉。”茅盾此说是自己的独创,还是援引他说?茅盾先生没有注明。但茅盾仅仅只是提出了观点,并没有提供证据或进行论证,且茅盾也确非专门研究西方文学源头的学者,因此茅盾的观点很可能是援引自其他学者。
这样一来,19世纪英国著名学者马修·阿诺德(1822—1888)的观点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了。马修·阿诺德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最重要的批评家。他一直被视为英美知识思想传统或者说主流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重要著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出版于1869年。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阿诺德明确指出:“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这两者之间的影响推动着我们的世界。在一个时期,感受到它们中的这一个吸引力大些,在另一个时期,又感到另一个的吸引力大些;虽说从来不曾,但却应当在它们之间保持适当和幸福的平衡。”阿诺德的这一关于西方文化源头的说法影响久远。因此,这一说法很可能影响到中国学者,然后又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茅盾。我以为,这种推断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然,也有西方学者指出,西方文学的源头还应加上哥特文学或文化:“欧洲文明的主流发源于古典文化和希伯来文化时代,随后又因哥特人的入侵而加入第三个重要支流。”哥特人被认为是耳尔曼部落中最凶暴、最活跃的一支。哥特人的主要特点是躁动不安和激情好动。他们没有在书面文学、艺术形式以及文化装饰品方面做出贡献,但是,“他们对个人自由理想的强调、对怪诞事物的迷恋、对妇女的神秘态度以及个人对首领的忠诚等观念,在创造中世纪和后来的欧洲生活形态过程中也颇有影响力”。这便等于说汾河源头虽然发源于“宁武县东寨镇西雷鸣寺泉”,但是,还应加上“周围的龙眼泉、象顶石支流”等才算得上完整全面。不过,比较而言,作为西方文学的源头,哥特文学出现较晚,希伯来文化则有些间接,作为西方文学最直接、最古老的源头应当就是古希腊文学了。
古希腊文学是西方文学的开端,铸就了西方文学的精神品格和基本走向。琼·肯尼·威廉姆斯在《古代希腊帝国》一书中指出:“他们(古希腊人)的神话,经荷马传诵,成为西方文学的源泉。”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近代世界就是希腊和罗马世界的延续。现代西方人是罗马人的孙辈,是希腊人的重孙。如果没有希腊-罗马文化,西方的现代文明将是不可想象的。西方文学的源头在希腊,希腊文学的源头为荷马。荷马是“当时唯一写作的人”,但他的写作并非只是一种消遣,有关特洛伊的战争也并非只是传说,甚至荷马根本就没有“写作”,他只是“吟唱”,当然还有整理或者改编。荷马与西方文学源头究竟为何种关系?如何能领略西方文学的精髓或精神?到古希腊文学那里去,大概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或理想之路,并且应该是我们最先的选择。如有可能,我们就应该到源头去饮水。这句话包含两个意思:一是若想品味西方文学,就得首先品味古希腊文学;二是若想真正品味希腊文学,就得去阅读希腊原著。但是,设若做到了以上两点,我们是否就饮到了“源头活水”呢?
三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西方文学的源头并非一泓固定不变的“死水”,等待着我们随时去“豪饮”。一旦我们诚心去追寻西方文学的源头时,我们发现这个源头其实并不确定,也并非可以轻易涉足其间。对于古希腊文学,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些断片或片面性的传说。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文学作品,我们所掌握的约有百分之二十,而越往前我们所掌握的就越少。英国古希腊文学研究专家吉尔伯特·默雷说:“每一种文学作品,当人们想起要保存下来的时候,实际上大部分早已毁弃。”古代人最初创作文学作品时并没有想到要保存,而之所以想到保存,则是因为许多文学作品已经永久消失,已无法保存了。我们保存下来的文学作品大都经过书写和印刷而定型,而文明之前的野蛮人的文学作品的保存却只能通过记忆和传承,在今天看来,这种保存方式自然是不可能精确可靠的。而文学的真正源头显然来自后者,而非前者。前者在经过文字的记载和传播后,已经从“源”变成了“流”,且蔚为大观。
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中写道:“希腊古代文学最早者为宗教颂歌,今已不存。”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18年出版,迄今已逾百年。百年来有关希腊古代宗教颂歌的材料已有零星出现,并非完全不存。不过,正因为这种宗教颂歌不复存在或难以寻觅,因此我们便以为希腊神话的最重要特征是“神人同形同性”。其实,所谓“神人同形同性”只能概括以荷马为代表的世俗文学,真正的宗教文学恐怕并非如此。在以荷马为代表的世俗文学存在之前,极有可能还存在着一种宗教文学,譬如俄尔甫斯和他的亲属缪萨埃阿斯创作的文学,据说古代许多宗教诗都是他们创作的。俄尔甫斯与神秘宗教及其仪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刘小枫在《俄耳甫斯教辑语》一书前言中写道:“在古希腊的经典作品中,我们的确经常见到这个诗人的名,据说,他辈分比荷马还高。可是,俄耳甫斯基本上没有完整诗篇传下来,如今能见到的,大多是古希腊经典作家的文字中说到他的地方,而且都是一些片段而已。20世纪初,德国的古典语文学家OttoKern将古希腊作品中所有提到俄耳甫斯的地方辑出来,编成‘俄耳甫斯辑语’,仍然见不到什么完整的诗章。从而,俄耳甫斯其人始终不过是西方诗人最为古老的魂影,令后世诗人不断追忆的亡灵——如诗人里尔克在《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中所唱的。品达的诗句‘这人是一个魂影之梦’虽未必说的一定就是俄耳甫斯,用在这位历史面目如此模糊的诗人身上却也实在恰如其分。很可能与这位俄耳甫斯相关,古希腊还盛行一种所谓‘俄耳甫斯教’,诗人俄耳甫斯在这个以秘仪为主要特征的宗教中身为神主,据说在古希腊影响最为广泛,其重要意义越来越受当今学人重视——所谓‘俄耳甫斯教祷歌’就是这一宗教传统的见证(今据古典语文学家考订,共存87首,中译见《俄耳甫斯教祷歌》,吴雅凌编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这就意味着,真正作为希腊文学源头的宗教文学我们已经不可知,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世俗文学已经不是真正的西方文学源头。这便等于推翻了传统意义上的汾河源头说,另出新说:“其实汾河真正的源头还应从正源雷鸣寺泉向北向西上溯16公里,至岔山乡宋家崖村之西北与五寨县交界处。”汾河的源头在别处,我们仍然需要另行勘探。
如此看来,真正的西方文学源头,由于没有文字记载下来,现已大多散失,我们已不可知。我们已知的最早的荷马史诗所记载的神话,经过数百年的重复、编辑、改动,已经不可能是真正的源头了。而我们今天通过文字——不论是那种文字,阅读或吟诵的荷马史诗,也已经不可能是当年荷马吟唱的史诗了。即便我们尽可能地将荷马史诗还原,我们也不可能拥有荷马时代的听众,况且,物是人非,时过境迁,吟唱荷马史诗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情境早已不复存在了。没有了古代的听众,荷马史诗还是荷马所讲述的那个故事吗?当代著名学者伊迪丝·汉密尔顿在《希腊精神》一书中指出:“希腊文学和希腊雕塑一样都不尚雕琢,行文素朴、率直,实话实说。如果直译的话,译文往往显得非常直白干瘪……但如果我们不能欣赏直接的译文,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知道希腊人的作品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希腊语和英语非常不一样,希腊语一旦译成了英语,原文的风格就丧失殆尽了。”希腊语与英语如此不同,以至于任何翻译都不可能获得成功。如此一来,英语与中文又如此不同,希腊语与中文反倒可能有更多的相近或相通之处,希腊语一旦译成中文,其原文的风格或者比英译本保留更多?这倒是别有意味的问题。
的确,我们渴望到源头去饮水,我们相信“唯有源头活水来”,但是,真正的源头却并不易发现,或者永远不可能被发现。欧洲文学的源头在哪里?有没有可称为文学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它孕育、培养或启发了往后的所有作品?正如是否存在作为源头的第一滴水,或者说是否有作为“零时”的时间的起点。文学的渊源较之国家、民族、文字的渊源似乎更为幽深错综、扑朔难辨,“沿波讨源”,真“幽”则未必“显”,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我们所饮之水,只不过是稍稍地接近了源头而已。德裔美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认为,从诗歌的角度,我们不如说,历史就是从俄底修斯在法雅西亚国王的宫廷里,倾听他自己的事迹与他遭受的苦难的那一刻开始的。的确,许多人认为,荷马就像《奥德赛》中的那位盲人歌人得摩多科斯(Demodocus)。“游荡在古代希腊各地的人民歌手行吟诗人的诗歌一代代流传下来。这些说唱者走进人们家里,用三角竖琴(cithara)伴奏,歌颂英雄们的功绩,歌颂庇护他们的神以及很久前发生在他们故乡的各种事情。”荷马就是这样一个盲人歌手行吟诗人。史诗《奥德赛》第八卷,俄底修斯漂落到法雅西亚国王阿尔基诺斯(Alcinoos)居住的海岛。国王的女儿瑙西卡(Nausicaa)在海边洗衣服时发现了他,并把他带到王宫。国王设宴招待他,席间请来了这位盲人歌手:
你们再把神妙的歌人
得摩多科斯请来,神明赋予他用歌声
娱悦人的本领,唱出心中的一切启示……
传令官回来,带来了敬爱的歌人,缪斯宠爱他,给他幸福,也给他不幸,
夺去了他的视力,却让他甜美地歌唱。
得摩多科斯歌唱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和俄底修斯的英雄事迹,俄底修斯听后不禁泪流满面。当俄底修斯的生活故事变成了他自身之外的东西,成为了所有人看与听的“对象”时,历史也就从这里开始了。因为俄底修斯的故事是以诗歌的形式讲述的,因此它就是诗歌的开始,即诗之源。于是,西方历史从这里开始,西方文学从这里发源。如此看来,我们或许可以说,俄底修斯在法雅西亚王宫里倾听说唱艺人得摩多科斯讲述自己的故事大概便是西方文学的源头了。至于说到汾河水的源头,“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地流过我的小村旁”。尽管有关汾河的源头众说纷纭,但我们还是宁愿相信它的源头就在“宁武县东寨镇管涔山脉楼子山下水母洞”,因为这里包含的文化底蕴深厚:既有史书记载,又有民间传说,还有神话故事。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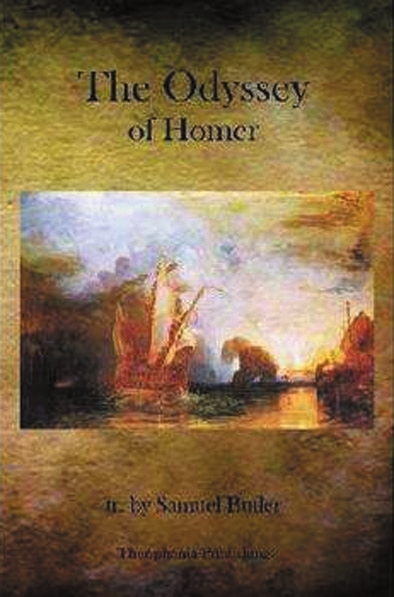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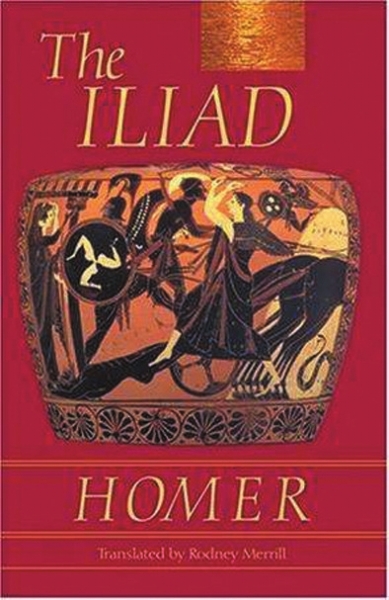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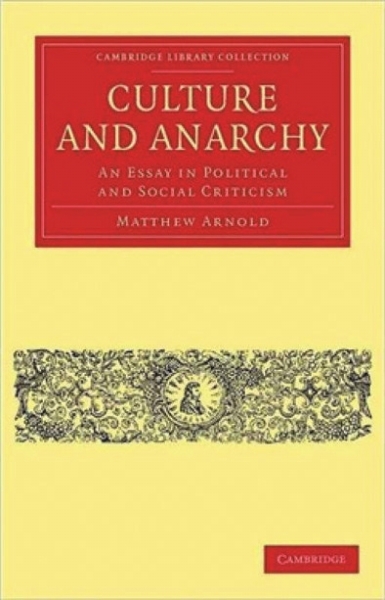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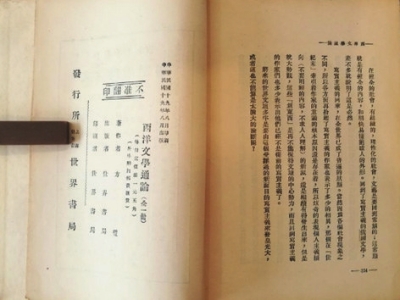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