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始终激荡着两股相互碰撞的潮流,那就是西方文化思想的逐渐传入中国,所谓“西学东渐”;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也逐渐走向世界,所谓“中学西渐”。在这交流之中,翻译成为不可或缺的枢纽工作。我们看晚近的翻译史上,由西书中译者可说相当多,例如严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严译名著”影响到几代的中国人;而单就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有朱生豪、梁实秋、孙大雨、卞之琳等名家卓越的译品;但若就中书西译方面就显得贫乏许多,但后者的意义显然更来得重要些,它是一种文化的输出工作。而要能担当此重任者,其中西文化的根底要极其深厚,而非只是语言能力足够就行,因此辜鸿铭就曾被视为近代中学西渐的第一人,而在他之后,也仅有林语堂可以当之。
辜鸿铭这位满清遗老在一九二八年风雨飘摇中死去,他的辫子、他的守旧,逐渐为人所淡忘;但他所译的《论语》《中庸》被介绍到西方去,再加上他的西文著作,曾引起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及举世公认的文评家勃兰兑斯的重视。而林语堂更是没有接受鲁迅的建议去翻译一些英国名著;他反而怀抱着“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雄心壮志,做起中书西译的工作,他早年曾想把《红楼梦》译成英文,但后来考虑再三,觉得它距离现实太远,因此他借鉴了《红楼梦》的艺术形式,用英文写出了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它曾是诺贝尔文学奖候选的作品。但到了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林语堂终究还是完成了耗时十余年的《红楼梦》节译本,惜未能出版[按:据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宋丹博士表示林语堂英文打字稿,现存于日本某家市立图书馆,林语堂将《红楼梦》的书名译为《The Red ChamberDream》。书名下印着“ANovelofaChineseFamily”(一部中国家族的小说)。原稿共859页,包括林语堂的解说、序章以及作为主体的六十四章和终章,是对《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的编译。一九八四年有日本佐藤亮一根据林语堂的英译本译成日译本。而之后他又以英文出版了《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全面向外面人介绍儒家及老庄的思想,在在引起国际上的关注。当然在译书之前,林语堂以英文撰写《吾国吾民》与《生活的艺术》,成为欧美畅销书排行榜的年度冠军。《吾国吾民》与《生活的艺术》成为当时西方社会眺望中国的一扇窗口,林语堂扮演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这个角色,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它成为林语堂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贡献。
其实早辜鸿铭二十年,早林语堂五十年,就有人在做这样的文化输出的工作,他应该是真正的中学西渐的第一人,他就是集翻译家、西文作家、诗人和文化使者于一身的陈季同。
陈季同(1852—1907),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同治六年(1867),他十六岁时考入福建船政局附设的求是堂艺局前学堂读书。学堂的教师多为法国人,用法语讲课,所用的教材也是法文书,因此陈季同在此打下了扎实的法文基础。光绪元年(1875)年初,船政第一届学生毕业。陈季同与魏瀚、刘步蟾、林泰曾等人,以“在学堂多年,西学最优”,被船政局录用。同年三月随法人日意格赴欧洲采购机器,游历英、法、德、奥四国。一年后返国,光绪三年(1877)三月三十日,福建船政局选派三十五名学生从福州启程赴欧洲学习,其中有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严复、马建忠、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萨镇冰等人。而陈季同在这次赴欧时的身份,已提升为文案,远较这批留学生高出许多。到法国后,陈季同进入法国政治学堂及法律学堂,学习公法律例。光绪四年(1878)陈季同充当中国首任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的法文翻译,郭嵩焘对年轻的陈季同评价甚高,他认为陈“再经历练官场,中外贯通,可胜大任矣”。而陈季同果然没有让郭嵩焘失望,几年之后,他在外交界就崭露头角了。当时亨利·比卢瓦就曾在《北华捷报》上说:“在他之前,中国使馆形同虚设,仅仅充当一个拖着长辫、身穿蓝袍、头皮光光的大人物的住宅。从外交角度坦率地说,因为有了这个年轻翻译的活动,中国才开始在欧洲崭露头角。”
陈季同在欧洲共居住了十六年,他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外交上,更体现在文化上。但可惜的是陈季同的事迹正史不载,辞书不收,就这样被历史遗忘将近一个世纪,直到十几年前才有学者论及。而大陆学者李华川博士更曾远赴法国查遍外交部档案及巴黎的图书馆,以三年的时间写就了《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一书,于二〇〇四年八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全面评价陈季同的开始。据李华川的搜集陈季同有八本法文的著作,分别是:1.《中国人自画像》,2.《中国人的戏剧》,3.《中国故事集》,4.《中国的娱乐》,5.《黄衫客传奇》,6.《巴黎人》,7.《吾国》,8.《英勇的爱》。而这些著作还有英、德、意、西、丹麦等多种文字的译本。李华川认为在清末的文人中,没有人比陈季同在西方更引人注目。
其中《中国人自画像》和《中国的娱乐》两书,在西方影响尤大,甚至都被译为英文,就如同半个世纪后林语堂的《吾国吾民》与《生活的艺术》所产生的影响一般。陈季同写这两本书的目的是要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习俗和娱乐,从而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而对于《中国人的戏剧》一书,李华川认为是中国人以西方方式论述中国戏剧的第一部著作。陈季同触及中西戏剧中一些本质的问题,可说是相当精辟的。他认为中国戏剧是大众化的平民艺术,不是西方那种达官显贵附庸风雅的艺术。在表现方式上,中国戏剧是“虚化”的,能给观众极大的幻想空间,西方戏剧则较为写实。在布景上,中国戏剧非常简单,甚至没有固定的剧场,西方戏剧布景则尽力追求真实,舞台相当豪华,剧院规模很大。
学者钱林森对于陈季同有极为深刻的评价,他说:“作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阐释者,作为中西交通最初的沟通者,陈季同的创造最具价值的部分,不是他直面西方文化时所流露的自豪甚至自夸的情愫,而是他正视西方文化时所拥有的比较意识(如《中国人的戏剧》)、自省意识(如《巴黎人》),以及在移译、阐述、运用中国文学和文化时所表现的现代意识、创造意识和世界眼光(如《中国人的戏剧》《中国故事集》《黄衫客传奇》《英勇的爱》)。他在这方面的尝试和实践,无疑又担承着一个先行者的角色,并取得了成功。……当时法国文坛的领军人物法朗士等,便是通过陈季同和他的作品一窥中国文化的。”
“十几年致力于让欧洲认识中国”的陈季同,却因私债风波把他的成果毁于一旦,使他在外交界的努力化为泡影,他在光绪十七年(1891)以戴罪之身回到中国。后得李鸿章的庇护,在清偿债务后,留在李鸿章幕府中襄助洋务文案。
著名的小说家和翻译家,同时也自称是陈季同的学生的曾朴说:“回国后,李鸿章极器重他,屡次派往外洋,官至总兵。后来因事件忤了鸿章,就退居上海,过他文人浪漫的生活。先生不独长于法文,中文也极有根底,尤其是诗歌;性情质直而热烈,不受羁勒;晚年颇染颓唐色彩,醇酒妇人中,往往作狂草,唱悲歌。”
之后,陈季同在上海首先参与创建中国女学堂,后又创办《求是报》。此时他的主要工作转向中国知识界传播西学。他在《求是报》中翻译、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法律、政治制度,宣传了维新思想,传播了西方的政治、法律观念。他是最早翻译《拿破仑法典》的,因为他精通法国的政治律法,“虽其国之律师学士号称老宿者莫能难”。即便晚年闲居沪上,“西人有词狱,领事不能决,咸取质焉;为发一言或书数语与之,谳无不定。其精于西律之验如此。”
陈季同在当时就很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文化不应故步自封,应该走向世界。他不遗余力地向西方宣传中国文化,其用意在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让中国能够融入世界。他曾向曾朴谈过如何消除中西文化的隔膜和误会,他说:我们首先应确立“不要局限于一国的文学,嚣然自足,该推扩而参加世界的文学”的态度,然后“要参加世界的文学,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须全译出去!要免误会,非把我们文学上相传的习惯改革不可,不但成见要破除,连方式都要变换,以求一致,然要实现这两种主意的总关键,却全在乎多读他们的书。”这种国际的眼光在当时可说是领先于许多知识分子的。当然它对于曾朴走上研究、翻译法国文学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未来的三十余年中,曾朴翻译法国文学作品有五十多种,他也始终未曾忘怀陈季同这位他的法国文学的启蒙老师。
曾朴在给胡适的信中追述陈季同说:“我自从认识了他,天天不断地去请教,他也娓娓不倦地指示我;他指示我文艺复兴的关系,古典和浪漫的区别,自然派、象征派和近代各派自由进展的趋势;古典派中,他教我读拉勃来的《巨人传》,龙沙尔的诗,拉星和莫里哀的悲喜剧,白罗瓦的《诗法》,巴斯卡的《思想》,孟丹尼的小论;浪漫派中,他教我服尔德的历史,卢梭的论文,嚣俄的小说,威尼的诗,大仲马的戏剧,米显雷的历史;自然派里,他教我读弗劳贝、佐拉、莫泊桑的小说,李尔的诗,小仲马的戏剧,泰恩的批评;一直到近代的白伦内甸《文学史》和杜丹、蒲尔善、佛朗士、陆悌的作品;又指点我法译本的意、西、英、德各国的作家名著。”可见其国际视野的眼光,在那个年代诚属不可多得,也难怪曾朴赞其为中国“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
今天,除了一小段和台湾有关的事迹外,大家对陈季同的成就与贡献,可说是茫然无知了。一个百年前杰出的文化使者,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先驱者,是不该再让他湮没无闻的,在他的法文著作陆续翻译出版的今天,也是我们重新认识他的时候了。久违了,陈季同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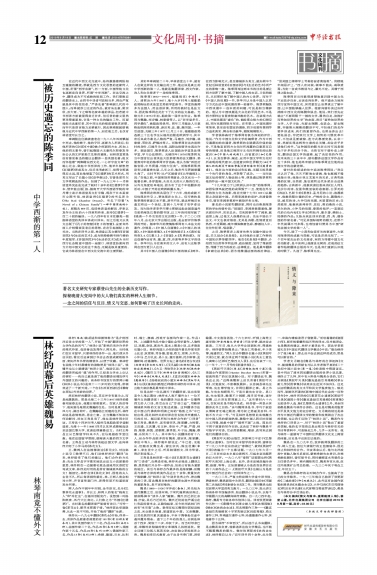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