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曾是我的上帝,我倒在污泥中。”
——兰波《地狱一季》
作为一名小小的诗人,兰波诗歌的中文译者,从前我只是感叹兰波的诗歌之美,语言之神奇,而今,更加关注、更渴望探究的,却是兰波的不幸与不幸的根源。在长期的翻译与创作实践中,我悲哀地发现,与诗歌相伴而生的,不是幸福与荣耀,而是孤独与不幸。而认识到这一点,还有几个人愿意再写诗呢?是的,我现在相信,诗歌与不幸是孪生姐妹、并蒂莲。如兰波在《地狱一季》中说:“不幸是我的上帝,我倒在污泥中。”
何以至此?一言以蔽之:“我是另一个(Jeestunautre)。”这句带有明显“语法错误”的名言,在我看来,触及诗歌艺术的本质,也是打开“通灵者”兰波精神世界的一把金钥匙。
这话出自1871年5月15日,兰波写给导师保罗·德梅尼的书信,兰波在信中说:“因为‘我’是另一个。如果青铜唤醒铜号,这不是它的错。这对我显而易见:我目睹了我思想的孵化:我注视它、倾听它,我拉一下琴弓:交响乐在内心震颤,或跃上舞台。”在信中,兰波断言:“我认为诗人应该是一个通灵者,使自己成为一个通灵者。——必使各种感觉经历长期的、广泛的、有意识的错轨,各种形式的情爱、痛苦和疯狂,诗人才能成为一个通灵者。”人们常说,文学(尤其是诗歌)需要“陌生化”;而如何使诗歌语言变“陌生”,几乎是区分真假诗人的分水岭。不幸的是,现如今,放眼望去,成群结队的“诗人”,无论他们对于世界,或世界对于他们都并不“陌生”,他们的“自我”千篇一律,却误打误撞,在“时代大潮”中成了“著名诗人”,而一旦发现这条通向“荣誉”和“幸福”的“捷径”,他们就再也不想走别的路了。而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除了搞怪,除了拉帮结派,把水搅浑,再也没什么别的“高招”了。兰波早已识破这些人的诡计,将他们比做“comprachicos”(西班牙语),指那些混在小孩儿里进行偷窃的人——“想想看吧,一个人在脸上培植瘊子该是什么样子。”——“这些数以万计的朽骨;他们从古至今堆积着独眼的智慧产品,并大言不惭地自诩为作家!”
然而,真正的“通灵者”,只因感受世界的方式不同,在他们眼里,世界是“另一个”;或者说,精神深处与生俱来的“混沌”、“错轨”(dérèglement),注定将他们的生命,连同诗歌双双引入“未知”的“歧途”,孤单、漂泊的不归路。
总之,语言的“陌生化”非人为制造,而出自天生的“陌生人”(l'étranger)。这人曾出现在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开篇,及加缪的同名小说中。加缪的小说L'étranger通常被译成《局外人》,但其实“局外人”并非活在“局外”——人们同处一国,一个世代,面对同样的现实世界,终因感知生命与世界的方式不同而形同陌路,所以,我赞同翻译家沈志明先生的观点,将l'étranger译成“陌路人”——当“通灵者”寻找自我,从内在生命里与宇宙万物合一,而成为“另一个”,并亲眼见证了异象;于是,熟人变得陌生,此世终成异乡——“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鲁迅先生如是说;而诗人兰波得出更悲惨结论:“我的生活在此是一场真实的噩梦。你们不要想象我会过得好,远非如此。我甚至发现再没有什么生活比我的生活更悲惨了。”“总之,我们的生命是一场苦难,无尽的苦难!我们为何要生存?”这是诗人临终前在信中写给母亲和妹妹的话。我们不妨由此探寻兰波的生命轨迹:如何因“感官”而导致生命的“错轨”,以至于“通体崩裂,散入海洋”——
1870年9月5日,不满16岁的兰波离家出走,从家乡夏尔维勒,独自坐火车闯入巴黎;迎接他的,不是什么文学沙龙,却是警察局的铁栅栏——瞧,这是兰波在警察局里给导师乔治·伊桑巴尔写的求救信:“刚一下火车就被抓住,因为没有一分钱,还欠了13法郎的火车票钱,我被带到了警察局,今天,我在马萨等待判决!——噢!我把希望寄托在您身上,就像寄托在我母亲身上;我一向把您看作我的兄弟:恳请帮助我。”而日后的巴黎文学圈,兰波的身影也只是惊鸿一现,便永远消失——
1873年7月,在与魏尔伦决裂之后,兰波带着身心的伤痛,孤身一人,踏上了漫漫征途,足迹遍布欧、亚、非:从伦敦、比利时、到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意大利,从塞浦路斯(特鲁多斯山)、埃及(开罗)、到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旧名,亚丁)、吉布提,一路上当过雇佣军人、家庭教师、工地监工、摄影师、咖啡商、武器贩子,勘探队员,最终返回马赛港,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时候把我送到码头?”而这绝非浪子回头,却是无望的赤子,渴望重新出发。
当代评论家菲利普·索莱尔斯在《兰波的天赋》中,提到若干年前,有一群激进的法国年轻人,将兰波《彩图集》的手稿寄到法国各大出版社,不出所料,到处碰壁。可想而知,假如在中国做同样的试验(将兰波诗集的中译本署上普通人的名字向各大出版社投稿)结果又会如何?兰波的诗歌与生命是一体;而他之所以陷入孤独绝望,因为“诗歌将不再与行动同步,而应当超前”。兰波这样说,并身体力行:诗歌超前于生命,生命超前于世代。这是诗歌的幸运,抑或诗人的不幸?
有如俄耳普斯深爱着死去的新婚妻子欧利蒂丝,兰波曾对诗歌文字走火入魔,一场“文字炼金术”,足以让读者与作者一并疯狂。创作之时,兰波正如美少年俄耳普斯——可他并不认识冥王哈得斯,也没有跟他达成任何协议,全凭本能的节奏,发明一种足以贯通一切的诗歌文字,何惧回头一望——
当诗人猛一回头,果然看见了另一个世界,可那不是什么好地方,全然没有赏心悦目的美景;那不是别处,正是地狱(引自《地狱一季》)——
在城市里,我的眼前突然呈现出红黑的污泥,仿佛灯光摇晃时,邻家的一面镜子,又像森林中的一片宝藏!太棒了,我喊道,我看见天空一片火海,四面八方,无数珍宝有如万道雷电喷射着火花。
这巨大眩目的灵光,如诗歌本质,让诗人无法承受,随之而来的处境更加悲惨:
狂欢和女人的情谊与我无缘,我甚至没有一个伙伴。我看见自己站在被激怒的人群面前,面对行刑队,我哭泣并请求宽恕,而我的不幸他们无法理解……
最聪明的办法是离开这片大陆,这里,疯狂四处游荡,寻找苦难的人们作为人质。我进入了含的子孙的真正王国。
含(Cham)是黑人祖先,据《旧约》记载,是挪亚的第二个儿子,因为不敬父亲而受到诅咒。而兰波日后果然离开欧洲大陆,进入非洲荒漠,来到“含的子孙”(黑人)当中。对于一个“通灵者”来说,所有这一切,无论创作、生活都是在无意识中发生的,如《醉舟》从出发之日,便“抛开了所有船队”,没有“纤夫引航”,只“沿着沉沉的河水顺流而下”——
进入大海守夜,我接受着风暴的洗礼,
在波浪上舞蹈,比浮漂更轻;据说这浪上常漂来遇难者的尸体,
可一连十夜,我并不留恋灯塔稚嫩的眼睛。
在此,诗歌与生命合一,诗人已不再是自己,在经历了各种形式的情爱、痛苦和疯狂之后,已然化身为“醉舟”并自言自语——
比酸苹果汁流进孩子的嘴里更甜蜜,
绿水浸入我的松木船壳,
洗去我身上的蓝色酒污和呕吐的痕迹,
冲散了铁锚与船舵。
化身醉舟,诗人终成“另一个”——“当他陷入迷狂,终于失去视觉时,却看见了视觉本身!”我相信《醉舟》一气呵成,无须想象,直接“看见”;没有任何思考余地,更不必借助毒品——借助本质生命里的“醉”,让狄俄尼索斯在血液中“跳舞跳舞”足矣。评论家索莱尔斯认定,兰波的一些作品是毒品所致;可哪里知道,诗人早已化身“醉舟”,“吮吸群星的乳汁”——
至此我浸入了诗的海面,静静吮吸着群星的乳汁,
吞噬着绿色地平线;惨白而疯狂的浪尖,
偶尔会漂来一具沉思的浮尸。
所有这一切,非肉眼所见,却一语成谶:《醉舟》(兰波十七岁写成)成了兰波一生浪迹天涯的颂歌及咒语。
早在出发之前,《醉舟》已预言了自己日后(从非洲荒漠)回望的情景——
一阵战栗,我感到五十里之外,发情的巨兽和沉重的漩涡正呻吟、颤抖;
随着蓝色的静穆逐浪徘徊,
我痛惜那围在古老栅栏中的欧洲!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一词,在兰波的诗歌及日后的书信中反复出现——无论逃离,嘲讽、甚至诅咒,诗人始终“痛惜那围在栅栏中的古老欧洲”;欧洲不仅是诗人的出生地,祖先故居,更是神话的家园,流浪精神的归属。而诗人一生心心念念,却有家难回;一世孤绝,又为什么?
对照兰波的诗歌与生命,年轻的生命与古老的欧洲,我们与其说“超前”“落后”;不如说“错过”——“通灵者”无所谓前后,无论活在怎样的世代,总是孤苦伶仃,“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另一个”。
而对于诗人或作家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出版作品,并赢得时代的赞誉,自然是幸运、幸福的,比如雨果、巴尔扎克;可倘若作品与生命一并“超前”或“落伍”,同时代的人根本无法理解、接受,作者也只得被迫忍受荒凉孤单。无论曹雪芹老先生,还是少年兰波。而所有这一切,皆命运使然,非个人所愿。你说这是“恩典”,可领受这“恩典”的人,往往苦不堪言。起初,兰波也想出名,出版诗集的。1870年5月24日,兰波写信给导师泰奥多尔·德·邦维尔,请求他推荐自己的诗歌,说自己是一个“被缪斯手指触碰过的孩子”,渴望“成为一名帕纳斯诗人”;但当日后诗人觉醒,如“青铜唤醒铜号”,终于打消了一切“非分之想”,而以“另一个自我”,向“另一个世代”喃喃自语,或恶毒诅咒——这便是我们日后所看见的《彩图集》和《地狱一季》。在匆匆完成这两部“遗作”之后,兰波心如死灰,从此彻底放弃了文学,乃至文明世界,真正如他的祖先高卢人那样茹毛饮血,“在草原上纵火”,成为“那个年代最无能的种族”(引自《地狱一季》)。而这种“无能”,让人联想到波德莱尔的“信天翁”,被船员钉在甲板上,饱受凌辱——“冲天翼妨碍它在地上行走”。兰波的“荒漠书信”引燃的“荒凉之火”一直漫溢至今日,每一匹“荒原狼”心中。
总之,兰波的诗歌与生命线相互交织、激励:因为是“我是另一个”——“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祖国?——不知它在什么方位”;“朋友?——不知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是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所描述的“陌路人”;兰波也正是如此,故称波德莱尔为“诗人的皇帝”;这“皇帝”道出了他内心的苦楚——《恶之花》也不单纯是“恶之花”,也是痛苦之花,不幸之花。总之,“通灵者”生活在另一重时空:他的世界与众不同;世界于他,他于世界,咫尺天涯,形同陌路,彼此都是“另一个”。正如“红楼”中的宝玉,“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生于“花柳繁华地,富贵温柔乡”,却总感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尤其是“发作起痴狂病来”,竟将通灵宝玉狠狠摔在地上,并骂道:“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何以至此?因为“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如今来了这们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而回想起兰波冲天一怒,“抛弃文学”也是如此。
世人梦寐以求之“通灵宝玉”,或“创作天赋”,真的落在一个人的头上,是祸是福,也未可知。世人都渴望成为的“通灵者”,而各种感觉的“错轨”,“各种形式的情爱、痛苦和疯狂”谁来承受?谁愿意“寻找自我,并为保存自己的精华而饮尽毒药”?谁又能“在难以形容的折磨中,他保持坚定的信仰与超人的力量”,并“成为伟大的病夫,伟大的罪犯,伟大的诅咒者,——至高无上的智者”(引自兰波书信对“通灵者”的描述),并不惜为此忍受一世孤独、凄凉?世人都爱读红楼、梦红楼,仰慕兰波,但假如“宝玉”再世,兰波活在今天,处境又当如何?
而说到底,兰波之不幸,正缘于“通灵”;无论是被“缪斯的手指触碰过的孩子”,或天生含着“通灵宝玉”转世来到人间都一样——玉是女娲补天的巨石缩成扇坠大小;缪斯是奥林匹斯山上的文艺女神。而所谓“通灵”,无非是与祖先灵魂相通,让女神与元初的神话传说,从“通灵者”口中转世复活。
回望兰波早期诗歌,说的都是孩子,悲伤的孤儿(《孤儿的新年礼物》)、贫穷受苦的孩子(《惊呆的孩子》)、温柔死去的孩子(《山谷睡人》)、快乐流浪的孩子(《感觉》《绿色小酒店》)、温情恋爱的孩子(《初夜》《传奇》《狡黠的女孩》)、风趣幽默的孩子(《妮娜的妙答》《我的小情人》)、翻箱倒柜的孩子(《橱柜》)、桀骜不驯的孩子(《七岁诗人》);兰波自身,也正是这样一个单纯而丰富的孩子,他“培育了比别人更加丰富的灵魂”。而所有这一切,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仔细考究,均来自“前世”之精神血脉。如同宝玉含着女娲的灵魂转世投胎;兰波早期诗歌《太阳与肉身》携着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美神一并归来——这是兰波篇幅最长的一首诗,从牧神潘与山林水泽的仙女的爱情,说到天地万物之母库伯勒——“乘着巨大的青铜车,游遍光辉城池”;从丰产女神阿斯塔耳忒及海水中诞生的爱神阿佛洛狄忒,说到将奥德修斯留在俄古癸亚岛的女神卡吕普索,小爱神厄罗斯,被忒修斯抛下的女神阿里阿德涅,以及宙斯变白牛引诱欧罗巴、化身天鹅诱惑丽达等一系列关于爱与美,生殖与创造的神话故事,而所有这一切,与其说出自经典,不如说源于诗人自身的精神血脉与原始冲动——“通灵者”就这样与神灵相通,从自身的创作中,复活“古老的欧洲”——
骑在宙斯这头白牛的脖子上,
欧罗巴赤身裸体,
像个孩子一样晃来晃去,挥舞着洁白的手臂,
扑向波浪中颤抖的天帝强壮的脖颈,
天帝缓缓地向她投来蒙眬的目光;
她苍白如玉的面孔垂落在宙斯的额上,
闭上眼睛,在神圣的一吻中死去,
河水呜咽,金色的泡沫
在她的头发上开满鲜花……
这正是“欧洲”(Europe)的来源——不仅是“欧罗巴”这一名称,更包含源自希腊神话的人神合一、生命至上的精神,是对爱神与美神的崇高礼赞。
清代诗人袁枚诗云:“名须没世称才好,书到今生读已迟。”无论是宝玉、兰波,通灵者一样唤醒了自身血脉中的前世记忆。这也正是“莫失莫忘,仙寿恒昌”的含义。女娲“选择了”宝玉;缪斯“触碰了”兰波;而一旦诗人意识到自身使命,却又不得不因自身的孱弱,而陷入沉默——“科学,这新贵!进步。世界在前进!世界为何不回转?这是芸芸众生的幻想,而我们走向神灵。坚定不移,我所说的,来自天意。我心里明白,若不用异教徒的话语,便无法说清,因此,我宁愿沉默。”这是兰波在《坏血统》中留下的“遗嘱”,也是文学创作中一个悖论:创作者自言自语,“言说”自身的“沉默”。如鲁迅《野草·题记》中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我想,这“沉默”有多重语义:一种是不说、不写,不发声、不开口;而另一种“沉默”是不向公众、世俗开口,继而放弃今生,只喃喃自语,向来世及后人诉说。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语言作为寂静之言说,寂静静默,唯有寂静,能让世间万物进入其中。”或如布朗肖所说:“作品所封闭的,正是他不停展现的。”而兰波诗歌中的诸多暗语,恰好印证这种“沉默”正是对存在的庇护和隐藏,是无声的嬉戏,无声的聚集,内在的激情涌动。
有关与此,布朗肖在《文学空间》里论道:“在这种话语中,世间在退却,目的已全无;在这种话语中,世间保持沉默。人在自身各种操劳、图谋和活动中,最终不再言说。在诗歌话语中表达了自身的沉默。”而字里行间,“诗歌的话语不再是某个人的话语:在这种话语中,没有人在说话,而说话的并非人,但是好像只有话语在自言自语;语言便显示出他的全部重要性;语言成为本质的东西。”
然而不仅如此,布朗肖还借用希腊神话中俄耳普斯的故事作隐喻,向世人揭示了隐藏在这“沉默”之下的,更深更隐秘的创作原理:竖琴手俄耳普斯拥有超凡的音乐天赋,他的歌声和琴声能使木石生悲,猛兽驯服;而他深爱的仙子欧利蒂丝在新婚之夜被毒蛇啮足,命丧黄泉;深爱欧利蒂丝的俄耳普斯难忍悲伤,只身奔赴冥府,凭着美妙的歌声琴声,打动了渡口船夫、地狱看门恶犬,就连冥王哈得斯也被感动落泪,准许他带着欧利蒂丝返回人间,但条件是,在见到人世的第一缕光之前,俄耳普斯不能回头看身后的爱人。然而冥途将尽,俄耳普斯却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以确认爱人仍跟在身后,而就在那一瞬间,欧利蒂丝再次堕入冥府,万劫不复。而布朗肖以此作隐喻,认为欧利蒂丝象征艺术本源;“俄耳普斯的目光”正如艺术家与艺术永恒的悖论——艺术家(俄耳普斯)试图从虚无(冥府)中,救出艺术本源(死去而不可见的欧利蒂丝),使她复活,重现于人间;然而“直视”灵感及艺术本源,却又使之瞬间毁灭,再度化为虚无。
发现这一悖论,布朗肖继而认为,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必须抵御“灵感”的过度洋溢,从而使作品成形问世。换句话说,只有不去“直视”欧利蒂丝,才能使之复活重生。这一切,看起来很有道理,然而,兰波的艺术生命,却仿佛同时是在对布朗肖的这项艺术理论的印证与颠覆:在印证中颠覆,在颠覆中印证。为何这么说?因为在我看来,兰波正是那个回头一望的美少年俄耳普斯——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通灵诗人”,他分明以“俄耳普斯的目光”回头看了一眼,并在刹那间看见了诗歌本身,灵感之源(欧利蒂丝)——有《醉舟》为证,《地狱一季》为证。
兰波不像瓦莱里那样是个“代数学家”;瓦莱里认为“诗永无定稿”,而兰波的诗一气呵成,自然天成(我相信)。按布朗肖的话说,这“潜在的火花”“闪电的瞬间”和“闪电的爆发”是诗歌的高潮,同时也是诗歌的解体——可问题是诗歌不是幻象,是文字,一旦存在,瞬间永恒。而兰波就这样猛回头,不仅将看见的一切载入“诗”册,而且索性回身,跟着爱人“欧利蒂丝”(灵感之源,艺术本质)返回地狱,并完整经历了《地狱一季》——
当一对“妄想狂”的声音从地狱里清晰传来,我们还需要什么别的例证?这地狱中“奇怪夫妻”的对话实在太疯狂了,让人不禁联想到俄耳普斯与欧利蒂丝,或兰波与“通灵诗歌”或大致如此?——猛回头,面面相觑,相互直视,电光火石间,双双堕入地狱——原来艺术的本质,蕴藏着如此疯狂与风险!这让我想起自己近年在长江边采风所得的民间传说:相传说风水先生看地,谁看见真地,谁就会瞎了眼睛。还有龙洞里有个龙王小姐,美若天仙,但不能看,一看她就永远消失。——“神话千变万化,故事只有一个。”(约瑟夫·坎贝尔)其中隐含的真谛,耐人寻味。
再看“红楼”作者,因深谙“通灵”之危险,艺术灵感不能直视的原理,故借“假语村言”,环顾左右而言他:而其中所隐藏的,不仅是真人真事,更有艺术真谛。故“红楼”自始至终,小心翼翼,用“痴呆”“无能”“似傻如狂”来掩饰“通灵宝玉”,甚至不惜将“通灵宝玉”摔在地上,以此隐藏、保存自身,忍辱负重,将“通灵宝玉”传于后世。——他果然成了!“红楼”历经劫难,完好无损,亦真亦幻,足以让后世通灵者辉煌隐居。
而兰波日后绝望觉醒,故彻底放弃文学,扔掉“通灵”这“劳什子”,想做回一个普通人好好活下去。但“通灵”非身外之物,不是想得就得,想扔就扔的“劳什子”——尽管放弃文学,亡命天涯,这诗歌的“盗火者”,终究难逃普罗米修斯的厄运——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他都撑了过去,熬了过来;而最终残酷的疾病,剥夺了兰波年轻宝贵的生命。
我们今天阅读兰波,已不再冒任何风险,因为诗人已从地狱将这一切艺术本质、灵感之源带回人间——在我看来,《地狱一季》代表兰波创作的最高成就——这也正是少年诗人“回头”的代价和所见的一切。——当美少年乘着降落伞堕入地狱;地狱之火如烟花璀璨,又瞬间寂灭。也正是神奇光焰,顷刻耗尽了诗人全部的灵感与生命。
无可否认,此后兰波的艺术生命终结、枯萎了,好像一团野火,在非洲荒漠渐渐枯萎熄灭;没有亲人,也没有小王子从天而降,给他送去玫瑰与甘泉。然而自始至终,这位“倔强的苦役犯”抱定必死的决心,直到下地狱也不做丝毫让步妥协,或如《醉舟》在诗的海面“通体崩裂”。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兰波的“彻底颠覆”,反过来印证了布朗肖的艺术理论:艺术家不能回头,“俄耳普斯的目光”注定毁灭一切。而悖论正在于,他必定回头,这是俄耳普斯,也是少年兰波的宿命。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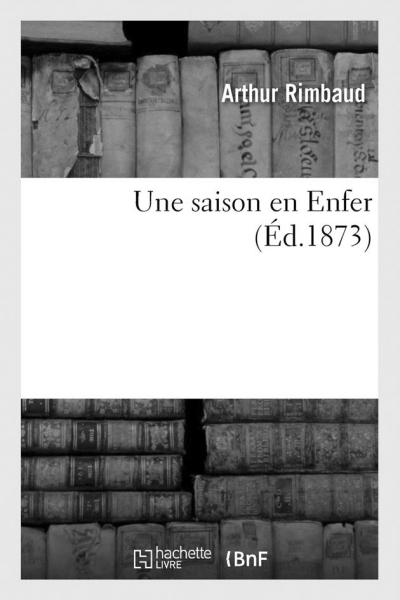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