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含混的叙述人格
在《童年兽》的写作中,陆源可能最为珍视的是诅咒式的叙述腔调,而非情节。小说情节并不复杂,讲述的是陆小凤九岁进入市体校学棋至离开棋校的一段经历,穿插着海南旅行、郑州集训等一系列碎片。如果未曾在塞利纳中寻到这样一种叙述腔调,陆源可能还需要在更长的时间里痛苦摸索叙述这段封存了近三十年的故事的最佳方式。我们需要叩问的是,《童年兽》为什么需要此种腔调,它在此间起到究竟何种作用?以及两种腔调的区别在哪里?
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里将塞利纳作为擅用非人格化叙述的道德技巧的典型。当第一人称的自陈意在导向刻意的混乱和含混,早期小说中那种清晰的价值判断实际上已经烟消云散。小说的现代性某种意义上必须包含这种松动的道德。对亨伯特的道德观察绝非易事,他辞令典雅,与之相比,《童年兽》中,陆小凤出口不逊,欺凌弱小,仅仅因为智力差距,棋童阿阮就被他和同伴骑在裆下,他的得意并未持续一页,就被化为正义闪电的教练黄晋材打落在地。
不安和恐惧真切伴随,又蒙着一层世事麻布。只有展开布匹,我们才能透光看见罪愆的纹脉。但当我们刚刚嗅探到一点受害者的痕迹,判断又迅速被带着强烈情感色彩的语调以及其他情节带走。直到十四章,小说才回到之前那句话开启的裂隙,将前尘旧事一点点暴露。侵害始终被安插在其他事件的缝隙中,只在偶尔间吞吐恐惧,好像那种事件只存在于黑夜,白日即无影踪。比起塑造单面完美的受害者,叙述者更想呈现一个更立体的人,来判断你那点同情是否仅仅来自于浅表。或者说,同情也全不重要。这种叙述的声律如此复杂:从自怜到狂躁,从猥亵、咒骂至抒情、崇高,从嘲讽、训斥至模糊的冥想。
是的,幼童再狡狯凶狠,也不过带着面具,手执玩具枪支,在成人面前,他们矮小孱弱,不堪一击,凶狠是因为被不由分说便推进噩梦,狡狯是因为身处囹圄,以致服下催熟剂。
——我们远比自己想象的要更接近他们,哪怕足够幸运,未曾历经残酷,也依然不可避免地接收着成人世界给予的训规与混乱,直到最后成为混乱的一部分。在一开始,乃至最后,我们确实不断祈求被爱,直到爱的欲望以不同形式出现。
如果没有这样的比对,和父亲的那段叙述不会显得如此动人和温存:
穿行过蛙声阵阵的星湖之中,我毫无预兆地认识到父子间的鸿沟何在……我发觉,父亲像鸟一样害怕不可预知的事物,他在儿子长大成人之前就匆匆老去了……崎岖不平的塘边小径上,父亲推车步行,指导我辨认水鸟、云气乃至星座……多年以后,我才总算明白,那是古老时代残留在父亲身上的语序,是地方传统和市镇荣誉感的最后一抹亮色。而作为他生来叛逆的小儿子,我势必一天天远离这个渐冷渐暗的太阳系。
陆小凤成人后重访体校,发现深鸿已成过去,恐惧烟消云散,剩下的都是淡金色记忆。这一段至少经历了三次时间以及心境的跳转:男童已不复天真,但是父亲尚未意识到此一变化,鸿沟显现,男童的苦恼无从倾诉,寄望于尽快踏过,但时间难逾。这一段描写是如此精湛优美,痛苦深刻:古老残存,却已是夕阳余晖、虫瘿遍身,工业尚未侵入,新世界的到来已不可逆转。命运在前方昭示,父亲佯装镇定,儿子缄默无声,两人在单车上短暂相靠,任由岁月慢慢垂落,恰如等待一场缓慢的雪崩,再最终被隔开。
南方、记忆与童年
塞利纳之前的现实主义者认为,福楼拜提供了一种写作样本:在观念之上附着文字,将思想凝结为语句,句与句之间紧凑,空间狭窄,在狭窄之中趋于精准。这确实为一种向度,也因此可以预见陆源在长句叙述选择上的风险。但整饬后的古旧似乎与这种叙述文本更相宜:所有被禁锢、遭遗落的意象和情绪都必须从那一处黄昏暮色或死荫之地飞来,直至再次被唤醒。恰如克莱尔·帕尔奈所言,尼采用德语所做的事情就是在他自己的语言里成为一个异乡人。我们在其文本中再次获得了新异感,陆源在其间横冲直撞,奔涌不休,并最终产生了德勒兹所言的写作速度,变成了一种流畅绵延的音乐。语言的声音在小说那一段关于京剧院的叙述中被有意识地提炼:声音的龙卷风在荒寂的大院内肆虐,俚语黑话、本地方言与京腔、与西方古典乐在南方炎昼中混合,这恰是陆源在文本中所使用的这种文鄙兼备、东西杂糅的复杂文法的外观象征。
小说最后说,“离开棋队,我才算与真实相连”,故事已告一段落,但合上书页后,我们依然不得不充满怀疑,我们真的从那个变形、疯狂的幻象里抽离出来了吗?我们现在面对的世界是真实还是另一个洞穴投影?事实上,旧日之影从未烟消云散,童年是食人巨兽,是长夜伤痕,是幢幢鬼影,残楼腐地,若要往前一步,必须不断回溯、不断注视,否则我们只知自己愤怒,却不清楚愤怒来源以及消解之道。当我们注视得足够持久、深入,才能看到那过去的时间如何变成了一截可以不断再访、往复穿梭的长廊,变成了一种空间似的存在,容纳了“我之前人生的所有时间,所有我可能心怀过去的,被压制又熄灭的恐惧和快乐”(赛巴尔德语),我们才能意识到这些碎片如何改头换面构成当下,成为索骥之图。我们既欲求探索,只能不断回访,不断向内,直抵记忆与存在,直至接近真实轮廓,“让我们一瞥那个无底深渊,那儿源源向外涌着祈祷的需要”(齐奥朗),深渊恢宏,光的垃圾最终被锤炼成璀璨的气层。在自我向度的无限开掘中,陆源正试图找到某种更具深味的时代解码,将个体私密的生命经验与变革动荡的外部相连,关于日渐凋敝、日渐抹平的城镇生活,在叙述中,成为火光,并且完全燃尽。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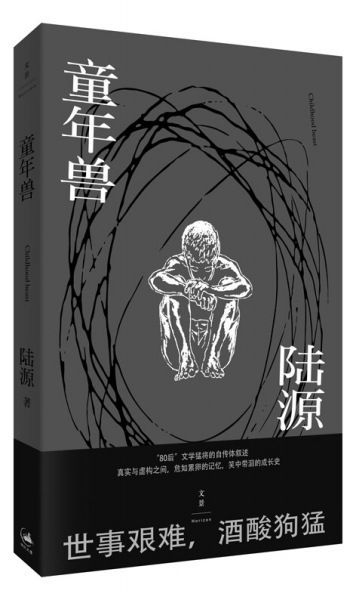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