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有写书话的传统,那些堪称典范的古典散文中的有些篇章,那些风韵飘逸的诗话、词话以及丰富繁杂的笔记,都有不少可以类属书话的佳作,谈书、论人、评文、钩沉、述掌故、叙历史,流利潇洒、韵味隽永。不过,这都不是自觉的书话写作与规范的书话作品。也许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书话作品,是从现代才有的吧。
谈起现代书话,虽然现在已渐趋沉寂,但曾经颇热,而且成就可观,影响不小。其作者大都是作家、学者,或者“一身二任”者,而其作品则可视为他们的作品或著述的分支。比如书话名家周作人、西谛(郑振铎)、阿英(钱杏邨)、晦庵(唐弢)以及旅居港台的梁实秋、叶灵凤等,年轻晚辈则有黄裳、姜德明等,便都是。也有的还同时是藏书家,如郑振铎、钱杏邨、黄裳、姜德明他们。
书话写得最漂亮,有文采的,要数晦庵(唐弢)吧。至少我是最爱读他的《晦庵书话》:有史料、有掌故、有人事、有见闻、有亲历,千把来字,娓娓道来,文采斐然,篇篇超出书话范围,而成精致散文。想当年,上世纪50-60年代,在《人民日报》副刊连载,真个是不胫而走,誉满文坛。听李希凡笑谈,时他与唐弢皆为政协委员,开会休息时,二人相偕散步,李盛赞《人民日报》的书话,问“晦庵是谁?”唐弢笑而答曰:“就是鄙人哪”。晦庵写的都是关于现代文学作品的,因此其书话也就成为这门学科的鲜活的研究资料。在这方面,阿英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夜航集》更是即时的“书话纪实”,其为史料,价值更大了。在这方面,姜德明是后起之秀,他的《书边草》《书梦录》《书味集》,也是资料丰富、掌故连连,于名作大家,连及作家逸文等,多所述说与钩沉,于冷僻掌故与文坛逸事,也不乏剔抉,文字也类乎散文,可读性强。
现代书话之作,出现时间最早、文字最老到而声誉最高的,莫过于周作人了。他的书话确实不同凡响,特别是颇具学问、知识渊博、学底深厚、思路开阔,文化含量高:这都是他的书话的优胜之处;而且,他写得要言不烦,言简意赅,意味蕴藉。读起来味道隽永。这都是应该肯定的。不过有些对他的吹捧,却不敢恭维。如有的文章解说周氏某些书抄式的书话,写得如何如何了不得,凭空说道;而他的文章实际只是开篇提个头、引过书名,便是抄书一段,随即煞尾;有的则是连抄数书、数段,终篇。故当时就遭“文抄公”之讥。倒是周氏本人还实事求是一点,据说他有言:文抄公嚜,抄什么书、抄哪一段、如何摘法,也非易事;而他之所抄,皆非凡品,也常不为人所知,或者是非习见之书,此等处所,就是学问所在。这话有道理,他所抄之书,确实少见多味。
我很爱读的书话,除唐弢的佳作外,顶数梁实秋的《梁实秋读书札记》、杜渐的《书海夜航》和叶灵凤的《读书随笔》一、二、三集。梁氏的读书札记,以大学者写小文章之姿,古今中外、诗歌戏剧文学,涉及知识领域广,有“引荐”、有“掘藏”、有考订、有论辩,还有剖析评论,驾轻就熟,中西贯通,文笔又清新流丽,文化层次上高出一般读书札记一层,十分引人阅读,足可供人欣赏。如《莎士比亚与性》等三篇札记、《玛丽·兰姆》之绍介、《纯文学》之议论,足称西方文学评论;而《读杜记疑》《〈登幽州台歌〉》《万取千焉,千取百焉》等作,又俨乎国学评议,至于《寒梅著花未》则是文学短论,而《四君子》更是一篇清雅散文。
杜渐在书海里夜航之作,却没有如梁氏之作那般轻舟泛清溪、舟中书香清新、水上落英缤纷、两岸风光旖旎,足可留连观赏那般飘逸潇洒;杜氏之作,另具格调,别有风韵。他的书话,篇幅长、容量大、知识性强,夹叙夹议,带有一种学术性。如《堂·吉诃德的武士英魂》《唐·璜的原型及其他》《从〈风月物语〉看中日文学渊源》等篇都是如此。他还以介绍国人知之甚少的外国作家作品而引人入胜。那篇《永恒的童心》写得多么引人:一个少女,为了安慰她生病的小朋友而写文绘画,编造了一个兔子、刺猬、鸭子和松鼠的小小的快乐花园世界,这些“慰问信”,后来竟集纳成为一本书,以《小兔子彼得的故事》为名问世,且风靡世界,至今已译成许多种语言,那些插图竟然同大师的名作一起,挂在伦敦塔狄美术馆,供人欣赏。但更有趣而令人玩味思索的是,作者后来嫁到乡间,隐居山村,操持家务,当崇拜者前来拜访向宛如农妇的她致意时,她却对应赞誉之词说:“胡说,没那回事!”这位女作家的名字叫:比阿特里斯·波特(BeatrixPotter)。《书海夜航·二集》后面还有《书海掇拾》则是短短的书籍介绍小文,多涉外国文学,也甚可读。
上世纪三十年代活跃在上海文坛的作家兼画家叶灵凤,后来在香港以书话闻世,他的《读书随笔》一、二、三集,可谓别具风格。从内容上讲,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历史地理、丰富繁杂,有内容介绍、史料钩沉、版本考索、作家轶闻,方面很广泛。尤其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更有不少作者亲历的与著名作家交往的逸闻轶史,如《达夫先生的气质》等八篇有关郁氏的随笔,相当集中;此外还有关于鲁迅、郭沫若、郑振铎、林语堂以及倪贻德、张光宇、谢澹如、罗家伦等人的文章,都有逸闻轶事,堪属珍贵史料之作。文章大都短小,娓娓道来,亲切引人,于趣味的阅读中,增长知识见闻,享受书趣,于不知不觉中获益受惠,充分体现了书话的特点与作用。这些随笔,原来曾有各自的名目,如《霜红室随笔》《晚晴杂记》等,表明作者的写作这些随笔,是在晚年,而《香港书录》,则全是谈关于香港的书,内容专门而珍贵。
陈原的《书林漫步》和王西彦的《书和生活》类同而内容有别。所谓类同,是它们都带有专业性、学术性,有的甚至是正宗的论文模式,虽然如此,但都同书籍有关,所以还是可作书话看。如陈原的《语言的污染与净化》,长达20多页,可谓长文;王西彦的《读巴尔扎克札记》专辑,更是文学笔记系列。
略述往昔书话如上,却甚感如今书话的式微,几乎不见报刊书肆,几疑其绝迹文坛。尤其现在出现纸质书籍消亡论,怕是书话真的要寿终正寝了吧?令人遗憾而感伤!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否和现在的社会读书风气不盛有关?果如此,那么,提倡写书话,以激励读书风气,就更有必要了。在这方面,我以为以鼓励读书和介绍评论图书为职志的《中华读书报》是能够起到倡导作用和使之繁盛的园地,具体地说,就是《家园》这个专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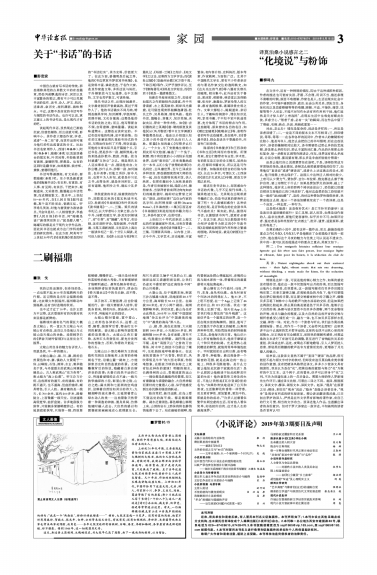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