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良的《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中国与世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下简称《坤舆》)试图对“世界史三大经典学说:明代郑和下西洋止于东非洲;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利玛窦世界地理西学东渐”发出挑战,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坤舆万国全图》主要是郑和时代中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是中国文献。世界地理大发现始于郑和时代,明代中国人测绘的第一份世界地图。”笔者认为,该书逻辑漏洞百出。
逻辑的混乱与双重标准
柯南·道尔“排除所有不可能的因素后,剩下的无论概率怎么低也是真相。”是李兆良《坤舆》一书的逻辑基础,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逻辑是否能够成立,即使这是一个可以成立的逻辑,李兆良也没有完成依据这个逻辑得出“真相”所必须具备的前提:“排除所有不可能的因素。”同时,李兆良在论述《坤舆万国全图》与东方和西方地理知识的关系时,运用了双重标准:前者是无罪推定,后者是有罪推定,这样得出来的结论是不足以服人的。
在《经度的测量》一节,李兆良历数维斯普奇、卡博特经度测量的缺憾,并说“从没有经度的科萨1500年地图,到有经度的瓦德西穆勒1507年地图和1508年的《罗塞利世界地图》只有几年,又如何解释呢?”李兆良认为欧洲人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中自己发展出有经度的地图,他们只能是参考了中国人的有经度的地图。但这一论述毫无逻辑可言:首先,任何一种东西,出现之前,即使是前一天,都是没有这种东西的状态;没有有经度的地图,不等于欧洲人没有在为绘制有经度的地图而努力。其次,李兆良甚至没有证明中国人有经纬度的概念,也没有拿出中国人绘制的有经度的地图作为证明,就断言欧洲人从中国人这里学到了地图的经度知识。
接下来李兆良质疑了欧洲16世纪地图上的经度来源,“西班牙发现者在日记中也经常提到经纬度,然而,这些记载是不能尽信的,他们可能是看着已经有经度的地图而叙述,而这些地图的来历不明。”李兆良对西班牙人日记中经纬度数据的攻击完全出于猜测,却忘记了同时期的中国人,完全没有对于经度的记载。李兆良否定欧洲人首先绘制出了有经度的世界地图,既没有证据支持,也缺乏逻辑基础。
谈到中国人的地理成就,李兆良就变得极为宽容:“秦始皇征南越的时候(公元前217年),打通了长江与西江的上游,用灵渠连接起来,可以运兵到广西,再沿西江入广东,这是中国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当时一定有高超的技术测量经纬度和海拔高度才能减缓落差。以后隋朝(581-619)的大运河系统也是需要准确的测量技术。”李兆良甚至都没有证明中国人有经纬度的概念,就大胆地断言中国在秦朝已经具有了测量经纬度的技术,并将之付诸实践。建造灵渠和大运河真的需要经纬度么?恐怕答案是否定的。如果以灵渠和大运河作为衡量技术水平和地理知识的标准,那么中国一定比古代的罗马人逊色太多,罗马人建立的大量的、恢弘的高架饮水桥,其对于技术和地理测绘知识的要求远高于中国的灵渠或者大运河。
成一农在《“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中谈及中国人对经纬度的认识和测量时说道:“正如李约瑟所说,中国古代确实很早就掌握了测量经纬度的基本方法(虽然测量经度的方法直至近代才逐渐完善),而且至少在唐代就进行了一定范围的经纬度测量工作,在元代也进行过‘四海测验’,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两次测量工作,都是为了编订新的历法(分别为《大衍历》《授时历》)做准备,而不是为了绘制地图。而且与西方不同,中国没有保存下来一套经纬度数据集,而在西方,早在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等著作中就记载有很多经纬度数据。不仅如此,在西方的早期地图中就清晰标明了经纬度,但中国至少现存的受到西方影响之前的传统舆图中没有一幅体现出其绘图数据使用的是经纬度,也没有文献记载曾经为了绘制舆图而进行过经纬度的测量。”
谈到郑和在海上对经纬度的测量,李兆良说:“如果不用星辰去测量,在摇晃的海船上测量,必须有多只船从远处以通讯方法来计算距离刻度。我们无法知道当年郑和用什么方法,但是可以肯定,他们的船队那么大,能在海上多点观察是不成问题的,他们没有电报,但是有很多船和人力。通讯方法是白天用旗号,晚上用灯号,雾中用金鼓。陆地上的经度更不在话下。”“船和人力”很显然不能自然地解决技术问题,测绘终究还是需要有经纬度的概念和可行的测绘方法,而对于这两点李兆良都没有展开探讨。他对于郑和测绘经纬度和郑和绘制地图的论证陷入一个因果的循环论证:因为郑和船队测绘了经纬度,所以他们绘制了给《坤舆万国全图》提供重要参考资料的地图;因为郑和或者与其相关的船队人员绘制了给《坤舆万国全图》提供重要参考资料的地图,所以他们必然曾经做过详细的经纬度测量。
朱鉴秋《〈郑和航海图〉之基本特点》对《郑和航海图》的特点做了清晰的描述:“1.在总的内容方面,突出表示与航行有关的要素。2.江河、沿岸及大洋不同图幅的内容的差异,反映出区域的航行特点。3.图幅的排列配置以航线为中心,图幅的方位是任意的。4.航线的注记详细而有较好的精确性。5.配置有天文导航专用的‘过洋牵星图’。”《郑和航海图》的核心特点在于其以航行为目的的实用性,在这套由40页航海图和4页过洋牵星图组成的《郑和航海图》中没有出现经纬度,而所谓的“针路注记详细而相当精确”指的不过是以传统罗盘的二十四个方位来表示方向;或者稍进一步,有用两个字表示方向的中间方位,即有“四十八向”。《郑和航海图》完全看不出绘图者具有经纬度的概念,那么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认为对经纬度完全没有概念的一群人,测绘出了全球精确的经纬度呢?李兆良对郑和或其船队人员测绘海洋和陆地经纬度的论断显然不能够成立。
李兆良否认欧洲人的地理知识是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的基础时说:“《科萨地图》的纬度只有简单的赤道和回归线。地图学与任何科技一样,发展要有个过程。西方在1507年的《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出现以前,没有经纬度的雏形,突然在1507年出现是不合情理的。”但是李兆良用以否定欧洲人测绘经纬度的逻辑也同样适用于否定郑和绘制《坤舆万国全图》的可能。更何况,李兆良要否定《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对《坤舆万国全图》的影响,还建立在其将《坤舆万国全图》的绘制时代强行提前到郑和时代的基础之上,这又是一个因果的循环论证。
对于《坤舆万国全图》的成图时代,李兆良认为是1428-1430年,他在《公元1430前中国测绘美洲》一文中对此做了比《坤舆》一书稍微详细的说明,但同样缺乏充分的证据和缜密的逻辑:“《坤輿万国全图》在西班牙上方有一段文字:‘歐羅巴洲……去中國八萬里,自古不通,今相通近七十餘載云。’此段明确了《坤輿万国全图》原图的成图年代。相通指正式建立国际外交关系。元朝时,欧洲教皇派使节马林诺里带领使节团50人来华,于1342-1347年驻北京大都。下数70年为1415-1426年间,正合郑和下西洋第六次以前。假如以利玛窦来华,献图,或者以欧洲奥特里乌斯地图出版日期算,为1500-1530年,为中国海禁时期(1433-1567),不与外国通,与此段文字不相容,因此文字是郑和时代记录的,原封不动,地图也是当时测绘的作品。”地图上的文字有可能是后来加注的,而并非与地图同时;“相通”在没有正式外交概念的中国古代,显然不可能指的是“正式建立国际外交关系”。
作为李兆良用以考证《坤舆万国全图》成图时代的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文献依据:“《坤舆万国全图》上西班牙上方的一段非常关键的注解”,李兆良在《坤舆》一书和《公元1430前中国测绘美洲》一文的征引却出现了误差,《坤舆》一书的征引曰:“此欧逻巴州有三十余国……去中国八万里,自古不通,今相通七十余载云。”《公元1430前中国测绘美洲》一文中的征引曰:“歐羅巴洲……去中國八萬里,自古不通,今相通近七十餘載云。”考之《坤舆》一书57页的地图,则两处征引皆有误,书中的征引少了“近”字,近七十年和七十年显然是两个有差别的概念;文章的征引将“邏”改为“羅”,“州”改为“洲”,地图上的文字可以成为判断地图时代的一个参照,李兆良对此文献资料的使用显然是草率的。
李兆良谈及“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的启示”,认为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中大量的经纬度信息,不可能是卫匡国亲自测量的,而只能是基于中国原有的数据。但是,第一,李兆良对卫匡国亲自测绘的否定不具有绝对性。第二,他也没有排除卫匡国从朝鲜获得中国地理信息的可能,毕竟他也承认,卫匡国的经纬度数据中,最为准确的就是今天首尔和平壤的经纬度,而朝鲜1402年诞生了伟大的《疆理图》。第三,李兆良忽略了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经纬度数据另外一个可能的获得途径:推算和估测。就像我们今天只要在Mapinfo中输入三个不在同一条直线上的点的经纬度坐标,Map⁃info就可以推算出图中任意一个点的坐标,卫匡国当年也可能是根据几个点的确切的经纬度数据,推算出了其他地点的经纬度数据。
对于“计里画方”,李兆良评价极高,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早已把地图的绘制规范化”,并将之视为“经纬度的雏形”。“计里画方”不过是在地图上打上了纵横的方格,为地图上的各种地理要素提供了一个参照系而已,与经纬度不具有可比性。正如成一农所说:“受到数据类型的限制,使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就现代地图的视角而言,是不准确的。不仅如此,这种绘制方法所使用的不是某一地理要素的绝对位置数据(经纬度就是一种绝对位置数据),而是一种与周边大量地理要素相关的相对位置数据。”“由于数据的问题,‘计里画方’并不能使得地图绘制得更为准确,只能在绘图时更容易摆放地理要素的位置;……‘计里画方’只是绘图(地图、图画、工程图)时的一种方法,并不能决定地图的准确与否。”
对明代时期的中国和世界的错误判断
李兆良对明代时期的中国和世界存在着巨大的误解,将中国看得过高,又将欧洲贬得过低:“以当时占全世界生产力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中国,七下西洋,每次两百多艘船,平均两万七千人,每次航程达两三年,总能力是当时任何欧洲航海者的一千倍以上,绝对有理由相信郑和船队有能力环球航行,这就是可信性(plausible)。”首先,明代中国的生产力占世界的比例,李兆良不知道是怎么核算的,如果他要下此结论,至少要给出一个基本的数据论证吧。其次,就算明代的生产力真如李兆良说的那么强大,也并不能推导出郑和的船队就有能力或者进行了环球航行。正如建造紫禁城需要的砖石材料和人力、物力可能比建造巴黎圣母院需要的多,但是并不能证明前者就比后者具有技术含量;事实是,后者对建筑技术的要求远高于前者。
李兆良对中国能力的过分高估并不仅限于明代:“中国是世界绘制地图最早的国家。……中国秦代早已具备精确测量术,结合天文观测与地面测量,有能力绘制精密的地图。为什么只相信西方才有能力绘制世界地图?”1881年,考古学家拉萨姆在西帕尔,今天伊拉克巴格达西南的阿布哈巴城发现了近7万块楔形文字泥板,其中一块距今2500年的泥板“是已知的第一幅世界地图”,“是现存最早的从地球上方以鸟瞰角度将全世界以平面形式呈现的文物。”([英]杰里·布罗顿:《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引言》,林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这幅刻在泥板上的“巴比伦世界地图”,比中国现存最早的地图“天水放马滩地图”的时代更早,同时,放马滩地图只是地区图,显然不能纳入世界地图的比较范围。李兆良“中国是世界绘制地图最早的国家”不知道是有何依据而做出的论断。绘制世界地图,需要的不只是技术,更重要的是对世界的观念,“制作地区地图和世界地图最重要的区别是感知上的区别,这在绘制任何世界地图的过程中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与地方性区域不同,制图者永远无法一眼捕捉世界的全貌。……在这项重大的创新(太空摄影技术)出现之前,制图者主要借助两种资源绘制世界地图,这两者都不是地球本身的一部分:一是头顶的星空,二是各自的想象力。”(《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引言》)世界地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绘制者对世界的认知。
李兆良对中国很多事情的论述是建立在对欧洲、中东的社会、历史、文化、科学、知识、技术的漠视和无视的基础之上的。对于欧洲的中世纪,李兆良的态度是轻蔑的,认为其除了宗教的禁锢一无所有。但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真的一无是处么?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怎么可能从一片蛮荒之中如石猴一般诞生?完成或者始建于中世纪的大量恢弘的天主教堂:锡耶纳主教堂、巴黎圣母院、米兰大教堂、科隆大教堂,其承载的技术能力使得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否定中世纪的科学、技术能力。
李兆良说:“西方的都城没有一个是方正的,主要街道从城中心扩张放射出去,巴黎、莫斯科是最有代表性的,马德里、罗马、柏林、巴格达、开罗亦如是。”我不知道李兆良谈论的是什么时代的欧洲诸国都城,建城之日的、明代时期的,还是今天的,这个问题不说清楚,就要据此谈论《坤舆万国全图》时代欧洲人的地理观念,显然是不严谨的。今天的巴黎,以凯旋门为中心,确实有多条向外发散的大道,但是现在的巴黎并不是明代时期的巴黎,更不是建城之日的巴黎。而所谓罗马的中心-放射,我实在不知道李兆良是怎么得出如是结论的,作为七丘之城的罗马实在无法满足他的预设,不管是在建城之日,还是在明代时期抑或是今天。
以“地名”考证作为判断地图作者的最重要依据
“地名”很显然保存了地图绘制者的地理知识和地理认知,但是要将此作为判断地图绘制时代和绘制者的最重要依据,甚至是惟一的有效证据,显然是不能够成立的。地名反映的是地图“表现”时代的地理信息而不是绘制时代的,要借助地名来考证地图的绘制时代,有太多的文献考证和辨析工作要做,绝不能做一对一的直接对应。同时,能够用以佐证时代的地名只能是常用地名,稀见地名最多只能为地图的时代提供旁证。李兆良对地名的解释有很大的随意性,对于地名中西互译的各种可能性,李兆良并未做全面的考察,他的解释是随意的。
对“太平洋”“大西洋”名字的解说,是李兆良用以推断《坤舆万国全图》原作者的重要证据。关于“大西洋”的问题,龚缨晏已著文《利玛窦的大西洋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学术》做了深入而细致的批评。以下仅就李兆良对太平洋的阐释做简要的批驳。李兆良认为西方“太平洋”的概念来源于对中国地图“宁海”一词的翻译,并将之错误地应用到了世界上最广阔的水体之上。李兆良说:“即使有季节性的变化,基本上太平洋的浪高和海流是有一定区域规律性的,只有个别的地区可能被视为‘太平’,如智利西部对外海域相对平静,位置是南纬30度和西经100度-120度。《坤舆万国全图》和《山海舆地全图》上标示在麦哲伦海峡以西的位置的宁海是正确的,宁海与太平洋同义。麦哲伦海峡一直是惊涛骇浪的水域。往西行,能绕过这段,就踏入比较平静的海面。取名‘宁海’是有亲自经历的航海者才知道的。西方制图者,一旦发觉‘南海’一词的谬误,代以‘太平洋’,越写越大,包括整个大海洋。以讹传讹,一直到今天,整个亚洲与美洲之间都叫太平洋了,实际上太平洋真不太平!”李兆良对于“太平洋”的解释随意而诗意,但是这些并不足以支持他的结论。“太平洋”的命名是因为麦哲伦环球航行,经历了大西洋的惊涛骇浪、经历了险恶的麦哲伦海峡,而之后从南美洲经过关岛到菲律宾的航行却没有遇到一次风浪,故有船员概叹:“这真是一个太平洋啊!”于是有了“太平洋”之名。李兆良认为西方人概念里的“太平洋”得自于对中国地图里“宁海”的翻译,是有巨大逻辑漏洞的。
关于“本初子午线”,李兆良《坤舆》一书的叙述完全看不出逻辑和他的论证所指。李兆良首先说“把本初子午线定在自己国家是一项荣誉,因为其他国家都得参照。”然后他举出了美国、法国、德国、英国争抢“本初子午线”命名的历史。继而李兆良谈到了托勒密,他质疑道:“为什么托勒密不把本初子午线设在他工作的亚历山大,而设在遥远的加那利群岛,出了大西洋以后还要航行一段路。在陆地测量经度已经有困难,何况是在海上一个不知在哪里的岛?”最后李兆良以一段不知所云的文字结束了他“本初子午线”一节的论述:“据说他(托勒密)以幸运岛为0度,每50里为一度往东算。他以为中国在180度,其实是130度。……可是托勒密地理影响了以后十几个世纪的欧洲人,这个误差使哥伦布以为到了中国,16世纪很多地图继续保留这些错误,最大的海洋没有算进去。托勒密经纬度不能当成今天的标准。”李兆良对托勒密的质疑很有意思,他认为托勒密应该把本初子午线定在自己工作的亚历山大而不是大西洋上的某一个岛上,但这是一个很容易解释的问题,“本初子午线”反映的是一个人的地理观念和地理认知,托勒密认为大西洋上的这个岛是已知世界的最西端,故以此为依据构建他的地理空间,这是完全可能和符合逻辑的。作为罗马帝国时代的学者,这符合罗马人的地理感知,公元40年,罗马帝国吞并了毛里塔尼亚王国,建立了延吉塔纳毛里塔尼亚行省,位于今天摩洛哥西面海洋中的加那利群岛成为罗马公民托勒密知道和认为的世界最西端是完全有可能,并且符合逻辑的。
关于本初子午线的问题,李兆良在《公元1430前中国测绘美洲》一文中说的比较清楚:“非洲最西海岸多处位于现在的17W。《坤輿万国全图》的本初子午线贴着西非洲最西海岸,……这是亚欧非大陆板块的最西点,离开非洲最西海岸就进入大西洋,这是制定本初子午线的合理思路,也表示中国人曾到达非洲西海岸,在这里测绘。”李兆良的话说清楚了,但是凭什么《坤舆万国全图》将本初子午线设置在非洲西海岸就是符合逻辑的,托勒密将本初子午线定在“幸运岛”就是不符合逻辑的呢?这是两个基于同样逻辑的设定,就是以已知世界,或者某一个有特殊意义的点作为基准来构建地理空间。以非洲西海岸为本初子午线,怎么就能证明“中国人曾到达非洲西海岸,在这里测绘”呢?李兆良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在我看来,这是完全不能建立逻辑的关联。
最后谈一下“澳洲篇:鹦哥地、厄蟇、火鸡的启示”,关于这个问题,李兆良2012年在《海交史研究》上发表了文章《(坤舆万国全图)解密中国发现澳洲——鹦哥地、厄蟇、火鸡的启示》,用大量篇幅说明了“鹦鹉的分类与字源”“欧洲的鹦鹉”“中国的鹦鹉”,可谓不惜笔墨,但完全不足以支持和证明他的结论:“鹦哥地这地名出现在欧洲人发现澳洲以前,而欧洲人‘发现’澳洲者,都不叫澳洲为鹦哥地。因为他们对鹦哥的兴趣还没达到要用它命名。如果是他们发现并知道此地盛产鹦哥,应该继续用这名字。命名鹦哥地的国家一定不是命名‘新荷兰’的国家。所以,鹦哥地这地名,不是来自欧洲发现者,是西方制图人从别处引用了中国资料。”李兆良试图以中国人和欧洲人对“鹦哥”的不同态度来证明是中国人发现了被称为“鹦哥地”的澳洲,但是“鹦哥地”是否就是澳洲尚存疑问,“鹦哥”是否是“南极企鹅”的误称也还需证明,李兆良要证明他的结论,显然还有很长的中间环节需要补足。
李兆良对“厄蟇、鹤鸵、鸸鹋、美洲鸵鸟”做了知识杂烩式的科普,然后得出如下结论:“(1)《坤舆万国全图》的厄蟇是中国以鸟声命名,包括三种鸟:鹤鸵、澳洲鸵鸟和美洲鸵鸟。厄蟇这名字早于任何西方对同类在澳洲、美洲的走禽的命名。西方最早的记录误写为emia、emei、eme,都不是原来的鸟声,应是传抄错误,后来才更正。(2)按照鸟声,应为uck-moo,不是uck-ma。因为蟇在不同的中国方言可以念ma或mo。葡萄牙人误译厄蟇为ema,证明他们不是首先知道此鸟,而是得自另外一种中国方言……”李兆良的陈述看起来很博学,细究起来却是漏洞百出,毫无逻辑。就算厄蟇真是以中国南方方言记录的鸟类叫声,并将之用以命名该鸟类,我们也不能直接认为最初做出这个命名的就是中国人;a-o的发音差别在多重转译之下是可以忽略的,要以此就论定谁先谁后,证据显然不足;而仅以一个鸟名就断言新大陆的发现,李兆良的设想堪称大胆,但是没有证据的依托。
对于“火鸡”李兆良的解释如下:“火鸡,普通话念huoji,与furkee不太近。但中国南方方言,火鸡念for-gai(粤、客音),fuikey(赣、闽方言),与美洲原住民的发音furkey、furkee几乎一样。中国明代出海的多是粤闽赣人士,因此今天东南亚华裔多操闽、粤、客方言。《明史》中讲多次从东南亚进贡的火鸡是食火鸡的简称。美洲火鸡与食火鸡样子很像,美洲原住民的firkee、furkee其实是明代中国方言‘火鸡’的发音。”李兆良就此又做了深情地表述:“庆幸的是,中国至今保持火鸡这名字,而不是翻译turkey为土耳其鸡、印度鸡等西方用的名字,而美洲原住民亦保持这叫法,把中美一线文化脉络保留下来。”翻译语词的确定有各种可能,音译不是惟一的选择,比如“God-上帝”,就是完美的意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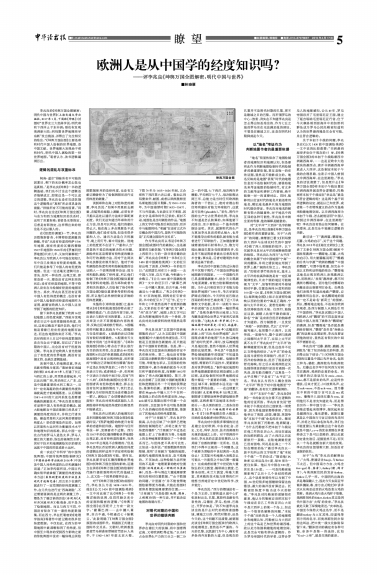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