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人生最大幸福不外乎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事实上,人们的幸福观不一样,所追求的幸福也千差万别,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昔日的幸福未必依然是幸福。对于绝大多数非农业人口而言,久旱也并不一定缺水,雨水的甘霖意义也就变得越来越淡了。他乡遇故知,今日通信交通如此便捷,音信全知,想见便见,难得有出人意外的惊喜。金榜题名即便还没有完全过时,但也没有昔日那种最高的幸福感了。至于洞房花烛夜是否还算人生最幸福之事,大概也是大可商榷的了。然而,有一种幸福似乎更源远流长,更让人兴奋不已、欲罢不能、身心欢畅、流连忘返,我们且回到3000年前的荷马史诗《奥德赛》吧。
《奥德赛》(Odyssey),希腊原文为Odusseia,又译作《奥德修记》,意思是“关于奥德修斯(Odysseus)的故事”。史诗叙述的是特洛伊战争之后,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回国途中历经海上风险,最后一家人团聚的故事。
奥德修斯离开特洛伊后,一路上历险无数,同伴们死的死、散的散,后来他又被迫在卡吕普索的仙岛上滞留了七年。离开卡吕普索仙岛后,奥德修斯被海神波赛冬发现,波塞冬因为自己的独目儿子被奥德修斯刺瞎,发誓要报仇雪恨,于是,这位海神搅动大海,将奥德修斯的筏船击沉。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流两天后,奋力游向一条闪光的河口,爬进一片树林,精疲力竭的奥德修斯在树叶中酣然入睡。
奥德修斯被海水浸泡的心,已经成为一颗“没有了心”的心。现在奥德修斯来到了岸边,这里是法雅西亚(Phaeacian,又译为费埃克斯人,即腓尼基人)国王阿尔基诺斯(Alcinoos)居住的海岛,该岛屿被认为是Corcyre岛,现在被称为“科孚”,是位于希腊西部的爱奥尼亚的众海岛之一。国王的女儿瑙西卡(Nausicaa)在海边洗衣服时发现了他,并把他带到王宫。法雅西亚岛被比喻为世外桃源,Nausicaa这个词和nauticus(在拉丁文中意为“海水的、水上的、航海的”)可能有渊源关系。国王设宴招待奥德修斯,席间盲人歌手德莫多克斯(Demodocus)被请来歌唱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其中也有奥德修斯本人的英雄事迹,奥德修斯听后不禁泪流满面。奥德修斯这样对国王说:
我想没有什么比此情此景更悦人,
整个国家沉浸在一片怡人的欢乐里。
人们会聚于王宫同饮宴,把歌
咏聆听,
个个挨次安坐,面前的餐桌摆满了
各式食品肴馔,司酒把调好的蜜酒
从调缸舀出给各人的酒杯一一斟满。
在我看来,这是最最美好的事情。
哦,原来这就是“最最美好的事情”。在奥德修斯看来,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与朋友们一起宴饮,听着歌咏,吃着美食,述说有关自己的故事,而奥德修斯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希腊语中,‘酒’是‘oînos’,但它最早的形式是‘woînos’,与英语中的‘wine’更接近一些。”这大概也是西方文学中最早关于酒的记载文献之一吧。
德裔美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说:“如果不从历史角度,而从诗歌的角度,我们不如说,历史是从尤利西斯(按:奥德修斯)在法雅西亚国王的宫廷里,倾听他自己的事迹与他遭受的苦难的那一刻开始的。尤利西斯的生活故事,此时成了他自身之外的东西,成了所有人看与听的‘对象’。曾经只是单纯遭遇的事情,此时变成了‘历史’。……尤利西斯倾听他自己生活故事的场景对历史和诗歌来说都是典范性的。”奥德修斯的生活故事,被歌者歌唱就成为诗歌,被人们用文字记载下来,就成为历史。在奥德修斯的历险变成诗歌和历史时,奥德修斯就是见证人,历史近在眼前,因而他激动不已。
英国当代历史学家和作家亚当·尼科尔森(AdamNicolson)在《荷马3000年》(WhyHomerMat⁃ters)一书中写道:“诗(按:《奥德赛》)里描绘的,是任何一个读诗、听诗的人的内心世界。这首长诗的每个部分,都是一则宏大的暗喻。奥德修斯的远航所穿越的,并不是地中海,而是人之一生中的恐惧和渴望。”“《荷马史诗》其实是人生的指南。它蕴藏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深知犯错、任性、虚浮在所难免,再渊博的知识也无法压过对高尚、诚实、正派的渴望……《荷马史诗》其实是一丛人文精神的火焰。它迅疾如电,如奔如流,不断迸出启迪,就像黑夜里引擎的齿轮擦出火花。它们速度飞快,数量巨大,带着暴力和威胁,但每一粒火花都闪烁着人性。”荷马史诗中最智慧的人就是奥德修斯,正如最勇敢的人是阿喀琉斯,最傲慢的人是阿伽门农一样。作为最智慧的人讲述的最美好的事,那自然是毫无疑义的了。这便是歌者的内心世界,亦是人生指南。
然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却不以为然,他在《理想国》中写道:“诗人让一个最聪明的人说世间最美的事是……你想年轻人听到这种诗能学会自制吗?”柏拉图认为,青年人应该有节制:“一般说来,节制的要点是不是一方面服从保卫者的统治,一方面自己能统治饮食色之类的感官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柏拉图认定荷马史诗如此描写是不妥当的。因此,他的理想国是不需要荷马的。于是,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向诗人下了逐客令:
如果有一位聪明人有本领摹仿任何事物,侨扮任何形状,如果他来到我们的城邦,提议向我们展览他的身子和他的诗,我们要把他当做一位神奇而愉快的人物看待,向他鞠躬敬礼;但是我们也要告诉他:我们的城邦里没有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法律也不准许有像他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把他涂上香水,戴上毛冠,请他到旁的城邦去。至于我们的城邦哩,我们只要一种诗人和故事作者:没有他那副悦人的本领而态度却比他严肃;他们的作品须对我们有益;须只摹仿好人的言语,并且遵守我们原来替保卫者们设计教育时所规定的那些规范。
接着,柏拉图以智者的口吻警告城邦执政者:
可是千万记着,你心里要有把握,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甜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或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再然而,柏拉图的理想国终究只是理想国,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美国当代哲学家、诗人罗森说:“从性质上说,柏拉图对话录就是一种诗性的模仿。柏拉图代表或至少似乎代表了所有他虚拟的对象来说话,这与荷马以及悲剧诗人没有什么不同。其次,在相关语境中,苏格拉底清楚指出,如果归于模仿,诗得被逐出城邦。当诗人以自己的声音来表达……城邦大门就向诗人敞开了。”说到底,柏拉图自己也是一位诗人,当他试图驱逐像荷马这样的诗人时,得当心他自己也可能被同样的理由驱逐出去。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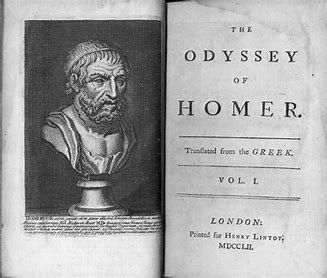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