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个单位称历史三所,归属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学者们,有一个关心爱护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的优良传统。老一代历史学家,如范文澜、刘大年、黎澍、李新等,都曾为《我的前半生》成书前的修改提出过宝贵意见。近十多年来,新一代历史学家,如李洪岩、马勇、朱宗震、步平、汪朝光等,也曾为《我的前半生》的继续出版参谋出力。本文聚焦《我的前半生》,记述这些承继前贤、渊源有自的历史界学术后劲。
才思敏捷的李洪岩
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李洪岩先生,长期在近代史所工作,中经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如今担任《历史研究》主编。我认识他由《中国史研究》主编彭卫先生介绍。那是2006年群众出版社进行宣传推介《我的前半生(全本)》活动时,我找彭卫举荐人选,得知一个从不知晓的名字“李洪岩”,便问,他能写东西吗?彭卫说,他只要写就能写——这是老彭的口头禅,经他给我推荐的人选,实践证明,都是一流的文章作手。
在心里没靠上谱的时候,我曾问询远在上海的董乃斌教授李洪岩如何,他说:“那可是研究钱钟书的。”顿使我心生敬意。未与李洪岩谋面时,我们先通过电话联系。也许是因为他的专业方向为近代史学理论和学术史,经常思考一些比较宏观的问题,所以,他对我在电话里的简短提问,迅速地做出了流畅地回答。他说:“为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也为了尊重作者,到了出版‘全本’的历史时刻了,这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他还说:“出版人不是史学家和读者,出版人的任务是出版一本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图书,其他工作由史学家和读者去做,千万不要随意删改或加注。”对《我的前半生(全本)》中,溥仪描述1955年春“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带着“金晃晃肩章”接见他,李洪岩表示,既然全军授衔授勋在1955年9月底,可见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本《回忆录》没有错误,因为,人的记忆有不可靠之处,如果说溥仪记忆有误,不是编辑的责任,是专家考证的事情,在这个地方要忠实于原著,不能删改,不宜出注。无独有偶,彭卫介绍给我的另一位人物——近代史所民国研究室主任汪朝光先生在电话里也说:“对1955年授衔之事,可在出版说明中举例谈一下,让读者自行辩驳。可能溥仪记忆有误,也可能是他故意这样写的。”上海大学文学院的董乃斌先生则针对《我的前半生》重印时,有学者认为书中“西太后原是一个宫女”的表述有误,宜称“贵人”为妥,在电话里对我说:“溥仪能不知道慈禧太后的情况吗?也许他有意这样说的。”看来,允许创作主体根据自己的爱憎态度稍微变动语言或史实。这是自传体裁有趣的地方。
李洪岩与群众出版社的交往,最为闻名的是2006年底他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文章“在形象中感受深刻——评《我的前半生(全本)》”。约稿时,图书尚未正式出版,我给他抱去一大摞校样看,他一点儿都不计较。这篇文章在群众出版社的编辑中引起了轰动——满社争说李洪岩。该文夸书的作者“善于调动形象、运用隐喻,在字里行间播撒出感性的美,给人极大的阅读享受”“善于调动张力,采用对比的手法,表现对象假矛盾、真虚伪的特点”……这样写法“不但无损于该书的真实性,而且使其达到了更高层次的真实”。我想,李洪岩是在夸他的“一家子”李文达呢!尽管他一再嘱咐我,“全本”的出版说明,不提权利官司,也不提李文达,避免蹚浑水。他说:“这样做,有点儿对不住那位老李同志,但还是这样做较为稳妥。”
然而,李洪岩还是想得简单了一些。《我的前半生(全本)》出版后,他便遭到所谓“家族”势力的激烈网攻,嘲笑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学者、搞钱钟书研究的人,不懂溥仪。李洪岩对此一笑置之。直到四年后,他到群众出版社参加《我的前半生(灰皮本)》研讨会时,当面指责某些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难道在溥仪研究领域还要拉山头搞宗派吗?”我想,应该反过来说——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就不可能懂溥仪。
用“敏捷诗千首”来形容李洪岩的智力类型较为允当。我有两次深刻印象:一次是当我跟他通电话,告诉他群众出版社要出版《我的前半生(灰皮本)》,“灰皮本”是《我的前半生》的祖本时,他在电话里不假思索地做出了反应:“很好!这个本子是末代皇帝的人生观转捩进阶初期,最直接的心迹表露,与后来的《我的前半生》相比较,它有对照价值和历史存真价值。”还有一次是我跟他通电话,请教溥仪研究的核心价值时,他又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应该把溥仪作为新中国思想转变史上的一个案例来研究……”他的“不假思索”是由广泛的出版史知识和深厚的历史理论功底作依托的,使我经常默念于心。
认识宏通的马勇
马勇先生是李洪岩介绍给我的。2013年召开《我的前半生(批校本)》研讨会前,李先生有事不能到会,说:“马勇名气和学问都在我之上,你找他参会吧。”如果说认识李洪岩之前,我并不知晓他,那么,认识马勇之前,我大略听说过他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学术后劲。参会时,我们俩挨着坐,在开大会中开“小会”,便聊熟了。
马勇在会议上的发言我留下了记录:
几十年来,《我的前半生》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是最有影响的一本书,60年代以前对近代史的研究、判断都由于《我的前半生》被改写了,以后整个近代史的叙事框架都发生了改变。所以,它的影响太大了。群众出版社出了这么多版本,意义非常大。建议群众出版社应该再搞一个“汇校本”,把最早的底本找出来进行汇校,可以看到叙事框架的演变过程,看到溥仪的思想演变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因为这几个版本的表述变化还是非常大的。下面谈两个问题:
第一,《我的前半生》的重要价值不在于对中国近代史的现代史的表述,而在于它讲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究竟如何改造战犯的,怎样把战犯的脑洗净的,脑洗净到溥仪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是反人民的。这一点反映的是真实的,无论哪个版本,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怀疑哪些是假话,因为他们确实是真诚地表达忏悔。
第二,溥仪所讲的故事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去年日本一个媒体找我谈溥仪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日本的学者对《我的前半生》研究也很深,我对他们讲,我的基本思想是,书中前面大部分是晚清历史,对于晚清的历史从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应谨慎对待,因为溥仪对晚清的历史没有亲身经历,没有直观的感受,基本都是传闻,多数是听别人说的,如对慈禧的判断、对光绪的判断、对袁世凯的判断等,都与范文澜等那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我们不能说是曲解历史,但已经注入了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溥仪经历的20年代后的历史,如出宫、伪满洲国、战犯改造过程,史料价值最高。所以群众出版社把几个版本出版,将来对近代史的研究会有一个大的推动,而且可读性强,肯定有很大的市场。
对马勇的话进行纵向考察,也是无独有偶。半个多世纪前,历史学家杨东莼就曾指出《我的前半生》“不能算是一部历史作品”,“有不少东西还是写得眉目不清的”。但杨东莼所指为伪满洲国部分,如“作为一个整体,日本侵略者在1931年到1945年这整个历史时期对华政策的政治根据和经济根据;日本皇室、日本政府、日本军阀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什么;伪满朝廷这一批大汉奸的来龙去脉;东京国际法庭的有关史料;李顿调查团究竟起了个什么作用。”杨东莼把溥仪自传提升到修断代史或专题史的高度认识,而马勇是关注晚清史局部重大学术问题并略加轩轾,都体现出史家刨根问底以求“谨而信”的优良传统。
马勇先生对于晚清史研究有独到心得。他重视主体的亲历亲为,且具有符合社会发展的宏观认识,同时心存职业的警惕性。有一次跟我通电话提醒,“《我的前半生》后期叙事,由后来的情绪左右,因此,历史学家辨析史料,不能让回忆录牵着走。许多传记体作品都是后来写的,尤需注意这一点……”
两位逝者——朱宗震和步平
朱宗震先生与马勇先生都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但朱为老资格,1964年本科毕业,马则为改革开放之后朱维铮先生的高足。记得,李洪岩曾对我说,社科院有一些才华横溢、学问淹博的学者,时时冒出天才的思想火花,但并不是在学术实践中都能走到显赫的地位。朱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我与朱宗震相识,也是拜托彭卫先生介绍。他和李洪岩干的是同一件事——给《我的前半生(全本)》撰写书评。他的文章“信息封闭下溥仪的悲剧人生”发表于《南方周末》2007年4月阅读版上。这篇文章是细读文本的产物,看得出来,作者是一句话一句话地捕捉文本内容,抓住“信息封闭”和“悲剧”两个关键词进行分析阐述,得出“从《我的前半生》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实例,信息闭塞是如何使人变得愚昧可笑的”结论。朱宗震有一个稍离文章本身的潜台词:现代国民独立思考能力的提升,有赖于信息的全面开放。
我与朱宗震第二次联系已经是四年之后。他的头发凌乱,面容憔悴,形销骨立——癌症晚期患者,经常去医院做化疗。我心疼他,说,既然这样,您就不要参加《我的前半生(灰皮本)》研讨会了。他说:“我还没死呢,不影响参会,让社里派一辆车接送即可。”在会议上,朱宗震表示对“灰皮本”十分不满意。他原来认为,《我的前半生》及《我的前半生(全本)》对于广大普通读者来说,在知识、教训、审美、价值观方面,是一本好书。但对于以求真为目的的专业历史工作者来说,它在文史专家们的指指点点下,在捉刀人的润色之下,或许不一定完全符合溥仪本人的思想境界。人们从书中看到革命价值观的高度连贯一致,恐怕不是溥仪所能达到的水平,可是没想到,“灰皮本”过头的革命价值观水平令人大吃一惊,这怎么可能是末代皇帝这种身份的人当时的真实思想?由于朱宗震的言论不太对群众出版社的胃口,未留下他的谈话记录。我认为,溥仪是否被中国共产党改造好了,早已形成“千古莫易”的历史定论,溥仪接受改造的真实性也是不容置疑的,我们不能低估他的主观能动性。但,批判精神是一伟大时代学术不可或缺的成分,批判精神缺席,社会就易于堕落,学术也难得进步。朱先生作为一位学者,养成了从不人云亦云而颇富批判意识的习惯,这是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必备的职业素质。
那是个寒冷的冬夜,我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高级警官培训楼门口,目送朱宗震回家:他在夫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钻进小轿车,透过车窗向我挥手致意,脸上呈现出病态的笑容。这一别便是永诀!
我与步平先生相识,属于邂逅性质。2013年冬天,我与群众出版社另一位同志去了社科院近代史所,在一楼走廊里遇见一位年逾花甲、瘦瘦高高的人,便问:“步平先生的办公室在哪里?”这个人说:“我就是步平,进屋说吧。”我向他说了一些有点儿啰唆的话,详谈范文澜那代学者与群众出版社的渊源关系。他尚未听完话便说:“这些我都知道。是要开什么会吧,我肯定到会。”
在《我的前半生(批校本)》研讨会上,社方介绍步平是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他悄悄对我说:“不久前,刚被免职。”
步平在发言中实事求是地梳理了“批校本”中溥仪批校内容上的特点。他有两段议论给我留下的印象较深。一是说,“全本”中“东京国际法庭”审判的内容对研究这段历史很有价值,过去我们只关注日本律师的辩护,“全本”中写了美国律师按照美国审判方式辩护。这次拿到“批校本”觉得更有意义,能够全面了解成书过程。二是说:
战犯改造问题,我以前专门研究过这段历史,还在两位当年的日本战犯陪同下到过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管理所从所长到工作人员见了日本战犯都非常熟悉、亲热,从这些能体会为什么对溥仪改造那样成功,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改造战犯的细节和溥仪的真实心态。尽管溥仪对自己的批判有些过头,但书中还是采纳,反映真实性,这些很有价值。只有把这些历史档案材料展现出来,才能清晰地反映这段历史。群众出版社把有关溥仪的档案资料展示给读者,感谢出版社所做的工作(步平大概指笔者在《中华读书报》《出版史料》和《纵横》杂志发表的一些文章——引者注)。
近年来,有些人搞历史虚无主义,似乎溥仪如果还活着,说一声我没有被中国共产党改造好,他们就满意了。步平通过自己的研究经历,坚决维护溥仪被改造成功的真实性和《我的前半生》撰写的真实性,坚决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底线,同时强调了使用历史档案在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步平去世后,许多报刊发表了纪念他的文章,据一篇文章讲,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唁电中称:“步平前所长作为日中共同历史研究项目中方组长,为增进日中两国在有关历史上的相互理解作出了巨大贡献。”马勇也曾当我面表示了对他的缅怀之情。步平是从黑龙江省社科院院长平调到近代史所的,东北溥仪研究圈的同仁们对他的印象也非常好。
余话
今年将迎来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大庆,也是溥仪特赦六十周年的日子。《我的前半生》的出版为当代溥仪研究奠基,走到今天,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令人感慨。但学海无涯,任重道远,溥仪研究的火种接力燃烧,将在这一领域的传播和接受上写下新的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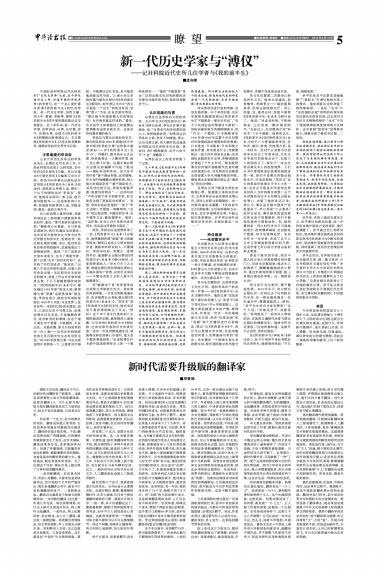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