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桌上厚厚两大册共120万字的《郭书春数学史自选集》(以下简称《自选集》),脑子里即刻浮现出郭书春先生伏案工作、奋笔疾书、几十年如一日从事中国数学史研究的身影。据郭先生自己回忆,他真正开始从事数学史研究工作,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年代,也是一个科学研究走向春天、科学史研究走向春天的年代。四十多年来,郭先生倾注全部精力投入中国数学史的研究工作之中,呕心沥血,刻苦钻研,披星戴月,不分昼夜,终于取得了足以令他自豪和骄傲的巨大成绩。可以说,他与其他同时代的数学史工作者一起,共同书写了中国数学史研究百花齐放的春天。而他的这部《自选集》,正是这百花园中艳丽夺目、笑傲群芳的一枝奇葩。
《自选集》共收入郭先生在数学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81篇文章,按作者自己的编排,分为不同主题的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九章算术》和刘徽研究”,共30篇论文,涉及《九章算术》的体例和编纂、刘徽的数学成就、刘徽的数学理论和逻辑思想、刘徽的思想渊源、《九章算术》的版本和校勘等各个方面。第二部分是“先秦数学及秦汉简牍研究”,共10篇论文,包括《管子》的重数思想研究、湖北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的校勘和研究、北京大学藏秦简《算书》及其他秦汉数学简牍研究等方面的内容。第三部分是“祖冲之和《算经十书》研究”,共5篇论文,涉及对祖冲之数学成就的再评价、对《算经十书》某些问题的澄清以及论重新校勘《算经十书》的必要性等内容。第四部分是“宋元明清数学研究”,共13篇论文,包括对宋元明清时期贾宪、秦九韶、李冶、吴敬、王文素、李善兰等数学家以及《河防通议·算法门》等数学著作的研究。第五部分是“中国古典数学综论”,共19篇论文,涉及数学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古典数学的机械化特点、对贬低中国古典数学的虚无主义态度的批评、回顾吴文俊先生的教诲以及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建所50年间中国数学史研究的总结等几个不同的方面。第六部分是“研究中国数学史的体会”,共4篇文章,重点阐述了作者关于尊重原始文献并认真研读原始文献的治学宗旨和治学方法,并对当前科技古籍整理研究的现状和规划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六个部分的81篇文章虽然尚不是郭先生四十多年数学史研究工作的全部成果——他另有专著《论中国古代数学家》(海豚出版社2017年出版)以及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数学卷》《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中华大典·数学典》等大型数学史著作均没有收入《自选集》中——但仅此81篇文章,就已经涵盖了中国数学史研究的绝大多数核心区域和最新课题,并引领这一领域的探索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然而以上六个部分的研究成果,在作者自己的心目中,并不是轻重相当、分量相同的。郭先生本人最看重的、并且在本书中篇幅最大、所收文章最多的,其实是第一部分“《九章算术》和刘徽研究”。该部分共收入论文30篇,占了全书文章总数81篇的近四成;全书分为上、下两册,而第一部分的篇幅就占了满满的整个上册。足可见其在全书之中的分量之重。郭先生在本书的“自序”中有一个说明:“之所以将《九章算术》和刘徽研究置于各专题之首,一是这是笔者40年来的主要工作,安身立命之所在;二是在《九章算术》和刘徽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研究方法和结论,直接影响到其他专题的研究。”而在我看来,这一部分的工作实在是凝聚了郭先生太多太多的心血,饱含了郭先生太多太多的付出,并且确确实实令人信服地汇聚了郭先生在中国数学史研究领域所作出的众多的创造性贡献。比如在刘徽研究方面,读者可以从《自选集》中清楚地读到郭先生关于这方面研究的诸多个独创性的“第一”:第一次全面解释了刘徽的《九章算术》“圆田术”注文,由此揭示了刘徽关于圆面积公式的证明,并给出了刘徽求圆周率的正确程序;第一次提出并论证了刘徽的极限理论和体积理论;第一次把刘徽关于“率”的思想提到“算之纲纪”的高度来认识,并由此启发并影响了当代中小学数学教材中某些内容的改革;第一次在前人(严敦杰先生)发现宋代时刘徽曾被祀封为“淄乡男”的基础上,考证出刘徽的籍贯在今山东省邹平县;第一次深入探讨了刘徽的逻辑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刘徽是中国古典数学理论的奠基者……再如在《九章算术》的校勘方面,郭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积30多年之功力,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对《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深入细致的校勘。他广搜版本,创见叠出,几番修订,三次出版,最终为学界提供了一部研读《九章算术》所能依据的“最佳本子”(李学勤语)。此外,郭先生的《九章算术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书自2009年12月出版以来,广受读者欢迎,至2017年2月已重印了6次。现在其修订本也已完工交稿,预计很快就能与读者见面。在2015年《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对我的一篇采访稿中,我曾经对郭先生在这方面的工作做过一个评价:“数学史界研究刘徽的专家学者很多,郭书春先生可谓是其中的佼佼者。刘徽的数学成就是通过注释《九章算术》体现出来的,而对于《九章算术》历代版本的考订和研究工作,可以说迄今为止,没有比郭书春先生做得更细、更好的。”(《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开拓和创新——周瀚光教授访谈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3页)这个评价应该是数学史界同仁们的一致公论。
我与郭书春先生相识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迄今已有35年的时间了。那是1984年的初夏,《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的樊洪业先生在重庆主持了一个小型的中国数学史研讨会,郭先生和我都参加了那次会议。会上在讨论刘徽的时候,大家一方面对刘徽的数学理论成就非常赞赏,另一方面又对这一历史现象感到困惑:为什么中国历史发展到魏晋的时候,才会出现刘徽这样一位数学家,来为中国古典数学奠定理论基础呢?大家觉得这个历史现象不太好解释。我当时提了一个想法,认为这可能跟魏晋时期思想解放的社会氛围有关,跟墨家思想在秦汉400年间被禁而到魏晋时重新复兴和流传有关。墨家学派在先秦时就已经具有了理论数学的萌芽和丰富的逻辑思想。刘徽读过墨子的书,他把逻辑学方法融入数学研究,用概念、命题、推理等一系列逻辑学手段来重新解读《九章算术》,这就为中国古典数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并由此而把中国古代数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我的这个想法提出来之后,大家都觉得有点意思,主持会议的樊洪业先生要我回去以后就此观点写一篇论文给他。后来文章以《刘徽的思想与墨学的兴衰》为题,发表在那一年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上。在那次会议上,我与郭先生初次相见,并了解到他在刘徽研究方面实际上已经做了许多扎实的工作,而且他的许多观点往往与我不谋而合。正如郭先生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所说:
我们在那个会上第一次见面。我在1979年研究刘徽割圆术时认为刘徽的‘不可割’与墨家的‘不可斫’是同义语,得出‘刘徽在先秦诸子中,更崇尚墨家’的结论。瀚光先生在那次会上进一步提出,中国古代数学之所以会在魏晋时期出现刘徽这样运用逻辑方法奠定古典数学理论的数学家,与当时思想解放和墨学复兴的社会思潮有关,与墨家逻辑思想在历史上的兴衰有关。这个观点在当时引起了与会代表和会议组织者的很大兴趣。我们在重庆会议上发现一些看法不谋而合,遂引为同道,经常书信往来,互相切磋学问。(郭书春《周瀚光文集·序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出版)
从那时开始,郭先生与我在刘徽研究和数学史研究方面就经常会有一些“不谋而合”的观点和主题,有时甚至达到了某种相当默契的程度。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两人竟然在各自独立且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几乎同时撰写了关于刘徽研究的专著:我的《刘徽评传》(周瀚光、孔国平《刘徽评传(附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杀青于1991年夏天,而郭先生则于1992年3月出版了他的专著《古代世界数学泰斗刘徽》(郭书春《古代世界数学泰斗刘徽》,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除了刘徽研究之外,我们在数学史研究的其他方面也有许多一致的看法,比如对于原始文献的尊重、对《管子》重数思想的研究、对秦九韶人品的评价等等。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学术观点上的分歧,例如对某种古籍底本的选择、对隋唐数学成就的评价等,有时还会争得不可开交,谁也说服不了谁。郭先生长我几岁,数学史功底也比我扎实很多,我从郭先生那里常常能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除了第一部分“《九章算术》和刘徽研究”之外,《自选集》的其他部分也记录了郭先生的许多独创性见解。其中笔者个人认为比较重要且需要特别指出的内容有:第二部分中关于湖北张家山出土汉简《算数书》的研究,第三部分中关于《算经十书》校勘的若干问题,第四部分中关于贾宪数学成就的评价及其思想资料来源,第五部分中关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历史如何分期以及古代数学有没有理论的讨论,第六部分中关于尊重并认真研读原始文献的观点。相信读者在阅读了全书之后,一定会赞赏郭先生的这些独创性见解,并从不同的角度得到各自的收获。
当然,《自选集》也不是完美无瑕的,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和不足之处。就中国数学史研究的整体而言,隋唐数学和明清数学这两个方面,明显是作者所有研究工作中的薄弱环节。读者虽不至于过于苛求,但仍不免感到些许遗憾。
郭先生在本书的“自序”中,曾说起他小时候老家经常贴在门上的春联是:“龙躔肇岁,麟笔书春。”在此,笔者衷心祝愿郭先生这支书写中国数学史春天的“麟笔”,能够虽老弥新,永葆青春!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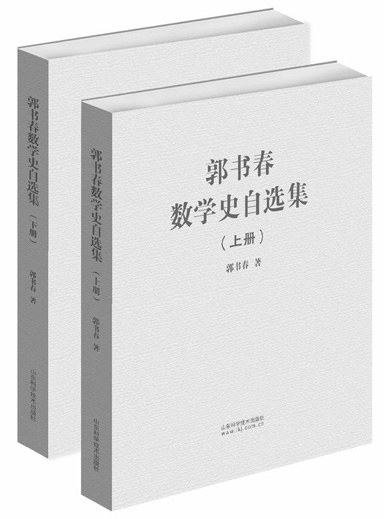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