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历任总统中,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是最难以捉摸的一位。他的思想与性格既单纯又复杂——博学多才却又过分天真,洞悉人心却又自欺欺人,高擎理想的火炬却又放纵不羁。在他去世的1826年7月4日,发生了两个耐人寻味的巧合——这一天恰逢他起草的《独立宣言》签署50周年纪念日,他的前任总统约翰·亚当斯(1735-1826)也在同一天逝世。亚当斯总统临终前的最后一语是:“托马斯·杰斐逊还活着。”这句话着实意味深长。同时代的华盛顿、富兰克林以及后辈的林肯、罗斯福等人大都归档于历史,唯杰斐逊一直属于当下,并以巨大的存在感参与到宪制、废奴、堕胎、医改、环保、平权运动乃至全球治理等美国各个时期内政外交的重大议题之中,成为检验各种信念、原则、真理成色的试金石。杰斐逊的“当下性”让历史研究者难以对其盖棺论定,只好称他为“多变之人”或“美国伟大的凡人”,认为其真正的遗产是“对遗产的否定”。正如亚当斯总统之重孙、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所说:寥寥几笔就能勾勒出美国早期所有总统的形象,唯有杰斐逊是个例外,“只能用笔尖一笔一画地画,画像是否逼真取决于能否画出变幻、飘忽的阴影”。
美国当代历史学家约瑟夫·J.埃利斯的“国家图书奖”获奖作品《杰斐逊传:美国的斯芬克斯》并未对杰斐逊的整个生平及其时代进行工笔细写,而是选取传主一生中的五个重要时期,充分利用包括DNA检测报告在内的研究成果,揭示其思想和行动,辨析其价值观和信念,评估其效应和影响。在作者笔下,杰斐逊之思想情感波澜、家族生活变故与美国革命政治风云相互交织,跌宕起伏。可以说,此书不但捕捉到了杰斐逊面孔上“变幻、飘忽的阴影”,也勾勒出了美国革命时代政治家的群像。
作者提醒我们,“后见之明”往往是读史的陷阱。《独立宣言》的创作是美国历史上的神圣事件,而在当时却并非紧要。1776年夏天,大陆会议的当务之急是制定各州宪法以及与法国或西班牙结盟。作为弗吉尼亚州最年轻的代表,杰斐逊被指派起草《独立宣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他合适的人选(如亚当斯、富兰克林等)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围绕《独立宣言》的光环是后来才形成的。然而,对杰斐逊个人来说,撰写《独立宣言》却是顺理而成章。他此前撰写的两个文本都已强烈地预示了《独立宣言》中的思想。其中,创作于1774年的《英属美利坚权利综述》通过考释诺曼征服之前“自由和谐的”撒克逊时代,抨击英国王室对殖民地权利的历史合法性,证明“英国议会无权对我们行使权力”。创作于1775年的《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公告》则建立了一种基于“道德二分法”的叙事模式:“邪恶腐败的”英国政府密谋剥夺“天真善良的”殖民地人民的自由。作者指出,三个文本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其核心是“辉格党历史观”。杰斐逊青年时代阅读了大量关于辉格党历史的经典著作,它们所描绘的田园牧歌式的“撒克逊代议制政府”迎合了杰斐逊骨子里的浪漫主义乌托邦倾向。
《独立宣言》这份奠定美国政治基础的文件同样带有杰斐逊式的浪漫色彩,其中关于自然权利的宣告甚至具有宗教教义的特征:“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作者指出,虽然深受洛克的影响,杰斐逊的政治愿景却比自由主义更加激进,“其动力源自一个年轻人心存高远的目标,不愿与不完美的现实相妥协的浪漫情怀。”(第78页)
1784-1789年,杰斐逊与本杰明·富兰克林和西拉斯·迪恩出使法国。在巴黎,杰斐逊与留在美国的门徒詹姆斯·麦迪逊、詹姆斯·门罗、威廉·肖特定期通信往来。尤其是与麦迪逊之间的信件交流开启了他们长达50年之久的合作关系。后者继杰斐逊之后成为总统,随后门罗接替麦迪逊任总统。19世纪的前24年,美国总统大位一直由杰斐逊主义者占据,形成了所谓的“弗吉尼亚王朝”。
出使巴黎使杰斐逊缺席了1787年的制宪会议,但也赋予他超然的视角看待美国关于制定宪法的讨论。他在给麦迪逊的信中说:“对于外交事务,我们团结成一个国家,但在国内事务上,可以有所区别,这是中央政府与州政府合理分权的要点。”(第129页)对宪政制度的思辨让麦迪逊、詹姆斯·威尔逊、汉密尔顿等政治思想家沉迷其中,但并没有激发出杰斐逊的思想火花。他追求的是个人拥有充分自由的乌托邦,将任何形式的外在的政府权力都视为灾难。麦迪逊主张的社会平衡与杰斐逊对个人自由的追求是相冲突的。虽然杰斐逊后来听从了麦迪逊的建议,支持批准新宪法,但又坚决主张权利法案。最终,麦迪逊也接受了杰斐逊的主张,且成了《权利法案》的起草者。可见,杰斐逊与麦迪逊之间并非简单的导师与门徒关系,而是亦师亦友。
在与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的斗争中,杰斐逊与麦迪逊之间“伟大的合作”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他们在1790-1794年之间建立了共和党(现代民主党的前身),从而与联邦党(现代共和党的前身)相抗衡。在崛起的共和党中,杰斐逊是“大元帅”,麦迪逊是“将军”,前者在战略上精心策划,后者在战术上正确实施。在反对汉密尔顿的融资计划和建立国家银行的提议上,杰斐逊运筹帷幄,麦迪逊冲锋陷阵。
1794年,杰斐逊卸任华盛顿内阁国务卿,“归隐”老家蒙蒂塞洛(Monticello),幻想成为西塞罗式的人物,躲在幕后影响美国的走向。然而,汉密尔顿主推的英美《杰伊条约》(JayTreaty),激起了杰斐逊重返政坛的决心。《杰伊条约》承认了英国在北美大陆内河航行的自由和在西印度群岛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否定了杰斐逊任国务卿时制定的对英国进口货物征收关税的政策,却保留了英国对美国征收进口关税的权利,使美国丧失了在领土主权和贸易方面的部分利益。汉密尔顿主导的亲英政策与杰斐逊主导的亲法政策相对立。蒙蒂塞洛很快成为共和党人反对条约运动的总部。虽然条约最终被参议院批准通过,但该运动也为杰斐逊日后竞选总统做好了铺垫。
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告诉我们,《杰伊条约》使得美英避免了在独立战争结束后的短时期内再次爆发战争的危险,为刚独立的美国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到1812年英美战争时,美国已经变得更加强大了。然而作者指出,杰斐逊反对《杰伊条约》具有性格与思想上的深层原因,根据其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道德二分法”,美法同盟代表的革命浪潮乃是浩浩天命,不可逆转,而英国则是天生的反革命力量,违背了历史潮流。
1797年,华盛顿卸任总统。经各州选举投票,亚当斯接任总统,杰斐逊任副总统。虽然同属于联邦党人,亚当斯其实是反对汉密尔顿的银行和融资计划的,对《杰伊条约》的态度也不积极。联邦党人的内部分裂给了共和党可乘之机,从而使杰斐逊在1800年的总统竞选中获得了胜利。杰斐逊从华盛顿那里学到了积极的经验,从亚当斯那里吸取了负面的教训。他践行共和主义“小政府”原则,其治理模式力图掩盖行使权力的痕迹——总统如同轮毂,各部门如同辐条,国家事务在轮辋处完成,但全部由轮子的中心来监管。这个系统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全局的掌控,又无须参与到具体事务之中。(第244页)
杰斐逊后来将他的第一次胜选总统称为“1800年革命”,认为1776年革命改变了政府的形式,而1800年革命改变了政府执政的原则。他的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是除了《独立宣言》之外他所创作的最精巧、最雄辩的文章。其天才之处在于非常概括地描绘了美国的政治愿景,而忽略了具体细节。杰斐逊所推崇的“纯粹共和主义”(purerepublicanism)执政原则是曾一度被联邦党人所破坏的“1776年精神”的再现,但他高明地宣称:“我们都是共和主义者(republi⁃cans)——我们都是联邦主义者(federalists)。”“纯粹共和主义”不代表与联邦党人的彻底决裂,也不代表从根本上否认宪法所规定的政府结构。就连汉密尔顿都认为就职演说“坦诚地化解了过去的误会,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新总统保证不会进行危险的改革,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会沿着他前任的脚步继续前进”。但必须指出的是,杰斐逊激进共和主义的根本信念并未改变:国家活力的唯一源泉不是政府本身,而是政府所依赖的广泛的民意。(第238页)
直到生命的最后十年,杰斐逊才对“1776年精神”和“纯粹共和主义”信念进行了新的提炼和阐发。作者写道:“这时,杰斐逊第一次提出了这个新的政治观点,最终将他的名字与之联系在一起,永远地为后人所熟知。他一直称作的‘纯粹共和主义’其实是‘民主’,他在‘1800年革命’中实际所做的就是在联邦党人背叛美国革命之后重新恢复革命的民主精神。”(338)“民主”一语并非杰斐逊首创,但他赋予该词以现代意义(在当时该词还带有暴民统治或无政府色彩)。杰斐逊明白,如果民主要成为一种政治信仰,必须保持一种神秘感(这是其一贯做派)。直到1824年,为回应弗吉尼亚州修改宪法的呼声,杰斐逊才不得已将民主的范围界定为“所有成年白人男性”。(第340页)
杰斐逊的矛盾之处既反映了其时代局限性,也反映了其政治上的灵活性。1803年,杰斐逊“绕过宪法”从拿破仑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使联邦国土扩大一倍。同时获得授权在该地建立临时政府,这是独裁君主般的权力。
由此案引发的1819年至1820年的密苏里奴隶制问题,同样有悖于杰斐逊推崇的“1776年精神”。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奴隶制,却又采取将奴隶制“扩散”到新州的办法来“消解”它。这种牵强的做法反映了杰斐逊对奴隶制问题拖延和拒绝的态度。无疑,奴隶制的扩散对半个世纪之后的南北战争负有历史责任。然而,当亚伯拉罕·林肯最终决定解放奴隶时,指引他的道德灯塔不是别人,正是杰斐逊(第341页)。
马克思曾把路易·波拿巴比作戴着斯芬克斯假面的骗子(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年版第13卷192页),指其不过是反革命的喜剧丑角。本书作者将杰斐逊比作美国的斯芬克斯,亦深得春秋笔法。只不过,杰斐逊是真正的斯芬克斯——他以高超的语言技巧、灵活的政治手段,试图弥合自身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巨大分裂,这种努力充满了悲剧意味。观其一生用舍行藏,作者不虚美、不隐恶,公允地诠释了杰斐逊永恒的精神遗产:“我已经在上帝的圣坛前许下誓言,永远反对笼罩在人类心灵之上的任何形式的暴政。”(第10页)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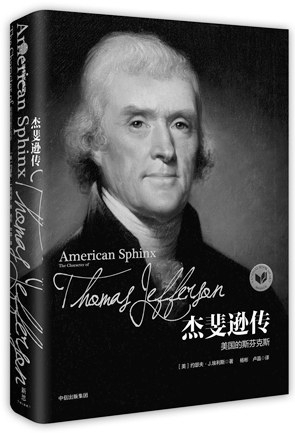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