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批评界曾出现过热闹的“双打现象”:潘凯雄、贺绍俊,李洁非、张陵,费振钟、王干,辛晓征、郭银星,汪政、晓华,盛子潮、朱水涌,王斌、赵晓鸣……1989年1月4日,广州新创刊的《沿海大文化报》,约潘凯雄主持了一个栏目,叫做“双打世界——关于人、文学、文化的对话”。在这个栏目里,潘、贺,费、王,辛、郭,王、赵,四组“双打”一共写了四篇小对话文章。
潘凯雄在“开栏赘语”中说:“近些年来,文学批评领域内两人携手、联袂为文者日渐增多,读者不时能在报刊上领略到一对对‘双打选手’的谈锋。……出现在‘双打世界’里的文章将都是一些短小的对话体,我期待着在这里经常地闪现出智慧碰撞的火花,更期待着广大读者对她的支持与帮助。”
由此可见,在80年代末,文坛上已经将“批评双打”作为要强调的一种现象,并且还开列了专栏集中“双打”,批评界也看好过“双打”的力量及其特有的形态。
是从什么时候起,“双打”陆续解散?时光流转到今天,“双打”辈出的现象也难以再现。是文坛热点不再那么紧迫,个人之力足以应付,还是当年那批青年才俊,均早已独当一面?总之,今天我们回顾当年的“双打”,不是缅怀1980年代的文化氛围,更非希望回到过去,而是希望1980年代自由的意志,平等的讨论,真诚的对话能再一次复活,让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更加真诚并充满力量。
“批评双打”之潘凯雄、贺绍俊
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九楼的办公室,潘凯雄回忆起当年和贺绍俊的合作,脑中不断回放着1980年代的文学场景。
是的,时隔30年,当两人将合作的文章结集出版时,潘凯雄首先想到的书名就是“1980年代文学现场”,那个回不去的文学现场、生龙活虎的文学现场、宽容和谐的文学现场。
1983年,潘凯雄和贺绍俊同时被分配到当时的《文艺报》理论组工作,成为中国作协在新时期第一批大规模引入的大学毕业生。
“作为中国作协机关报的《文艺报》在某种意义上既是一个文艺界信息的集结地,也是从事文艺研究与观察的重要位置,集聚了一大批人才。”提起那时的《文艺报》,潘凯雄对当年的领导和同事如数家珍:冯牧、孔罗荪、唐因、唐达成、刘锡诚、陈丹晨、吴泰昌、钟艺兵、雷达、孙武臣、高洪波、彭加瑾……
《文艺报》每月有三个会:选题会,落实每一期刊物选题;阅读交流会,基本上是张三谈短篇,李四谈中篇,王五谈长篇……大家把各自本月内看到的好作品提出来和大家交流共享;出差汇报会,不论谁出差回来,都要交流一下当地文艺界的种种动态,信息量高度集中。《文艺报》内部争论也很激烈,潘凯雄曾目睹唐因在会上急得面红耳赤,跺着脚说:“你们怎么这样!你们怎么这样!”但争论完后和气依然。大家观察、思考、研究,提出选题、写成文章。在这样一种学习、平等研讨和坦诚交流的氛围中,不受感染是不可能的。
记不清是如何开始合作写作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事先“预谋”,也没有刻意策划。在潘凯雄的印象中,当时他和贺绍俊都还是单身,一天中的许多时间都呆在办公室,常常说到某个话题,热火朝天聊半天,舍不得浪费,便形成文字。因为内容是讨论的产物,两人无意识、也是不自觉的,谁也没有单独署名。
当时学术氛围很好,大家也很恪守职业道德,写出文章如果不是自己刊物所约就只会向外投稿。直到现在,潘凯雄仍然清楚地记得,《文学评论》的地址是“建内大街5号”。1985年,俩人合作的第一篇长文完成后,在信封上郑重写下这个地址寄给《文学评论》编辑部,第二年就发表了。在文学研究的权威刊物初战告捷,这给了他们很大的信心。
如果说前一两篇文章的合作还是自然状态,那么后来就不同话题讨论合作已然成为约定俗成。谁执笔,谁便署名在前。文风于是根据署名先后呈现出些许差异,一般情况下,贺绍俊当时锋芒更甚,潘凯雄则略显温和。潘凯雄若执笔,贺绍俊会将文章改得“冲”一些;贺绍俊若执笔,潘凯雄则会将锋芒收藏一些。总体上,他们更注重基本观点与学术表达上的一致,至于文风则未必那么讲究统一。
说起那时的“批评双打”,潘凯雄、贺绍俊绝非“绝配”,李洁非、张陵,费振钟、王干,辛晓征、郭银星,汪政、晓华,盛子潮、朱水涌……因而也有人将此称为1980年代文学批评界值得研究的一种“双打现象”。
潘凯雄认为,特定的时代背景很重要,这样的组合,是思想解放,平等交流、自由探讨蔚然成风,人际关系单纯简单的结果。每个月拿到稿费(当时月工资50余元),贺绍俊和潘凯雄总是一人一半,署名前后无所谓,也从不考虑字数的多少或谁的付出多少。他们曾批评过莫言的《红蝗》“毫无节制”,也指出张宇的作品过于“疲软”,那些文章是犀利尖锐的,也是友善平和的。这一切都不影响他们和批评的对象之间照样称兄道弟友情依旧,彼此间还以此开着善意的玩笑。
1994年,潘凯雄调至《经济日报》,置身文坛之外,写作更为放松,文风也趋于鲜明。尤其是转到出版业之后,他的“终审札记”解剖畅销书背后的秘密、直陈平庸图书的共性,既有文学的专业眼光,也有社会、出版、市场的宽阔视野,多了些复合的成份。
曾经有人戏说潘凯雄,从一个曾经先锋的青年评论家“沦落”到市场化的位置。对此,潘凯雄回应说:“我有我的职业逻辑。我提供的纬度,现在一般的评论家未必提供得了。有人认为畅销书和纯文学是对立的,其实也不尽然。畅销书的确多类型化,但优秀的类型化图书,细节上都很文学化,而且是把某一种文学手段推到极致。所谓经典其实也不是单一的,不同的类型有各自不同的经典。我的文章‘不专业’了,但是观察文学的角度和视野更宽了。”
因为职业的原因,学术文章则写得少了,潘凯雄与贺绍俊的合作也随之减少。有趣的是,和以往比,他俩的风格似乎调了个个儿。潘凯雄更冲了,贺绍俊则偏于温和。
对此,潘凯雄的分析是,过去文风宽容平和,和自己胆怯内向的性格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承担的工作不得不与人交流,胆子也放开了。他写过《梁凤仪何以走红》,批评梁凤仪财经加言情的小说如何肤浅;也写过《不读书凭什么说话》,质疑那些还没等毕淑敏的《拯救乳房》出版就四处拿标题恶意炒作的轻狂。
《批评双打——八十年代文学现场》(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时潘凯雄已担任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回望当年的作品,他感觉“有点嫩。”收入集子的近九十篇文章,有三分之一带有学术研究,有些文体现在看来感觉生硬,“那时想方设法引经据典,一是环境使然,二是年纪尚轻,三是缺乏自信。”潘凯雄说,如果现在,他可能会用自己的话去写文章,更直白晓畅、也更老道。
但是,有些作品只能放在那个时代,那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时代。
90年代后,贺绍俊先后担任《文艺报》副主编、《小说选刊》主编,2004年调至沈阳师范大学,主要精力投入于当代文学评论。如今,文学批评已成为贺绍俊的职业,更是他的思维方式。他早已习惯用批评的眼光面对生活、面对世界。30年时光荏苒,他依然深深怀念当年的“双打”经历,尽管各自的经历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之间交流时也依然能时时感觉到思想碰撞的火花。在贺绍俊看来,作为批评双打选手中的一对儿,他们也曾觉得那个时代热衷于批评双打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俩重新捡拾起过去的那些合作成果,在缅怀1980年代那一段峥嵘岁月的同时,多了一些理性的思考。”他想,有那么多批评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双打”的方式进行文学批评,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与1980年代的文化精神有着某种契合。那时候没有QQ,没有微信,没有互联网等迅捷的交流方式,但同行们仍能通过书信或电话,进行不同空间的交流和讨论。而且在刚刚经历了一个知识荒芜的年代后,大家开始参与到文学批评时,备感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这样的条件客观上带来了一种良好的讨论风气: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批评双打就是在这样一种良好的讨论风气中悄然敲定下来的。
“由此看来,促成一对又一对的批评双打的外在条件是:自由的意志,平等的讨论,真诚的对话和互补的思维方式。这一切,应该同时也是1980年代文化精神的重要内涵。”贺绍俊说,当然,这些并不是1980年代文化精神的全部,但却是格外珍贵的部分。这些内涵后来都慢慢地弱化甚至消失,所以1980年代那种“批评双打”辈出的现象也就难以再现。今天我们一谈起1980年代便流露出浓郁的缅怀之情,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想要回到过去,而只是希望1980年代那些珍贵的精神内涵能在今天再一次复活。当然再一次复活的目的也决不是为了产生出新的“批评双打”,而是为了让文学批评变得更加真诚也更加有力量。
“批评双打”之汪政、晓华
时至今日,那些联系在一起的名字有的分开了,有的已经离开我们,仍有两个名字还在我们的视野中活跃着,他们的合作亲密而持久,至今,这一对伉俪批评家已经在中国文学批评的舞台上活跃了近四十年。他们是文坛几乎无人不知的文学伉俪:汪政,晓华。
“阿城自然不是在作文化史,但他试图写出一段历史,写出在这一段历史中,文化怎样遭到残害,而为文化人类学家看不起眼的芸芸众生又是怎样作为文化的主人,默默地抗拒着野蛮的迫害,顽强地追求着知识和文明,正是他们延续了我们的文化史,证明了文化的存在和人的伟大!这是阿城思考的独特之处。”这是署名“晓华汪政”发表在1985年06期《当代文坛》上的评论文章《阿城的思索——漫说〈棋王〉〈树桩〉〈孩子王〉》,一语中的道出阿城写作的独特意义。这是他们关于当代文学发声的第一篇合作文章。
早在读大学期间,汪政就开始文学批评活动,研究红学、古典诗词和当代诗歌,在《红楼梦学刊》等发表论文。因为在学校当语文老师,还发表了一些关于语文教育教学研究方面的文章。汪政将选择文学批评的原因归结为,一方面是受老师的影响,南通学界的“三驾马车”徐应佩、周溶泉、吴功正影响了几代学生;另一方面,也受当时的文学氛围影响。1980年代,他和晓华同在江苏如皋师范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就与志趣相投的同事一起开展语文教学的实验活动,强调语文教学应该与生活结合在一起,有时甚至将规定的教材放在一边,只凭一套学校推荐的古典文学读物和他们编选的当代语言作品进行教学活动。给学生们讲授文学概论和写作,他们要求学生关注文学理论的当代发展,关注当代文学创作的现状,并且要对当代文学进行分析和读解。这与后来的他们共同出版的《如何抵达文学的现场》一脉相承。
汪政曾经有一个观点:从事当代文学批评要“在场”,要像刑警一样“出现场”,获取第一手的痕迹、物证,然而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他和晓华正是和当代文学保持亲密无间的接触,才能深刻体会文学的细微变化,也因此,他们的批评始终保持着新鲜的活力。从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从莫言、马原、张炜、贾平凹、史铁生、余华、周梅森、虹影……他们从日常叙事和艺术叙事的关系发现中国文学叙事独特性的特点也一以贯之。在《游戏会不会失传》一文中,他们写道:“小说不能只是纸上的书写,也不能只是小说家操练想象与语言的地方,它应该生活在现实生活之中,是生活的一部分,有人情味,有烟火气。这与深刻与否无关,将现实、生活与世俗和思想的深刻对立起来以至搞得水火不容是没有道理的,是对小说艺术的极大的不信任。”
2001年,汪政和晓华分别调至江苏省文联和作协,目前,汪政担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晓华则是《扬子江诗刊》副主编。多年来,他们自然意识到创作的变化。“80年代末往后的二十多年的文章还觉得比较满意,那期间写了大量的作家作品论,批评做得比较实在。”更为关键的是,他们一直关注着中国文学的变化,从未没有缺席过。
评论家贺仲明就注意到,汪政、晓华的批评文章,观点往往平和而有个性,敏锐而不失温文,方法更是落到实处,从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入手,仔细而真诚。所以,它们不只使人感到思想的警醒,更能使人感受到一种理解的温情。“他们往往能够将自己的思想情感融入到被批评对象当中,深入到作家的内心世界和作品的核心中,其中虽然也有批评和否定处,但可以体会到批评者的观点是发自内心,其峻切和执着使人感动,那些以理解和真诚为前提的结论也使人信服。”
“对我们来说,理想其实并不高,能做到在场,有问题意识,能够将自己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融入自己的文字就已经很满足了,如果能够将批评与当下的社会话语联通起来,那更是一种理想。”作为跟踪中国文学三十余年的批评家,汪政、晓华所推崇的文学批评理念涵盖了从中国古典到现代西方,当然,他们也注意到,中国的文学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几种文学力量分而治之的状态已经成型。讨论文学,如果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所谓纯文学已经不能全面地说明问题。关键不在于是否承认这样的文学格局,而在于面对它们,我们如何进行描述与判断。正是在这方面,显示出传统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缺憾,更是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纯文学食物链中成长起来的批评家们的严峻考验。如果说在80年代,他们比较看重观念与方法,是那一时期批评大势所趋的话,到90年代,他们更加看重批评与自己生命的联系,也更加尊重批评对象,注重表达出自己对批评对象的真实感受。尤其重要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火气也渐渐退去,对所有的文学现象也变得很宽容,甚至为了再现批评对象的真实存在,会牺牲概念与思辨,宁可代之以描写和叙述。
“我们是一家人,讨论比较方便,谁在阅读中发现了问题都会提出来讨论,觉得有价值,就会进入写作,一般来说,谁愿意写,谁执笔,谁的署名在先。”汪政说,长期的合作,使两个人的文风逐渐互相模仿,就像人的面容一样,所谓夫妻相,就是在一起待得时间长了,就会不自觉地互相模仿,所以他们俩人在评论上的风格差别不大,但是细心的人会看出来,一个偏于理性一些,一个偏于感性一些。有的时候一个人写了半拉子,另一个人就接着写,至于比较长的文章,会分成几个部分,各自领一部分去写再合成,没有一定之规。
“双打”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观,是当时文学热闹而有趣的一种体现。有人说双打出镜率比较高,客观上也是如此。“双打”带来的优势是很显然的,毕竟是两个人的智慧,1+1必然大于2。但也会带来一定的弊端,因为对同一个问题,两个人的看法不见得能完全一致,这中间会有妥协,“如果两个人妥协得没脾气,那就一直双打下去,如果两个人妥协不下去了,那就会分手,这都很自然。”汪政说,长期合作,默契是肯定的,但也有争论,妥协不了就不写,或者就一个人写,他们独立署名的文章也不少。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许多当年的同行早已另谋高就,而更多的则进了学院,做起了学问。像汪政、晓华这样对批评称得上从一而终的人现在可算是凤毛麟角。“有时也不免孤独,而更多的则是在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但汪政和晓华持之以恒从未放弃。因为如果放弃,可能意味着对自己几十年生命价值的怀疑甚至颠覆。这对他们来说未免残酷。然而实际上,不但曾经一路同行的兄弟渐走渐少,批评“双打”更为稀缺。对此,汪政和晓华的看法是,主要是现在的评价体系的原因。1980年代评价体系包括职称、学术称号都没有,批评就是批评,很少被看作是什么学术成果,也很少与个人的评价体系关联,大学办学规模扩大之后,对文学批评的格局改变最大,大部分批评家都到大学做教授去了,都要接受大学的科研制度的管理,合作的成果如何计算,就不太方便,这就是原先的双打渐渐分离,而新的双打很少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李新亮用“款款而行,从容不迫”形容多年来汪政、晓华的文学批评。“在文学批评理念上,不固执已见偏执一隅,秉持开放多元的理念;在文学批评情怀上,从现实出发,回到文学现场;在文学批评姿态上,满怀着同情之理解面对文学批评对象,追求务实而不凌虚蹈空。”一言以蔽之,行走在当代文学批评的丛林里,汪政、晓华从未迷失自己的道路,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心底一直有文学批评的本色。
批评双打之其他
1985年,辛晓征尚在辽宁省文联理论研究室工作,郭银星在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和汪政、晓华一样,他们夫妻俩第一篇合作评论的对象也是阿城,当时,阿城的“三王”已经发表。辛晓征和郭银星当时各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同一期上,所以,虽然是共同讨论,互相修改,但要同一期发表,还是各自署名的。此后,凡是他们共同讨论,一人执笔,互相修改的文章,发表时就一起署名了。因为已经有比较充分的讨论在先,另一人的修改不会是颠覆性的。辛晓征有时候会尖刻地指责郭银星没有写明白他的意思,郭银星有时候会“含泪”再去重写一遍。
辛晓征和郭银星认为,更值得他们回顾的事,是当时搞批评的人与作家的关系:“比如我们,合作写过两篇不怎么像样的阿城小说评论,接着就与阿城成为好友,那时到北京坐着公交车到他在厂桥附近的平房里聊天,吃他做的云南辣椒面,是很随意的事。马原因为是同学,关系更深,他们夫妇拉着手来我家,大着嗓门聊到凌晨三点尽兴而归,是很经常的事。但是,这些从不影响我们对他们的小说说三道四,更不影响我们在文章里经常或明或暗地刻薄一下。我们那时都还年轻,不刻薄一下,怎么能显示出我们有理想文学的标准和批评的深刻呢?”
1996年,郭银星在中国社科院博士毕业后就职于中国大百科出版社,现为社科学术分社社长。而辛晓征已自中国版协退休。他们认为,归根结底,批评家与作家,包括批评家自己的实际关系表达着某个时期文坛的性质。人们经常说起八九十年代文坛的活跃、热络、有情有义,真正怀念的恐怕不是“单打”“双打”,而是作家持着作家的本分,批评家守着批评家的职责,大家互相敬重又各自砥砺前行。那样的文坛,“单打”也好,“双打”也好,都是惬意的。
学者李洁非回忆与张陵的合作,是在1980年代初期他到新华社之后,业余写评论。1983年,参与“现代派”问题争鸣,李洁非写了一篇赞成“现代派”的文章,投到当时徐迟先生任主编的武汉《外国文学研究》杂志,被发表,并接获徐迟先生一封亲笔信。此后,与同届分到《参考消息》、有相同兴趣的张陵日夜切磋,开始合作,共同属名,在《当代文艺思潮》《当代文艺探索》《当代作家评论》《读书》《上海文学》等处发文章,合作持续到1987年。当时关注重点在文艺思潮方面,是受时代的激昂,颇多前瞻性、宣言性观点,年轻气盛,指点文坛,在文坛颇有影响。
在李洁非看来,1980年代的文学,思想碰撞激烈。“那时我二十四五岁年纪,脑子里还有理想主义,把文学看得蛮高,觉得它如何如何,当时觉得文学病在思想浅薄,认为搞批评比搞创作更有意义,能更直接地介入文学的思想现实。这都是年轻气盛的想法,所谓把思想看重看高,无非是对胸中那些一己之见很在意。到了1980年代结束的时候,慢慢觉得执着于个人的东西蛮可笑的,它在现实世界面前分量很轻,根本不足论,与其用主观的想象和规划要求文学,不如脚踏实地研究些问题,认识事实。”认识到这一点,李洁非开始一点一点疏离文学批评前沿,后撤到一些专题的研究上。
这个变化出现在新世纪之初,李洁非留意到“延安文艺史”的课题研究,发现延安那段历史的复杂性、丰富性、重要性不是一个角度就能概括的,特别是自己搞当代文学研究,总会为现代文学如何演变成当代文学这个样子而心存疑惑,一直找不到根子在哪里。涉猎延安时期文学艺术研究对他来说其实是为当代文学起源的一种寻根,循着这样的契机,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才有他后来的一系列文章,才有《典型文坛》和《典型文案》。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的印象中,王干与费振钟这对双打崭露头角,一出场就带来江南清新之气。
“他们的文章直接犀利,敏锐中还透着醇厚之味。费振钟稳健、深邃,是智慧型的批评家,他尤其重视知人论世,常能看到作家背后的文化与心理,他的评价中肯而准确,令人信服。他们俩人的合作,经常有好文章问世,在1980年代中后期,他们的言说给那些新奇的文学现象提示了富有活力的解读。费振钟在1990年代激流勇退,有些可惜,他具备做一个优秀批评家的良好素质,艺术敏感、见解不凡,有风骨,有情怀。双打终结之后,王干就开始单打独斗,并且显出更加自由机敏的风格。双打的集体解散委实可惜,这表明文坛的节奏放慢,热点不再那么紧迫,可以个人之力来对付。同时也表明,当年一批青年才俊,也都长大成人,独当一面已成气候。”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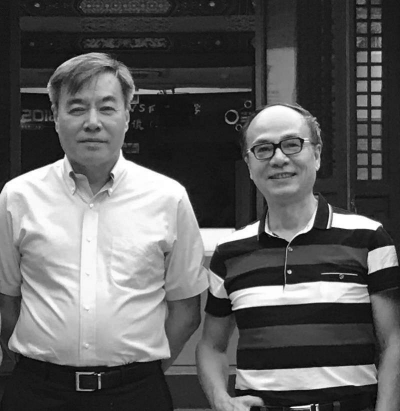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