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腔北调(167)
江:
刘兵兄,这些年你在“科学编史学”的大方向下,指导学生做了一系列各种方向的研究,成绩斐然,有目共睹,实属可喜可贺。这本《科学修辞与科学史》就是这方面最新的成果之一。
说实话,“修辞”这个字眼,是我比较常用的“修辞”之一。我比较喜欢将一些别有所指的、言过其实的、空洞的、煽情的……表达方式称为“修辞”。比如“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文青色彩的空洞话语,就会被我视为“只是一种修辞”。当然,这与古人“修辞立其诚”的说法似乎有相当的距离。
但事实上,在当代汉语中,人们在很多情况并没有将“修辞”视为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将它当作某种“现代”的表达——在所谓的“现代汉语”中,我们的“语法”都是借用西方术语和概念来表达的,“修辞”也在其中。
数十年来,作为一个科学史研究者,很多时候还是一个拿着“科学史牌”猎枪的越界狩猎者,我经常在各种媒体上谈论与科学有关的话题。在这些谈论中,“修辞”当然是经常会用到的工具。比如为了加强效果,我会对媒体说“科学已经告别纯真年代”或“科学就是我们厨房里的切菜刀”这样的话语,毫无疑问,这时我使用了“修辞”。
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中,我翻开了这本《科学修辞与科学史》,它马上让我产生了一些朴素的联想,又很快让我认识到它完全是在讨论另外一些问题。
刘:
说实在的,我真是有些迫不及待地想听听你提到的你所阅读此书时产生“朴素的联想”,以及你又“认识到”的它在讨论“另外一些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
其实,语言总是很微妙的,词义总是很多义的,尤其是对于某些常用词,某些常用概念,在我们最经常使用的语义之外,在专业的学理意义上,经常还有另外的含义和所指。我想,“修辞”这个词也正属此类。
从谭笑的这本《科学修辞与科学史》中,我想你应该已经看到了这个概念的复杂性,及其在悠久的历史中人们对之认识和理解的变化。或许,在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甚至哲学研究领域,人们从学术的意义上谈论此词的会相对更多一些。但在科学史领域,至少就我所见,这还是目前从科学编史学的角度对于修辞这一科学史的编史视角或者“进路”所论述最系统、全面和深入的一部专著。
科学编史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科学史著作(及其撰写)和科学史家,但科学史的直接对象毕竟是科学,因而其哲学色彩还是比较浓的,也无法脱离开哲学的分析和思考,特别是对科学本身的性质的分析和思考。当从修辞这一视角来考察科学时,也就发现了过去人们一直重视远远不够的科学的这个侧面。在传统中,人们通常总是将科学看作是中性的、客观的、与人的意志无关的对自然的真理性认识,而当发现科学竟然与修辞这种作为人类所特有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时,自然也就打破了传统中看待科学的纯粹客观性的那种“神话”。在此意义上,这不也正和你长期以来鼓吹的对于科学的看法有某种不谋而合吗?
江:
我注意到,本书大体可以视为两大部分:第1~3章,主要是正面陈述“修辞进路作为一种科学史方法”(第2章的标题);第4章可以视为本书的第二个部分,也是全书最长的一章,这是一个案例,即清初杨光先指控钦天监负责人汤若望的著名案件,通常被称为“康熙历狱”。
汤若望是来华耶稣会士(德国人),也是清朝任命外国传教士担任钦天监负责人这一奇特传统的开创者,因此杨光先的指控从一开始就具有宗教争议和天学竞争的两大背景。加之历狱案情又峰回路转,汤若望先是获罪下狱,又被赦出,然后另一位来华耶稣会士南怀仁(比利时人)为汤若望鸣冤,康熙帝为汤若望平反,而杨光先则黯然去职回乡。如今汤若望和南怀仁的墓都完好保存在今北京市委党校的校园中,作为历史文物受到政府保护。
丰富的背景和曲折的案情,使得康熙历狱300多年来广受关注,中外学者考证、论述此事的文章书籍,即使不足称汗牛充栋,至少也可说卷帙浩繁。在这样的情况下,本书选择康熙历狱作为案例,尝试用“修辞进路作为一种科学史方法”,来对这一著名历史事件进行学术操作,是有相当风险的。
风险在于,当我们选择一种新的方法(进路)来对众所周知的历史文化事件进行学术操作时,通常会面临学术界的要求:要么对事件本身操作出新结论,要么从事件中操作出新意义。你作为谭笑的博士导师,我非常想听听你的看法——本书是否能满足上述要求?或者,这种对新结论或新意义的要求是否有不合理之处?
刘:
因为一般来说,当在研究引入一种新的方法,如果不能得出与用已有方法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同的新结论,以及新意义,那么这种研究方法的价值就可能会被质疑。现实中,我们也确实经常会看到一些片面追求在方法上的“创新”而却并未得出新结论的、貌似新颖实则平庸的研究。你这里提出的,确实是一个可能非常具有杀伤力的问题。对此我是这样看的:
其一,对此已有长期学术积累的研究论题,谭笑前期并无很理想的学术基础和准备,但她敢于尝试用其新的进路并努力进入这一研究的勇气仍是值得赞赏的。
其二,你对此问题之已有研究的了解显然要更多,本应更有做出评判的资格。
其三,从文本上看,我觉得她还是努力地在研究中基于“修辞研究”的策略,引入了一些新的视角,并尝试对之进行探索。如从秩序世界的框架考察杨光先基于儒家文化的修辞建构,又如从准均质世界考察南怀仁基于近代西方思想的修辞建构,并以此展开对经争论的分析。就像她在书中所说的:“本研究对杨光先做了宽厚诠释,他对西方天文学的拒斥,不但是对于传统历法的维护也是对于秩序世界的维护。秩序世界指的是在近代物理学诞生前,宇宙作为一个和谐整体,在各个层面上充满着内在统一的秩序。它所对应的是哲学的思考方式,所产生的知识是垄断在一部分人手中的。这种宇宙观对于当时社会至关重要。更进一步的是,他的知识体系放在秩序世界中能得到完整的合理解释。他对西方历法的误解和无知应当与南怀仁对于中国传统历法的误解同等地看待,他在政治和宗教上的诉求并不仅是利益上的争夺也是与其知识体系相联系的。”像这样一些新的思考和理解此案的方式,不知是否也可算有所“新意”?当然,以这种修辞进路的研究显然还大有可继续深入的空间。
其四,退到最后一步,还可以辩护说,毕竟此书主要的目标是研究一种新的方法,此案例只是作为一种此法可试用的“示例”。即使由于前述的种种限制一时还未得出真正让你认可的新结论(其实何为新结论、新意义,对之的判断也经常与判断者的研究范式相关),也不能由此便判定这种进路对未来其他更理想、更深入的研究就没有价值吧?
江:
我同意,就像谭笑对杨光先宽厚一样,我们对谭笑也应该宽厚。况且我也能够找出有利于她的理由。这要分两个层次来看。
首先,我们确实可以质疑“这种对新结论或新意义的要求”。就好比做一道数学体或物理题,虽然已经有了标准答案,但我如果能够用新的方法(进路)得出同样正确的答案,尽管这并不构成对这种新方法的必要性证明,但仍不失为对这种新方法的有效性证明——它也能够得到正确答案。你说的第四点,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其次,对一个旧案进行学术操作,只要“创新”意识足够强烈,要操作出一些新结论或新意义来,很多情况下都是可能的。
就以康熙历狱为例,在以往的论著中,杨光先几乎百分之百处于被谴责、被否定、被鄙视的位置。他的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站在科学主义和改革开放的立场上来看,就是双重的荒谬和愚昧。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上,“好历法”就是科学的化身,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价值,为了它,哪怕让清王朝政权崩溃也应在所不惜。因为在科学主义者眼中,我们人类只是为了“发展科学”而存在的。而站在改革开放的立场上,“好历法”是“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化身,“西洋人”将它带进来,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情,有什么理由反对?
但是,如果让我们尝试将康熙历狱中的中西历法之争,代换为当下的某个类似情境,比如说代换为“北斗”系统和GPS系统之争,你会怎么想?我们能让“西洋人”来掌控我们的东风导弹吗?
所以,在康熙历狱上操作出新结论或新意义来,是有学术空间的。如果谭笑能够成功地证明:对于这样的新结论或新意义,科学修辞学进路具有独特的贡献,那就非常理想啦。
刘:
因为前面是就书中的特定案例提到新方法可能带来的创新问题,所以我们的讨论便向那个方向走了。其实,我觉得这项研究,正因为在中国还是初级的引进思考借鉴阶段,还不宜过多先纠缠在这点上,这更应由有兴趣者在以后的探索中去尝试。而目前我觉得更有意义的,还是在科学编史学的立场、视角、方法论等理论的意义上去考虑这本书的价值。
就这方面来说,我觉得此书还是很有意义地扩展了我们的视野,涉及到许多以往我们并未注意到的研究可能性,而且,不仅限于科学史,对于科学哲学,甚至对于一般哲学,其中对许多已有的研究成果的观察、分析和思考也是很重要的。
正如谭笑在书中的总结部分所说:“目前科学史中的修辞学进路在理论方面主要着重于对科学中修辞的交流性、发明性和认识论功能三种性质的分析。这三种性质也代表着修辞从外在性的,到内在性的不同层面贯穿于科学之中,而每一种性质中都包含着修辞比较显在和隐藏的一面。显在的部分是通常能够认识到但却故意忽视或排斥的修辞的表现方法和所在的情境,而隐藏的部分则是在传统对科学的分析中没有被发掘出来的部分”。
更有意义的是,“修辞的认识论功能贯穿于知识产生的全过程,即从个体的经验到共同体所认可的知识的过程。”尤其是,“修辞也以语言的形式,内在于科学知识产生、辩护的整个过程中。它象征着科学知识中各种社会因素的塑形作用。科学应当被看作是科学共同体进行的一种文化活动,是对于自然界的某一种认识方式和说明方式”。
仅仅从这些结论部分的抽取,我们也还是可以看到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对旧有观念的突破,甚至会带来对科学的相当不同的新认识。比如,我们以往并不会将修辞提升到一种从科学研究的一开始便存在并贯穿于整个活动进程中的认识和思考方式。就此而言,随着对科学的认识的改变,科学史自然也会出现有新意的新变化。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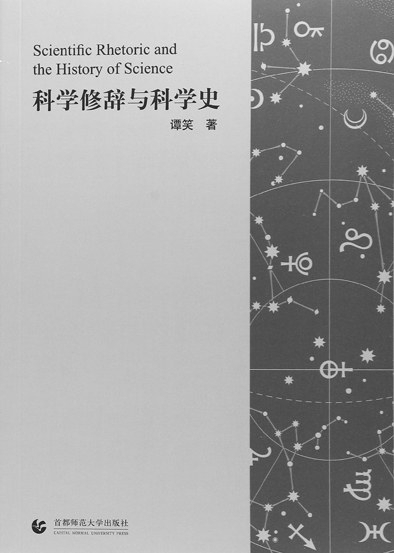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