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种糅杂着繁荣与颓败、开放与压抑、新创与沉滞的复调式的精神氛围中,阅读曾婷婷博士的著作《晚明文人日常生活美学观念研究》,会不由自地为之吸引、为之兴奋、为之感慨。
中国美学思想研究是一个成果丰硕、充满挑战的领域,但也是深受西方美学话语风格浸润的。西方的美学体系基本上是依存于哲学殿堂,是哲学体系(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逻辑派生物。这和中国美学的秉性品格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美学的生命诞生于历史上中国人的道德生活和艺术生活,而这两者又天然地寄存在生趣盎然的日常生活当中。西方美学崇尚体系化建构,因此,美学范畴是结成美学体系的纲领网节。研究美学史,必是以范畴梳理讨论为要务。而曾婷婷在这本著作中所采取的方法,则是观念史的研究。她不是从范畴的语义层面,而是从生动活现的审美经验层面来提炼和辨析一个时代的美学观念。
美学观念的研究,广义上说也是思想史的一种类型。豪舍尔在给伯林的《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所作的序言中对观念史作这样的概括:“观念史力求找出(当然不限于此)一种文明或文化在漫长的精神变迁中某些中心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再现在某个既定时代和文化中人们对自身及其活动的看法”;“它强调各种观念和情感、思想和实践行为、哲学、政治、艺术和文学的互通性”,“它的研究焦点,是某个文化或时代特有的那些无所不在、占支配地位的形成性观念及范畴”。由是可见,观念史的研究和范畴史的研究各有其不同的侧重。范畴史研究,比较注重理论性或专业性的文本,并以理论概念的词语作为分析基元;而观念史研究则要以更加广泛的材料作为支撑,场景、物件、形象、概念、抒情、事件、行为都可能成为观念分析的基元。这对于研究者来说是相当有挑战性的。什么材料才可以作为适当的观念史材料?对这些材料的梳理和阐释如何聚焦于核心的或居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或者说,如何从分散的材料当中提炼出一个时代的核心观念?这是对研究者的文献功夫、洞察力和理论概括力的考验。
曾婷婷的这部著作,给她自己提出了挑战。她选择了晚明这个人心浮动的特定的时代,选择了一批政治失意而放浪形骸的才子文人的日常生活,选择了内容驳杂风格各异的小品文作为基本文本,试图从中把握从日常生活行为到精神生活的一以贯之的审美观念。
近百年来关于晚明小品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典文学领域。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晚明小品文一度作为性灵解放先驱的文字得到新式文人们的垂青。鲁迅曾说,“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这话是在民国四十四年那个“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氛围里说的,他从“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看出晚明小品文里的光彩。这种具有强烈的社会改造使命感和抗争意识的评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衡量晚明小品文乃至所有文学价值的主要尺度。当人们逐渐走出那个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的年代,其阅读文学的视角和价值尺度也会有所丰富和调整。晚明小品文所体现的精神生活的复杂性、多面性乃至矛盾性便在研究者的视野中呈现出来。
晚明美学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葩,她不仅在面貌和本质上区别于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主流文化,而且也有别于以道家思想为依归的审美精神。就前者而言可一目了然,而对于后者则尚需辨析。晚明美学的世俗性、物质性、身体性、感官化、娱乐化、都市化,是区别于以往美学观念的重要特征,由此也深刻影响到明清小说、戏剧和工艺创造的辉煌成就,开启近代艺术和思想解放的先河。小品文的品类虽小,其所折射的思想流变的取向却耐人寻味。回到我们今天的矛盾交织的时代,重新阅读晚明小品文,透过张岱、袁中道们的充满性灵和梦呓的文字,去体会繁华旧梦的日常生活,也犹如通过历史透镜折射出中国人的审美兴味和精致理趣。
曾婷婷在晚明小品文中提炼概括出来的“欲”“闲”“癖”“奇”“生”等五大美学观念,既是对晚明文人群体的社会生存方式和思想类型的全面解读,更是对晚明美学独创性价值的深入发掘。她以五大观念为框架勾连起丰富的文本资料,旁征博引,读来并无隔涩胶柱之感,倒是觉得立论坚实可靠,有血有肉。
给我最多启示的,是这项研究通过中国美学的经验向西方美学的一些既定法则提出的补充和挑战。例如,“欲”可以成为一个美学观念吗?柏拉图主义界定了审美观照的反欲望模式,灵肉二元论的观念,一直贯穿在西方美学的传统中,直到现代主义出现,西方美学才正视由欲望和身体所唤起的审美经验。曾婷婷在晚明小品文里面发掘出“欲”的内在审美价值,她认为,晚明文人日常生活之“欲”是建立在生命快感基础之上的,但又不仅仅满足于感官享乐,而是通往审美。晚明对欲望的重估包涵着对人生价值的重新思考。在任情放诞的背后,是晚明文人的精神挣扎与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欲望和审美之间,身体是中介。晚明小品文所展示的对身体感官经验的迷恋是对于宋明理学道统的反叛,通过珍重人的自然本能,凸现人的生命价值,将“体舒神怡”合并为一个完整的审美体验,将感性欲望作审美提升。
曾婷婷对于晚明小品文中记载的文人“癖好”的美学讨论也很有新意。她指出:在西方,审美是智慧,是超越,而“癖”作为一种非理性的情感投入与耽溺,在西方美学史上是没有地位与价值的,通常被视作生理或心理的“畸变”;即使其中包含有审美成分,也是一种病态的审美。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癖”的宽容,是出于对生命的深刻体验与理解。而到了晚明,追求“癖”的多样性、丰富性、独特性,竟成为风标时尚。这里面有社会政治和理学道德观念压抑的原因,但主要的却是由于晚明物质文化和都市生活的条件催生了新的“物-我”关系。“癖”之所以可以作为新的美学观念,指涉的正是物与我之间的关系。“癖”的主体是否发自天性,悟自本心,真正与物相投契、相感发,也是“癖”能否成为审美活动的重要指标。她写道:“晚明文人对物质世界的深入了解,不仅在于回到大量的文献中去搜寻前人对名物世界的观察与领悟,依‘细究物名’‘了解物性’‘辨明物用’等几个角度,建立起一个纸上认知的名物世界,还经由自己的亲身体验与实践,建立起独特的美感经验,以获得对物质世界细腻的辨知与领悟。”“‘癖’一方面反映出一种反抗社会世俗价值的意图,另一方面则显示一种以‘癖’来寄托、承载生命价值、意义,透过‘癖’让生命超拔于世俗世界之上,以‘癖’来创构一个理想世界,进入新的人生境界。有所癖好者,对物的全情投入,正是离弃世俗世界,进入特殊生命理想境界的入口。”这样的阐释有深刻的见地,可以说在中国美学观念史研究方面是一个有示范意义的尝试。
晚明美学的当代意义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历史的发展有时候会呈现出表象上的类似性。从曾婷婷的著作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美学注重经验鉴赏达到了极为精致的程度,这和某种粗鄙化的世俗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日常生活美学,绝不等于审美经验的尚丑或粗鄙化,即便是后现代西方美学的理论范式已经宣告审美价值的终结,中国美学的深厚传统和人文底蕴仍将焕发她的魅力来继续滋养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将其从物质功利主义和感官消费主义的洪流中带入审美绿洲,并终将改变其日常生活哲学。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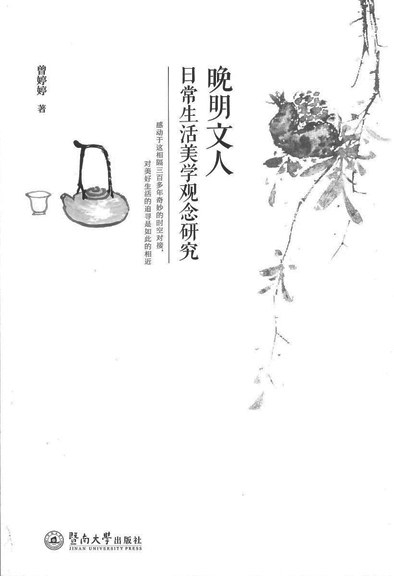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