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中(字容甫,1744~1794)是乾嘉学派中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但同那些终身埋头于典籍、干巴巴的学者不同,他的故事很多。两百多年过去了,若干八卦传说在他的故乡扬州一带仍未衰歇,例如他的狂傲和喜欢骂人,又如他不幸的婚姻,还有他家的门联“海内存知己,高堂有老亲”,都为人们所乐道——他父亲死得早,家里极穷,是母亲千辛万苦带大的,他对高堂极其孝顺,以至大书于门首。一般的学者当然有学问,可惜文章大抵以干巴巴的居多,汪中则诗文皆属一流水平,骈文尤为绝顶高手,在文学史上很有地位。
汪中创作和研究的成果,数量都不算很多,而含金量极高,现已全部收入《新编汪中集》。近日重读此集,深感这位前辈乡贤最值得注意的乃是他的思想超前、学术创新。在当年许多学者醉心于一字一句地细抠儒家经典的时候,他却在好几个比较大的方面开辟了新的道路。
一是还原儒家经典的本来意义,反对宋儒之妄加改造。
汪中精研经学,对于名物制度、古书真伪、语言、史事等各个侧面都有开创性的研究,所著《明堂通释》、《左氏春秋释疑》《释三九》《周公居东证》等,都是一流水平的大文章。批评宋儒的典型之论如关于《大学》的定性,《大学》原来是《礼记》中的一篇,作者不明,而宋代理学家却指定为孔门高足曾子的著作,说是学习儒家理论体系纲领性引论性的大著作,朱熹且对历代相传的文本加以改编,分别其“经”(正文)、“传”(阐释),调整其顺序,还自己动手补写了一段“传”,列为《四书章句集注》之首(参见顾农《朱熹对〈大学〉的改造与发挥》,《中华读书报》2017年5月3日第10版)。这种经过整容大手术形成的文本,后来却成了新的经典,规定为国家科举考试的依据。汪中在《〈大学〉平议》一文中指出:
《大学》,其文平正无疵,与《坊记》《表记》《缁衣》伯仲,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于孔氏为支流余裔。师师相传,不言出于曾子,视《曾子问》《曾子立事》诸篇,非其伦也。宋时禅学盛行,士君子入之既深,遂以被诸孔子。是故求之经典,惟《大学》之“格物致知”可与傅合,而未能畅其旨也,一以为误,一以为缺,举平日之所心得者著之于书,以为本义固然,然后欲俯则俯,欲仰则仰,而莫之违矣。习非胜是,一国皆狂。(《新编汪中集》,田汉云点校,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281页)
这样的议论是很大胆的,而含有对于学术史的深刻理解。汪中又进而指出说:
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明乎教非一术,必因乎其人也。其见《论语》者,问仁,问政,所答无一同者。闻斯行诸,判然相反,此其所以为孔门也。标《大学》以为纲,而驱天下从之,此宋以后门户之争,孔氏不然也。宋儒既借《大学》以行其说,虑其孤立无辅,则牵引《中庸》以配之。(同上)
这里根据孔子“因材施教”的一贯风格,指出《大学》中的意见必不出于孔子本人。把《大学》抬到极高的地位,再加上《中庸》,置于《论语》《孟子》之前,构成所谓“四书”,完全是宋儒“变易孔氏之义”之所为,这种做法是不合适的。汪中这样的观察有理有据,击中了理学的要害。朱熹在康熙年间已被请进孔庙配祀,敢这样批评他是不容易的。
凡重大的创新,总是难免要得罪权威。汪中一辈子不得意,同他因创新而言论大胆有很大的关系。在那个时代,理论创新要付出代价。
二是开创研究子学之风,寻求儒家经典主线以外的思想资源。
汪中用很大的力气研究荀子、墨子等先秦诸子,创立了新的研究方向,大大活跃了学术空气,后来影响很大。
汪中指出荀子是孔子的重要传人,也是战国至西汉初经典传播的关键人物,历史贡献极大。汪中指出:“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自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荀卿子通论》,《新编汪中集》,第412页)他看重孔-荀一线,大大高于孔-孟一线。荀子后来之被边缘化是一个至今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汪中对墨子的研究更为深入,他看出了墨学曾经乃是显学,其中精华甚多。虽然汪中整理研究《墨子》的有关成果未能完全面世,却已经相当惊世骇俗,有人因此骂他是“名教罪人”,甚至提出要“褫其生员衣顶”,用行政手段予以打击。
此外汪中对《老子》《庄子》《吕氏春秋》也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许多高论。当时虽没有太大反响,后来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颇多采用其说者。在汪中的时代,治子书者亦非无人,大抵热衷于考证个别字句一类琐细问题,像他这样能高屋建瓴畅论其学术史意义的颇为少见。
三是汪中有志于撰写一部有系统的思想学术史《述学》,可惜未能完成。
从遗留下来的一些材料看去,其规模非常宏大——他的《述学》一书以及《补遗》《别录》只是其中很少的一点片段和若干准备材料。这是非常可惜的。
汪中只活了五十岁,没有地位,没有官职,从小就穷,后来也一直潦倒,身体不好,婚姻不幸,他的学术工作只能在辛苦谋生之余断断续续地进行,这一切都逼得这位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远远未尽其才!晚年汪中因几位学者型高官之荐,得到检理四库全书的差事,可以全力从事学术工作,但身体已经很差,不久就匆匆病逝了。
缪钺先生在《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一文中说过:“康熙、雍正以还,理学已成强弩之末……故容甫直斥理学为‘宋以后愚诬之学’(《大清候补知县李君之铭并序》)。乾隆之时,考证之业极盛,治考证须有才识,始能有创见,有发明,非徒记诵而已。然风气既成,趋附者众,横通者流,游谈杂览,亦自附于学术之林,此又容甫之所深鄙。”(《缪钺全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182页)汪中的学术工作同理学末流及汉学庸众完全异趣,终成一代精英,尽管他毫无名位,还得罪过若干要人。
汪中后来被列入扬州学派,该派人才辈出,成果甚多,而扬州及其周围一带在先贤感召下从事汉学者亦复实繁有徒。从后来的情况看去,按规矩做考证写注释搞汇编的甚多,也有不少成绩,而创造性开风气的贡献比较少了。试看宝应学者刘恭冕(他的叔祖刘端临是汪中的好友)写于同治五年(1866)之《论语正义·后叙》云:“先君子少受学于从叔端临公,研精群籍,继而授馆郡城,多识方闻缀学之士,时于毛氏《诗》、郑氏《礼》注,皆思有所述录。及道光戊子(1828),先君子应省试,与仪征刘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泾包先生慎言、丹徒柳先生兴恩、句容陈丈立始为约,各治一经,加以疏证。先君子发策得《论语》,自是屏弃他务,专精致思,依焦氏作《孟子正义》之法,先为长编,得数十巨册,次乃荟萃而折衷之。不为专己之学,亦不欲分汉宋门户之见,凡以发挥圣道,证明典礼,期于实事求是而已。”这里提到的一批学者后来都在辛辛苦苦地做学术工作,如“先君子”刘宝楠(1791~1855)从事《论语正义》历时二十七年,未能完成,由其子刘恭冕续成;刘文淇(1789~1854)做《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80卷),几代人接力进行,迄未完成。此外梅植之、柳兴恩、陈立、包慎言等等,也都是很用功的学者,但大部分人似乎都存在一个长年低头拉车、只求“发挥圣道”、创造性有所不足的问题。用“发策”(抽签)的办法决定各人做哪一经的疏证,有点像是现在申报项目做一个什么课题的样子,尚未研究而已有题目和大纲,这样的项目能有多少创造性的含量呢。多下抄撮功夫虽然也可以形成汇编性的成果,但这种事情汪中大约是不肯做的。回顾这一段学术史,人们不是可以获得许多宝贵的启发吗!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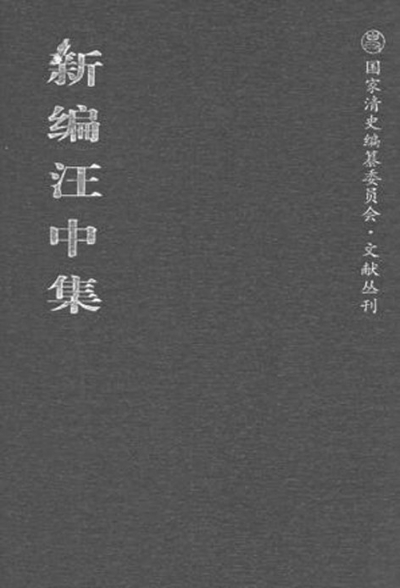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