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蓝的著作里,有一座从蜀地的山林旷野里,从废旧的砖石缝里,从寂寂无名的草木里滋养生成的逶迤建筑,它看似封闭保守,实则开放叛逆,它是蒋蓝的“成都”,也是你我的“成都”。
“树举起闪电一饮而尽/天空龟裂/向更高处塌陷/剩下树,和树的酩酊大醉//反刍的时间/空气里浮满树幼年的小手/身体被火的利斧劈开/树汁的星星喷射到高空……”,这是蒋蓝在“成都地区多民族诗人、作家与评论家迎新联谊会”上朗读的《雷击之树》中的句子,那些让人惊栗的隐喻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天是2013年1月19日,是我与蒋蓝老师第一次在同一空间出现的日子。遗憾的是我当时忙于会务,没有主动与这位个子高大的作家攀谈。
随后几年,“蒋蓝”这个名字不时出现在好友罗安平与梁昭的微信朋友圈中,就连我回家乡邻水参加“匠心读书会”的活动,也能从家乡书友的口里听到“蒋蓝”这个名字。原来身边这么多朋友都在读蒋蓝!最新出版的《成都笔记》是一部为古今巴蜀风云人物立传的书,与另一部表述四川古今文化的非虚构散文集《蜀地笔记》构成姊妹篇,前者是蜀地“人物卷”,后者是蜀地“风物卷”。用“蜀地”与“成都”这两个地理名称连接“笔记”,容易唤醒蜀人对蜀地久远历史的固恋与矜夸,同时也提醒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地方文化书写。不过,与“蜀地”一词本身侧重“中央”之与“四方”的关系不同,“成都”尽管也对应着一个客观的地理区域,但它更像是一个动词,是一个靠无数生灵血肉之躯与精神之树数千年来层叠累积、造化孕育而成的都城。就像蒋蓝在第一篇《蜀人自古足英雄》中所言,“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特色是城市的标志,城市最大的特性是文化性。”假如没有蜀人,蜀地的灵魂从何谈起?所以,是蜀人造就了成都,成都滋益了蜀人。
《成都笔记》凡三十四篇,分为“蜀地异人传”“踬踣者外传”与“蜀地心史”三编。蒋蓝的随笔杂记带有强烈的个人体验,他敢于用笔记为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写传,在于他对正史的精确掌握以及民间史的烂熟于心,当然还有他多年来养成的徐霞客式的文学田野考察的功底。蒋蓝用稳健又峭拔的笔力,将正史与民间史、人物访谈与图像实物资料杂糅在人物故事中,使得叙述线索看似毫无章法可言,但故事的枝蔓与人物悲喜的命运又在彼此的缠绕错结中,自见分晓,随后便有种醍醐灌顶的感激与酣畅淋漓的欢喜。当然,在阅读中,也会对内陆腹地的天下之府,对巴山蜀水与蜀人,生发出别样的深情来。
《成都笔记》三编中,“蜀地异人传”编中的“异人”非怪异之人,而是“天赋异秉”,“峭拔其上,独立于世”的雄奇。“踬踣者外传”编中的“踬踣”原意是“遭受挫折”,蒋蓝引用孙中山的话语,用“踬踣者”借指那些“以坚毅不挠之精神,与民贼相搏”的人。“外传”与“正传”相对,显然蒋蓝写的不是正史,而是民间史。“蜀地心史”编由二十一篇文章组成,讲述了晚清以来入蜀的21位文人的故事。这部分历史书写,可以称作“入蜀文人踪迹探寻史”,资料多来源于蒋蓝深厚扎实的文学田野考察。
因为蒋蓝重视文学田野考察,其写作常被视作“文学人类学式的书写”,蒋蓝也因此被称为“学者型文化创作者”。关于这两点,我深有同感,不再赘述。除此之外,在我看来,蒋蓝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儒侠”。他坦承,书生剑气,一直为他供给“活着”的血气(《铸剑者龙志成》),因为这血气,他在叙述中,会忽然跳将出来,对他感兴趣的事物做蒋蓝式的极致想象,比如恐惧或是鲜血。蒋蓝叙述中的这种跨越,应与他对“中道”的理解有关。蒋蓝认为,必须有能力去实现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跋涉,才可能获得一种冰炭相遇所构成的消融,直至恬然(《画家钟知一:于牛角间了悟中道》)。蒋蓝的书房里挂着一把剑,他以笔为剑,在折叠的历史踪迹间挑拨开一道缝隙,剑光射进黑暗,那些被史籍遮蔽的部分,终于在蜀地鲜活复原起来,在历史的镜像里生长为一束光,照亮我重新审视生养我的巴蜀大地的漫漫路程。
《成都笔记》中,蒋蓝除了对蜀人与入蜀之人踪迹与心史的追寻,还特别注重地方性知识的收集。对孤陋寡闻的我来讲,纳溪竹海的“竹飙”与“脆蛇”,报春花科的“四块瓦”,唤起我步出房间走向山野的欲望。我知道,当我重新面对我所身处的蜀地时,它将不再是我以往所认知的蜀地了。在蒋蓝文字的昭引下,我将会用心去触摸那些从未被我认真关注过的建筑、植被、街坊、饮食与风俗,在触摸里,我将第一次真切感知那些我从未看见的历史。
写到这里,我想起蒋蓝评价流沙河先生的话语来,他说,就展示成都的历史、文化、风物、习俗、遗构而论,沙河先生完成的是一座“纸上成都”的逶迤建筑,为蜀地葆有了弥足珍贵的文化记忆(《布金满地流沙河》)。实际上,蒋蓝的著作里,也有一座从蜀地的山林旷野里,从废旧的砖石缝里,从寂寂无名的草木里……滋养生成的逶迤建筑,它看似封闭保守,实则开放叛逆,它是蒋蓝的“成都”,也是你我的“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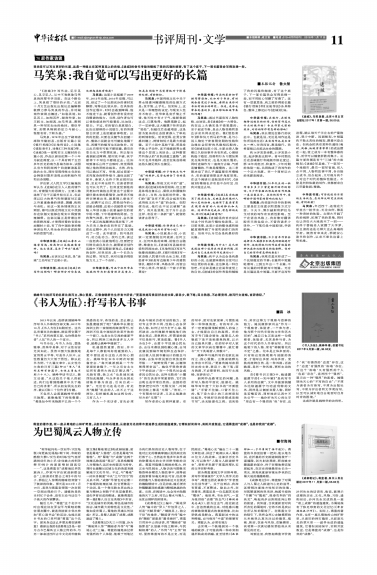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