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大学急切地把“全球化”作为创建二十一世纪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指标。但这远不是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第一次试验。早在民国时期就有许多中国大学致力于与世界前沿教育接轨。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大学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另一个就是在美国和欧洲教会帮助下建立的一系列新教和天主教大学。这些面向全球化教育的尝试引发了许多争议。其初衷与如今的中国大学相似,即学习国外先进教育与发展适合中国的教育模式,这两大需求要努力达到能让人接受的平衡。
从民国时期到现代,哈佛燕京学社(以下简称“哈燕社”)都是大力推动高等教育领域中西交流的有影响的支持者。哈燕社于1928年成立,到1951年其主要活动在中国大陆停滞。樊书华教授《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人文学科的再建:1924—1951》一书基于丰富的原始档案资料,极具洞察力地阐释了哈燕社早期历史中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些是光荣的,而另一些是不光彩的。樊教授著作围绕哈燕社的主旨与经营中的矛盾,反映了理念与利益的冲突不仅在国家之间,更在国家自身当中。应如何开展中国研究——是用英文还是中文,是运用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还是遵守中国传统的研究思路,是将范围限制于人文学科还是将社会科学学科也涵盖在内,它是否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福音主义、民族主义、大同主义等等)——都是严肃的学者们从当时到现在仍在争论的议题。最近,北京大学新设燕京学堂引发的争议表明这些议题即使在今天仍很敏感。
新发展
从哈燕社1951年在大陆工作终止到现在已六十五年,现在她已极大地改变和扩张了它在亚洲的学术活动。在日本史专家赖肖尔教授(EdwinO.Reischauer)的领导下,除了中国大陆,哈燕社还将学术合作的大学以及研究机构延伸到了中国港台地区、日本及韩国。接下来哈燕社也将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建立联系。除此之外,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哈燕社在亚洲的活动仅限于支持在中国的教会大学开展国学研究不同,她从1954年开始了访问学者项目,专注于从亚洲大学挑选和支持年轻有为的学者在西方(主要是哈佛大学)进修。今天,访问学者(主要是来自亚洲合作大学的学者)以及访问研究生(来自亚洲合作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仍是哈燕社的重要项目。
自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哈燕社恢复了与中国大陆的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合作关系。今天哈燕社同中国二十所高等教育机构建立了伙伴关系(此外还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三十所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哈燕社因此拥有来自亚洲地区主要大学的几千位学者组成的卓越而且活跃的校友网络。在同香港大学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合作中,哈燕社为在东南亚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开设了奖学金项目。在和德里的中国研究机构合作中,哈燕社为在中国研究领域攻读博士学位的印度学生提供奖学金,使这些学生能够在中国和哈佛学习中文以及撰写博士论文。在和亚洲地区友好大学的合作中,哈燕社为新兴研究领域(例如城市研究、人文医学、大众政治、世界文学等等)的年轻学者以及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提供有关人文和社科的“学科拓展”训练课程。在这些项目中表现突出的研究者将有资格获得奖学金,继续在哈佛一年的研究和学习。
在哈佛大学,哈燕社(一直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在法律和财政上同哈佛大学分离)努力在更广阔的学术环境中为访问学者和访问研究员提供更多的奖学金。所有访问学者以及研究员都能从哈佛的教员中分配到一位导师,鼓励他们同导师一同进行定期的学术研讨。访问学者会在研讨会中展示他们的研究,导师主持会议,研讨会在哈佛公开进行。访问研究生将同哈佛人文和社科领域的博士研究生一同参与论文写作训练课程。哈佛教员、硕士生及博士生发现他们通过和哈燕社的紧密联系,比原先仅有的师生互动学到了更多东西。
在哈佛之外,哈燕社致力于支持具有影响力的亚洲学者面向西方听众。例如,资助他们在由一流亚洲研究学者参与的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上演讲。哈燕社还资助了一批出版项目(英文以及中文的学者专著和期刊,用亚洲语言写成的针对重要学者著作的在线书评等等)。哈燕社同样针对亚洲本土学者在哈佛大学、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以及其他地区举办的重要亚洲研究会议提供旅行资助。
中心任务
尽管有了这些新的发展,哈燕社的中心任务并没有变化:在亚洲人文和社科领域推动高等教育。
哈燕社的捐助者,查尔斯·霍尔(CharlesMartinHall)于1914年逝世,在他最后的心愿和遗嘱中明确承诺要在后来广为人知的“东方”(“日本、亚洲大陆、土耳其以及欧洲的巴尔干国家”)推动高等教育。十四年之后,他的愿望随着哈燕社成立而实现。哈燕社的主旨是:“支持有关中国文化、亚洲大陆和日本、土耳其以及欧洲巴尔干国家的研究、教学及出版工作……”哈燕社明确承诺“为训练有素的中国和西方学者提供研究资助,并开展文理学院研究生的教育工作……在中国,支持探索、发现、收集和保护文物,或是资助博物馆及其他机构从事前述工作。”(哈佛燕京哈燕社协定(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Agreement of Association),1928年1月4日)
哈燕社成立于中国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当时中国许多古代文化遗产受到战乱毁坏的威胁,哈燕社认识其使命即保护与阐释——而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基于此,哈燕社同当时在华传教的西方势力有本质的不同。在最后的遗嘱中,霍尔先生对于他在亚洲地区教育事业的支持有明确要求,“任何财产都不可用于神学教育”。尽管霍尔以及其财产受托人倾向同中国的教会大学(特别是燕京大学,也有美国教会支持下的其他教会大学)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想要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而是赞同教会学校自由教学的办学主旨。霍尔本人就毕业于基于宗教信仰成立的文理学院(奥柏林学院)。作为一位科学发明家和成功商人,他坚信这类教育机构的优势。同理,哈燕社也认为中国的教会大学为保护中国文化提供了最大的希望。他们重视建立图书馆、博物馆作为保存文化价值的场所,为了激发批判性思维以及纵览全球的视野而开设多元文化课程,这些都与哈燕社的追求目标相一致。
对中国教会大学而言,同哈燕社合作以加强国学研究,是被看作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这一更高宗教目标的途径。但对哈燕社而言,同教会大学合作则是其实现学术追求这一更高世俗目标的途径。在哈燕社眼中,教会大学的角色就是把“西方科学方法”运用到中国文化研究中去。这样的研究方法,在哈燕社受托人看来,不仅对中国的未来一代,对整个世界文明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贡献。
但是哈燕社的领导们从来没有清晰地阐释过“西方科学方法”运用到中国研究的准确内涵,而呈现出某种未经检验的文化帝国主义,即认为哈佛学者(以及他们在燕京和其他教会大学的学生)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理所当然地优于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方法。就像樊书华所说,虽然许多重要的亚洲研究成果——不管是在亚洲还是哈佛,部分归功于哈燕社,但它同时也要为很多表现为文化迟钝以及令人讨厌的越轨行为负责。多数不幸的历史插曲可以归结于哈燕社早期领导者自以为是的科学优越主义,他们信奉精英和卓越学术分层化的观念,而哈佛确立了全球标准。虽然哈燕社没有试图改变中国文化本身,但它确实试图改变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方法,从而能更好地适应西方学者所认为的最先进的国际学术标准。
今天的哈燕社意识到哈佛大学师生应该从从亚洲本土学者身上学到的东西至少和其他地方学者那里一样多。虽然哈燕社的创立目标——通过中国和亚洲文化的深入研究来推动高等教育——依然没有改变,但哈燕社不再认同自己是霸主的地位:哈佛的教授高居学术顶层,受过哈佛教育但在其他高校的学者屈居第二,而其他人叨陪末座。哈燕社新启动的项目,如本地工作坊和联合培养计划,都是以与亚洲数十所友好大学密切合作的方式开展,因此哈燕社认可有多个充满活力、杰出的亚洲文化研究中心。
最近在大中华主要高校中开展的多个跨学科中国学研究院项目(和在日本一流高校开展的日本学项目类似)令人兴奋,她挑战西方现存的对这些领域的限定。这些项目无论是用英文还是亚洲语言开展,无论对国家软实力或纯学术贡献多大,也不论是促进文化多元化还是全球同质化,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议题。哈燕社在这些复杂和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上并不占据任何权威地位。但哈燕社欢迎在当前趋势中所展示出的更新中国学的努力。哈燕社希望在其创立九十周年之际,能为在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复兴中国文化研究贡献微薄之力。
作为哈燕社社长,我谨表示对斯克兰顿大学(UniversityofScran⁃ton)樊书华教授书写哈佛哈燕社早期历史,以及山东大学刘家峰教授认识到其学术价值并及时促成本书翻译出版表示真挚的感激。
(作者为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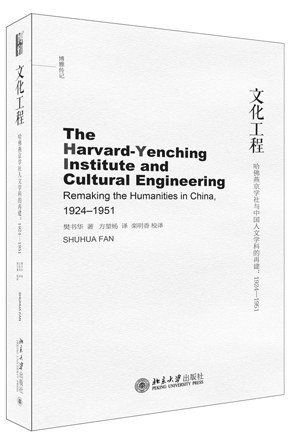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