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在《半农杂文》(第一册)序言中解释书名之“杂文”二字道:“谓其杂而不专也,无所不包也。”“全书按年岁之先后排列。”这种办法实即编年体文集。鲁迅也采用这种办法,他在《且介亭杂文》的序言中明确地写道:“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他们的路径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这样的文集中甚至可以包括译文,鲁迅的《二心集》里就有一篇译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原作者日本岩崎昶)。
书中所收的半农杂文约可分为三大段落,一是早期,以译文为多,这时他还是鸳鸯蝴蝶派中人(参见陈学勇《鸳鸯蝴蝶派的刘半农》《浅酌书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二是《新青年》时期,向旧思想旧文化作战,颇有名篇,如《奉答王敬轩先生》《作揖主义》等等;三是到欧洲留学以及归来之后,因为研究的是语言学,文章中这一方面的内容不免渐多,如《国语问题中的一个大争点》《汉语字声实验录提要》《国语运动史提要》等等,但他的兴趣仍然广泛,敦煌文献、古代小说、新诗、歌谣、翻译、时事,无不涉及,内容丰富多彩,笔法也更加老到。
这里有许多有趣的文章,即如他的《海外的中国民歌》一文中在正文之前提到“洋泾浜话”,即有言简意赅的分析道:
所谓PidginEnglish,意译应当是“贸易英语”,因为pid-gin是英语business一字的转音,但在上海,大家都叫做“洋泾浜话”。据说当初这一种话,是洋泾浜里的撑船的和外国人交际时说的,故有此名。现在洋泾浜已经填去了,说这话的,也已由撑船的变而为包探,买办,跑街,跑楼之类,所以洋泾浜话一个名词,只是纪念着历史上的一件事实罢了。
在发生洋泾浜话一个名词之前,在南洋,必定还有一个更早的名称。这名称我不知道。但记得三年前在伦敦,看见英国博物院书目中有一部书叫做《华洋买卖红毛鬼话》。亦许这“红毛鬼话”,便是比洋泾浜话更早的一个名称了。
这种话的构造,用字与文法两方面,都是华洋合璧,而且都有些地域性的……
这种语言,一定有许多人以为可笑,不足道。但在言语学者,却不能不认作有趣有用的材料。安见从这种可笑的东西里,不能在语言心理上,或语言流变的哲学上,或变态语言上,发现出很大的道理来呢?但现在我只是要介绍民歌,不能愈说愈远了。
“洋泾浜”英语在长三角一带曾经流行多年,代表中外交往一个时段一个地域的特色,很值得加以研究。现在已经有这方面写得很是充分深刻的论著问世了(详见司佳《近代中英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涉》,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10月版;参见顾钧书评《“洋泾浜英语”的意义》,手机版《粤海述评》2017年3月9日)。
刘半农关于小说《何典》《海上花列传》的介绍和分析也都是读来大有兴味的妙文。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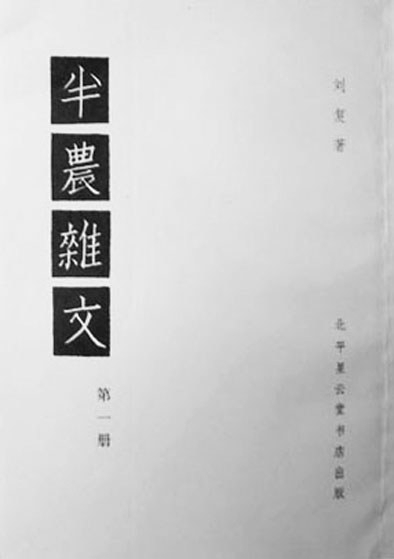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