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心悦目的有趣故事
此书作者KristieMacrakis博士在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做访问学者期间开始撰写本书,为此她拜访了美国和欧洲的众多档案馆及图书馆。
但这些都是我读到很后面甚至读完时才注意到的。最初吸引我邮购此书的,是某“群聊”里传阅的第一章《爱情与战争的艺术》的第一页,上书:“在古代国际大都市罗马,他(奥维德)在铺满鹅卵石的小道上漫游,找寻勾搭情人的完美地标……”。在他的建议中,就包含了“用新鲜牛奶书写”。这好似提前了一千六百年应用的浮世绘笔法,让我对此书的剩余部分充满期待。
接下来的几个故事也没让我失望,如希波战争的“头皮刺青”故事。但严格说来,这封写在奴隶头皮上的密信——“让伊奥尼亚起义”,不能归到希波战争里,因为整个失败的起义还只是战争的“近因”之一,暴动的城市本属帝国的一部分。又如,快乐将军苏拉率罗马军团与米特里达梯六世的盟军交战时,以墨水、胶水混合物书写的猪膀胱塞入灌满油的玻璃瓶内与他的间谍秘密沟通;如此,他得以掌握敌军动向而发动奇袭取胜。
到17世纪,波义耳笔下较复杂的配制过程已带有《哈利·波特》中魔药课的韵味:“这些原料应该在水中浸泡两三个小时,偶尔搅拌一下……最后……在烧热的煤炭上加热,使它们在几个小时内互相‘融合’,直到‘溶剂’出现一种香甜味道”。同时,繁荣起来的隐写术衍生出一些“魔法玩具”,如可变化的风景画:画里的季节随着颜料被壁炉加热或自然冷却而来回变幻。
再如,作者指出18世纪是大众科学兴起的世纪。仅仅伦敦就出现了超过500家咖啡馆,其中很多都提供科学讲座;文艺复兴时期的皇家庭院转变为珍奇屋(又名多宝阁),后转化为近代的博物馆。该世纪末还发明了“便携式化学柜”,被用于“介绍化学知识和娱乐活动”,也即20世纪的教育玩具“化学套装”之前身。公众兴趣的增长如此普遍,我们甚至发现通常只在哲学史、政治史上现身的卢梭,年轻时也涉足“隐显墨水实验”——结果瓶中液体爆沸、炸到脸上,又吞下很多粉尘和三硫化二砷,整整六个星期失明,此后也未痊愈。这些背景介绍有助我们理解从17世纪末科学革命完成到19世纪初工业革命发生,基本上依然“无用”的科学何以继续前行——尽管它未能兑现培根式“知识即力量”的承诺,对实际技术没起多大推动作用。
本质上是一部技术史
尽管有这些趣事点缀其间,从作者对相关政治、军事背景一笔带过不求甚解来看,本书实质上仍是技术史。技术史不一定枯燥无趣,譬如查尔斯·辛格经典的《技术史》,图文并茂,详略得当,读来兴味盎然。但本书一离开熟悉的古典时代,我就昏昏欲睡,差点放弃;直到伊丽莎白一世与玛丽女王的谍报战,才又恢复点阅读兴趣。这又是何故?
其一,隐形书写是一种进展极缓慢、进三步退两步的技术,过程拖沓,读来缺乏“爽快感”。它与密码技术自始就是双胞胎,却不如其兄远甚。前四世纪的埃涅阿斯在其有关守城术的名著中,介绍了标记某几行某些字母、让收信人重新排列这些字母来解码信息的做法。这诚然也有隐写意味,但归入密码术似更妥当。他还认为,相比上个世纪在刻字木板上覆蜡(详下),用最好的墨水写在黄杨木板上、再以石膏刷白更稳妥。但在我们看来也许会觉得简直算不上什么技术进步。
希腊化时期许多科学、技术领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隐写术也不例外。拜占庭的菲隆记载了将瘿结(树瘤)捣碎、溶解后书写的方法。这种隐写术,须用浸透硫酸盐的海绵擦拭方可显形;反过来,两者若一开始就混合,则是古代西方黑墨水的主要配方。须特定“显影剂”方可读取的隐写术,放在古代固然是一大突破,但两千年后还在北美独立战争中大显身手就有点夸张了——隐写术进展之慢可见一斑!
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个现象,她在给“间谍与技术史”课程的学生讲课时发现“当书架被密码学和研究编码、解码的书籍压得嘎吱作响时,它的姐妹学科——隐形书写、隐形墨水或者秘密书写的技艺,却极少被记录”。她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有时,最简单的就是最好的。人们常常觉得怎样隐藏比如何书写更重要。密码学使用暗码时,它等于已经对外宣布自己隐藏了秘密,而隐形书写则可以保守秘密,除非有人怀疑消息是用隐形墨水写的,否则就不会遭到细致的审查。
隐写术成功的关键不在于配方有多高级,而在于“赌”信件不被怀疑、审查。即使在一战、二战那种谍报技术不断升级的有利环境下,常用隐形墨水也就那么几种,且配方复杂的高级墨水只会配发给最受信任的极少数间谍。多刷几次、多试几种法子,总能让字迹原形毕露的;多数隐写密件甚至连“通用显影剂/显影方法”这一关,都难通过。
和公然挑战对方智力、宣称“要让你们解码解到地老天荒——至少也得时过境迁、失去意义”的密码术相比,隐写术是一种大众化的亲民技术,不仅间谍,企图越狱的囚徒、暗通款曲的恋人都能使用,立足于“大部分信件能蒙混过关”的假设之上。因而在隐写术之战中,有条件更彻底推翻该假设的一方——也即审查能力更强的一方——终将获胜,技术么,不至于落后太多即可。但话说回来,隐写术的使用者多半清楚自己的技术不可靠,这比盲目信任一种羸弱的密码要好些。玛丽女王正是在使用了一种能用频率分析法轻易破解的编码表后,身首异处的。
其二,隐形书写对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委实很有限。薛西斯皇帝集结遮天蔽日的大军准备入侵希腊,这消息是瞒不住的。斯巴达流亡者用刻字的木板覆蜡发出示警密信,固然为希腊人争取到一些时间,但绝不像书里暗示的(“隐藏在蜡衣木板上的一条信息保卫了西方文明的火焰”),仿佛能决定萨拉米海战乃至希波战争的成败——毕竟中间还隔了温泉关战役及联军后撤、修整期。萨拉米海战的胜利应主要归功于地米斯托克利的计谋、善用地形之利,而非有充分时间预谋。
从一战开始,这点就更明显了。尽管章名叫“秘密墨水之战”,但从叙述重点来看,不如改名叫“审查员与间谍之战”。不少篇幅被用来讲述著名间谍的生活琐事和心路历程。最初落网的一大批德国间谍都用柠檬汁——小学生都知道的配方——进行隐秘书写。但他们失败的缘由不是这种墨水太原始,而是他们不知道英国的邮政审查制度已经“成熟、庞大到何种程度”,并拥有一个持续更新的黑名单来监控中立国的掩护地址。
德国人随即开始升级他们的墨水配方;于是19世纪就存在的碘蒸气测纤维扰动法被挖出来对付日益复杂的配方。德国人又发明了“浸泡法”“复写法”使之失效。法国人则开发出新的通用含碘显影剂,能使重新浸泡过的受干扰纸纤维被检测出来。但显然,这种隐写术的军备竞赛并未显著影响战局走向,与二战时军用恩尼格玛密码机被破译的后果不可同日而语;彼时德国开始用微缩影像系统替代传统隐写术,也没有证明其重要性。为此“倾注的大量资源最终都显得一文不值”。
趣味性包裹的“繁琐史学”:出路何在?
综上所述,这本排在以视角独特著称、历史读物为主的“新知文库”第63号的书,可算一部很专门的专门史著作,或者说技术史领域的查漏补缺之作。作者在自序中交代写作缘起时,也明确指出过这点。
此类写作难以避免的问题在于,所涉主题通常不会在历史上起过显著作用——否则早就被长期以来主流的政治军事史吸收进去了。因而作者考察得越细致,越容易给读者以“小题大做”之感。从“附录:玩转厨房化学实验”来看,作者所期望的读者至少还有相当部分是化学爱好者。这姑且不论,在史学观念上此书延续了19世纪兴起的趋向,就是认为历史由最大量无可辩驳的、客观的事实编纂而成。
在过去的百年间对近代历史学家产生了如此毁灭性的影响,以至于在德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出版了一大批、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枯燥无味、满页事实的历史著作和专门至极的论著,也造就了一批未来的历史学家,他们在越来越小的范围内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最终无影无踪地消失在事实的汪洋大海之中。(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
当然,搜集、整理史料也是历史学家分内的工作;史料集编得好,功德无量。但此书显然又不想写成史料集。难道真没有更好的写法吗?
至少还有两条出路。其一,干脆否认政治军事史的主流地位。为什么军国大事天然就优先于谈情说爱呢?相当部分秉持个人主义理念的现代读者,早就可以接受这样的“价值观颠覆”。如果把本书从囚徒和间谍的故事为主,改成以秘密恋情的故事为主,“隐写术”自然不再显得无足轻重;而实际上,正标题的三位主角:囚徒、情人与间谍,中间那位就偶尔出来凑个数,存在感极弱。
其二,回归主流的政治军事史。那就不能“以技术为纲”,而要以技术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为准绳,那就不宜把协同工作的密码术与隐写术分开讲述。
最后指出两点:作者有明确政治倾向性,因而对冷战中“东方阵营”更全面更无顾忌的邮件审查能力持否定态度,认为西方“在间谍战中落败可能是赢得更大的意识形态战争的代价”。这也体现在对“9·11”以来美国日益堕落的担忧上。二战之初,美国人秉承“绅士不看彼此的邮件”的精神,厌恶最有效的间谍抓捕工具——英国审查机构式的大型而高效的审查组织。1941年战时审查项目组才勉强在美国成立。冷战初起,中情局似乎遗忘了二战期间开展的大量秘密墨水研究,其邮件审查活动也只能偷偷摸摸进行,于70年代被叫停。但反恐战争模糊了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的边界,改变了一切。“如今,将近500万美国人有权调阅秘密信息”,“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美国的风气已经从‘绅士不看彼此的邮件’变成‘我们有能力轻按鼠标看到每个人的邮件’”。对此甚为痛心的作者,也许会觉得英国放弃大英帝国、无须再“审查天下邮件”是莫大的幸运。但确实,自从英国失去世界霸权、甩给美国以来,普通英国人的生活是大大改善了,而美国则债台高筑,国内矛盾日趋尖锐。
另外,用拉丁化的“乌斯”做希腊人名的词尾译音、把米利都译成“米莱特斯”之类问题,非出自古典学者之手的多数译著皆所难免,只能让译者背锅啦。这篇书评里对人物和地点译名的改动不再一一指出。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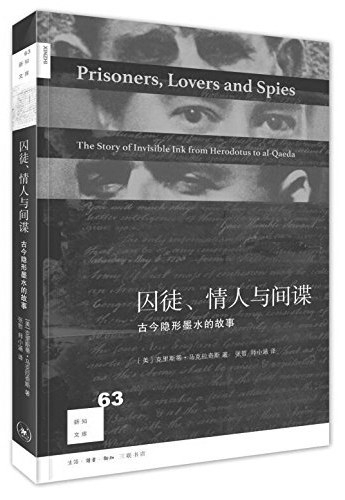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