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士大夫打造君臣可以共同接受的祖宗之法的过程中,新的政治共识逐渐形成了。一是对私人性君主权力的限制,一是对政权与治权边界的划分。北宋的政治文化生态因而表现出与其他时代迥异的面貌,尽管因为武人受抑制带来对外开拓的某种不足,但却出现了中国文化的又一次高峰。
“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这是东晋谢安(字安石)东山高卧时被时人推崇的一句名言。许多人注意到,当北宋政治家、学者、一代文豪王安石早年屡次辞官不就,因而声誉日隆,为天下所瞩望的时候,他所面临的境遇竟然与谢安差堪仿佛。天下阽危,强敌环伺,内虽承平,暗含隐忧,希求振作的“庆历新政”草草收场,超迈五代、直绍汉唐、甚至远追三代的梦想还遥遥无期。中唐以来,士大夫以道自任,希求“内圣外王”以平治天下的理想还没有真正实现,朝野上下都在寻找一位“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能够“作新斯人”(皆苏轼语)的人物。
这个人物似乎果真出现了,那就是王安石。但也正是这位死后不久便被奉入孔庙配享,晋封王爵,被宋哲宗钦许为“孟轲以来,一人而已”的人物,很快便被视作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遭到绝大多数士大夫的蔑弃。其高者尚仅否定其政而不没其人,其下者则吠影吠声,极尽侮辱谩骂之能事。于是明清以来,为之辩诬雪谤一时成风。近代以后,除了如梁启超所谓“六大政治家”的褒扬之外,因为列宁的推许,在一个以富强为首务的时代里,王安石被奉为变法图强的先驱。随之而来,王安石及其代表的学派似乎被重新发现,甚至被一些历史学家推许为宋代儒学的真正源头,连对其予以激烈批评的程朱理学都被描述为王安石的追随者了。王安石其人其学及其学派与宋代政治学术的关系,仍然有待澄清。
譬如,把王安石看成宋学的先驱之一,并反对把程朱理学等同宋学的观点,具备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假如因为王氏新学的巨大影响,以及程朱之学较其晚出,便片面强调后者对前者的继承性,又未免过于简单。不仅政治上的主流与学术上的影响不可混为一谈,而且哪些是时代的风气使然,哪些是王安石新学的独特影响,也应该具体辨析。宋学本来是与汉学对等的概念,清人用这两个概念分别代指当时的程朱理学与考据学。20世纪一些历史学家误解了这一概念的内涵,笼统地认为存在一个与汉唐学术相对的所谓宋学学派,其中王氏新学曾居主流,而蜀学、关学、洛学等则是这个学派的分支。这一理解本身便是理论汗漫的表征。正如我们不能承认有一个可以纳三民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新儒学等为一体的所谓近代学派,这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所谓宋学只能是一个笼统的时代风气的指称,并非真有一个叫作宋学的学派。
不仅如此,对于一个具有极高品格及学识的历史人物,为王安石个人雪谤当然是必要的,但同时也必须理解王安石的“受谤”之由,后者并非仅仅出于学术或政治上的意气之争。譬如,王安石变法到底和北宋崩溃有何关联,在传统思想框架下古人是如何理解这一问题的?一个品行高洁的人物何以会遭到大多数品行并不卑劣的群体反对,而且反对者甚至也包括那些在庆历新政中堪称变法先驱的人物?历史评价不能止于针对个人的道德评价,如何回到具体情境之中去理解历史,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最近,由王水照先生主编的《王安石全集》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相信对王安石的相关研究必将产生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师道缘何复归
理解王安石何以后来被否定,首先应该了解王安石最初被推崇的原因所在。这个以伊尹、傅说自期的人物,作为周予同先生所谓中唐以来“孟子升格运动”在宋代的主要政治推手,其新学之崛起本来便是这一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
孟子学的复兴,其实只是唐宋间时代精神嬗变的一个侧面。将近二十年前,我曾在一部著作中把它概括为中唐以降士大夫师道精神复兴的一个表征。大概地说,经学所谓天地君亲师,乃是根据权力的几个来源。借用今天的语言,天地对应宗教权力,君对应政治权力,亲对应宗族权力,而师则对应现世的教化权力。这些权力在每一个时代中同时存在,但相互之间却永远处于博弈状态。在汉代,教权与君权结盟;在门阀时代,族权与君权分享天下;唐宋时期,君师实现某种程度的共治;明清之际,君权企图凌驾一切,巍然独尊。
中唐以降,随着门阀解体,庶族或寒门地位上升,此前已经复苏的师道精神逐渐彰显,并在学术趋向上表现为孟学的复兴。因为坚持以“天爵”规范“人爵”,强调民贵君轻,主张士大夫于君权要“学然后臣之”的孟子,是经学传统中师道精神最直接的代表人物。由此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隋唐之际以“王孔子”自命、倡导“河汾师道”的王通,不仅在中唐以后声望渐著,并且在整个宋明时代成为学者讨论的中心人物之一。甚至在启蒙读物《三字经》中,还进入与荀、扬、老、庄相提并论的“五子”之列。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那篇名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考察了从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文学艺术到社会体制如人身依附关系等在内的多种历史变化,却唯独不及精神领域的变化,未尝不是一种缺憾。
政治经济与社会形态固然与时代精神互为表里,但与其像有些学派那样简单把精神当作被决定的产物,毋宁说前者乃是后者的承载物更为恰当。精神的变化乃是唐宋以降一切学术文化形态嬗变的总纲。师道精神的复苏带来了唐宋以后以经学为基石的整个知识体系的更新。表现在史学上,则是中唐至宋代以义法史学为中心的新史学运动;表现在文学上,则是以“文以载道”为核心的古文运动;表现在经学自身,则是以内圣外王为取向的孟学复兴运动,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兴起。
了解这一点,与其把理学家的尊孟简单看成受王安石的影响所致,不如说是中唐以来许多士大夫的共同诉求。只不过,这种师道精神为什么在史学和文学领域更早地体现,乃是因为经学义理上的变化与基于考据的史学和基于意象的文学不同,前者需要精神的纯粹自觉与更艰难的劳作。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从个体实践角度,还是作为古文运动领袖之一,王安石都确实体现了孟子学以道自任的精神,但在经术上却并没有能够恢复孟子的心性之学,反而更多地保留着玄学或道家学术的某种倾向,便是其学术尚未实现完全自觉的表征。
作为一代文豪,王安石在古文运动中只是一个后来者。早在韩愈和柳宗元那里,师道精神已经是自觉的诉求。这首先刺激了道统论的出现,由上古圣王所传,经过孔子、孟轲达成自觉的道统,成为天地君亲师一切权力的根源。可惜“轲之死不得其传”(《原道》),需要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来挺身自任。韩愈本人也因此被苏轼推许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领袖人物,这显然不仅是指文章技法而言。这种精神需要与现实的各种力量艰难博弈,但文学领域“韩门”的出现,表明它已经成为士大夫内部的某种精神传统。虽然经过唐末五代的一段挫折,但还是在宋初有了复苏的迹象。先驱者如原名肩愈、字绍先(指柳宗元)后改字仲涂的柳开,便在自己的名字中表达了对前辈的景仰,所谓“肩韩、绍柳、开文中子涂”,那显然是在向文中子以来的师道精神致敬。而北宋士大夫精神的完美代表范仲淹更是表字希文,因为文中子王通便字仲淹。范仲淹对张载等人的影响更是有目共睹。另如北宋古文运动的首要人物欧阳修,同时也是疑经思潮的代表,他的《新唐书》与《新五代史》则是义法史学的代表作。“文以载道”这一确切说法则出自北宋五子之首周敦颐。王安石之以孟子自任,及后来表彰孟学,都是这一大潮的产物,对其重要性似乎不必强调太过。
但这位“拗相公”所具有的某些性格特征,却很快使他在同时代的士大夫中脱颖而出。野史所盛传的一些轶事,譬如他的不修边幅,他的不近人情式的矫世励俗,不管是否真切,都在烘托着他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形象。他的辞官不出,他的难进易退,符合孟子对“不召之臣”及“学然后臣之”的期许;他所坚持的经筵坐讲,更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以师道抗衡君道的凛凛高标。至少从个人实践上,他的所为符合孟子对师者的期许。加上他在文学上不世出的天才,学术上的独树一帜,政治上的宏伟抱负,以及“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那种舍我其谁的气概,在一个对个人操守的期许超过制度革新的时代,真可谓“安石不出,奈苍生何”!
士大夫的自觉
与现实权力结构调整
师道精神的复兴意味着新兴士大夫阶级的群体自觉。至少自唐朝开始,随着社会本身的结构性变动,这种群体自觉逐渐开始影响现实的权力结构,以及士大夫的精神诉求。历史学家早就注意到自唐初开始日益彰显的君权,与包括关陇在内的门阀士族之间的矛盾纠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造纸术与印刷术使知识的传播日益容易,南北朝时代被世家巨族垄断的学术文化,所谓“诗礼传家”的传统,受到了虽然缺少经学传承,但又很容易通过博学方法表现为文学才情的新兴士人的挑战。而在南北统一过程中居于士族群体弱势地位、却在文化发展上居于前列的南方士族,也不同程度参与到这一挑战的过程之中。
这些复杂变化的结果便是隋炀帝以来科举制度的发展。一方面,科举制度通过考试来取士的方法,建立了君权相对门阀士族日趋优势的地位;一方面,从隋炀帝到唐太宗等统治者对文学的倾慕,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学在科举考试中地位的逐渐提升,为门阀制度退出历史舞台找到了新的替代机制。这个机制虽然在唐朝还长期表现为以经学为关键的明经科,和以诗赋为首要的进士科的相互博弈,但其大方向显然是确定了。在社会经济相对稳定的时代,科举考试无疑可以使更多的在野英豪被纳入到统治机器之中。因此,中唐以后,师道精神的复兴首先表现在文学领域,便不难索解。所谓“传心之法”的道统,说穿了,便是强调知识或大道的接契可以通过自得,而不必经由“诗礼传家”形态的师法。所谓自得,正是孟学的精义。
安史之乱虽然使一部分门阀势力遭到打击,但其后的藩镇割据同时也成为新兴武人的堡垒。骄兵悍将、尾大不掉,成为晚唐五代君主挥之不去的梦魇。这一局面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可以说稍为缓解,但倘欲长治久安,势必需要某种制度性的力量。除了各种政治上的分权机制外,后者主要表现为科举制度下文官政治的发展。与唐朝相比,宋代科举制度无论从录取人数,官员除授的方式,无疑都更有利于新兴士大夫群体。文官群体的庞大,甚至造成颇受诟病的“冗官”之弊。但也正是因此,使得获取天下与五代初无二致的赵宋王朝,摆脱了武人干政的魔咒,与汉唐等伟大王朝一样,奠定了自己真正的立国规模。
在传统时代,这种立国规模常常被称为“祖宗之法”。从经学角度来看,每一时代的立国规模,其实便是支撑一个时代建立稳定体制的政治共识。因为是共识,所以尽管贯以“祖宗家法”的名义,但与其说是某一个时代的开国君主所订立,不如说是朝野上下各个主要政治集团相互磨合的产物。北宋首先用赎买的方式换取了武人的兵权,通过身为文官的枢密使加以掌控,同时推行右文政策,无形中鼓励了文官政治的发展。但这种政治格局的变化并非只是一种历史的盲动,必然会反映在政治理念的变化之中。在“宰相需用读书人”“不杀士大夫”,这些偶然的表述逐渐被士大夫打造成君臣可以共同接受的祖宗之法的过程中,新的政治共识逐渐形成了。
这种共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私人性君主权力的限制,一是对政权与治权边界的划分。通过君主与士大夫的分权,一方面可以分割武人的权力,一方面激发士大夫的主体意识以及对政治体制的认同,并因而达到长治久安。北宋的政治文化生态因而表现出与其他时代迥异的面貌,尽管因为武人受抑制带来对外开拓的某种不足,但却出现了中国文化的又一次高峰。
大概地说,君权即政治权力本身包含两个层次。作为统合人群的公共性政治而存在的,即所谓公共性君权;作为具体承担政治权力的某一组织或个人,是所谓私人性君权。因此,政治的根本问题,往往表现在私人性君主权力如何有效地承担其公共性职能。当二者不能有效协调的时候,不足以承担公共性职能的这个组织或个人便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必然走向覆亡的命运。
按照顾炎武的说法,宋朝可以称作家法并度越前代的主要有几个方面。“人君宫中自行三年之丧,一也;外言不入于梱,二也;未及末命即立族子为皇嗣,三也;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汉唐之所不及。”(《日知录·宋世家法》)所谓“外言不入于梱”,其实是防止外戚干政,保证君权通过正常的官僚建制予以实施,这是对文官分有治权的尊重。至于行三年丧与立族子为皇嗣,则是对私人性君主权力的限制。“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也是对君权陵跞治权的防范。因此,顾炎武的这几条总结,主要都是从私人性君权受限的角度而言的。从历史实践来看,私人性君权受到制度约束,是钱穆等先生所谓北宋时代君主与士大夫共治(我称之为君师共治)的基础和前提。
对政权与治权的划分,主要体现在对治权所具有的某种独立性的肯定。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相权的肯定。我们很容易注意到,为了防止宰相专权,宋代设置了非常严密的分权机制。但更重要的是,北宋朝野上下对“人君之职,唯在置相”这一观点的共识。所谓共识,便意味着这不仅是士大夫的一种观念,而是得到君主背书的观念。譬如王安石拜相,宋神宗的诏书便明言“尔则许国,予唯知人”。这意味着君主享有政权,而治权则是以宰相为代表的外廷士大夫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这为宋代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张载)那些伟大理想提供了一种友善的制度环境。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何以南宋宰相真德秀在所进《大学衍义》一书中,只是从格物致知到修身齐家为止,因为对于君主而言,他的主要责任是诚意正心,治国平天下则是大臣之责。朱熹一生在朝时间很短,但其上奏皇帝,却主要以诚意正心为言,颇为后世所诟病,以为迂阔,其实必须放在宋代的政治环境中去理解,才可以心通其意。当然,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各种政治权力永远处于博弈状态,但并不影响政治共识的存在,这是人类许多政治斗争斗而不破以及一个体制保持稳定的前提。
其次表现在科举取士的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观念变化。唐朝采纳了科举取士,但如何使新兴的科举士人不是在雁塔题名之后,便因为榜下招婿或与许多出身门阀的大臣结成门生座主关系,成为门阀士族的补充力量,却也颇费了一番脑筋。高宗及武则天以后开始的殿试制度,致力于把新进士打造成“天子门生”,至少从观念上表达了这种努力。从具体的角度而言,为什么殿试制度发生在高宗及武则天时代,也是因为与李唐已经离心的武则天更需要迫切找到在旧门阀之外的新生支持力量。到了宋代,尽管榜下招婿之风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但宋朝所面对的是黄巢及朱温之后门阀一蹶不振的局面,尽管新兴士族也同样以婚姻等方式相结,与唐朝以前门阀体制显然是不一样的。但即便如此,宋代的士大夫仍对皇帝亲自主持的取士行为颇致不满,王禹偁在真宗即位之初,便上疏“谓举选非天子亲临之事,请以归有司”。这一观点被仁宗时的大臣田况记入所撰《儒林公议》,表达的当是许多士大夫的共同意见。殿试后来的常态应该视作政权与治权划分边界后的折中状态,即皇帝只是为会试中选者分别等地,但选拔权却掌握在外廷士大夫的手中,尽管依然被称作“天子门生”,但新进士与选拔者的门生座主关系其实是得到了保留。这种经过分权的科举制度,实际上使宋以后的治权在某种程度上掌握在士大夫的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某种政治制度,不能只是纠结其极端运作状态,更不能一言以蔽之,而是必须与不同时空下的观念、运作等具体情境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宋以后逐渐得到强化的“青天”观念才具有了现实意义。李白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在这里日指代君主,浮云是指皇帝身边的佞臣。但宋代以后,民间对青天的向往则转到包拯这些守正不阿的执法清官身上。南宋金元时代,包拯就已经在民间故事里成为青天的典型。
动摇“立国之本”?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所谓立国规模就如同一座房子的地基,地基的牢固程度,决定了这座房子的大概寿命。譬如唐朝立国,如陈寅恪所言,依靠关陇集团与府兵制度。当府兵制度逐渐消歇,且重心移往东都,唐朝立国便出现了根本性的危机。同样,明代的内阁制度,民国的临时约法,1949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政治共识的意义。假如这些共识遭到破坏,相应的政治体制便会遇到危机。
北宋时代的政治共识便是所谓君师共治。士大夫以师道自任,对君主学然后臣之,君主则与士大夫分享治权,以换取后者的支持。可以说,王安石上台的过程便是这一政治共识的完美体现。甚至当朝皇帝也不吝褒美之辞,不仅说他“觉斯民也,任同伊尹之心;如苍生何,居起谢安之志”,而且“功已齐于荀、孟”,“名当迈于皋、夔”(《王安石进左仆射制》),古来人臣,受此推崇,可以说无以复加了。
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王安石得君如此之专,因为当王安石的政策遭到外廷的反对的时候,宋神宗几乎总是维护王安石的体面,对反对的声音予以压制。后世学者大都把这看成宋神宗对王安石个人的知遇,或对变法内容的认同,这些因素也并非不存在,但假如仔细进行考察,问题便没有这么简单。关键在于宋神宗通过支持王安石的变法行为,打破了对私人性君权予以限制的祖宗之法,并因此扩张了君主个人权力。
《宋史·王安石传》的一则记载透露了此中消息。当御史中丞吕诲上疏指目王安石为奸佞之徒,韩琦、司马光这些重臣也都出面反对王安石的时候,王安石不仅“上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而且还说了一段关键的话:
“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重轻,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于是陛下欲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
这里的流俗便主要指外廷士大夫的声音,而这个声音又是士大夫群体长期形成的某种“公议”。陈襄上言:“且以为流俗之论,亦不思之甚也。故天下之公议……君人者不可不察。”(《论王安石札子》)在这个意义上,以师道自任反映的本来是治权与政权关系的问题,但到了王安石这里,却变成他本人与宋神宗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作为治权承载的外廷士大夫被推到了君主个人权力的对立面。尽管王安石本人还是师,但当他与皇权结成一体而与流俗相抗之后,自己则成为私人性君权的代言人。这与明代张居正改革时的情形是极为类似的。
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外廷士大夫,包括许多支持庆历新政的士人,所反对的并非一定是王安石新法的具体实施,更主要的是因为王安石变法打破了此前一百年所形成的政治共识。譬如李常在《上神宗皇帝论王安石》中便直接指斥皇帝:“臣不知陛下甘其所以得利,而力行之耶?徒悦其顺适心意而恶违忤之耶?抑曲徇安石而苟为之耶……凡古之所谓众贤和于朝,与舜命九官,济济然和之至者,非雷同阿党,能顺适人主之心意之谓也。”司马光则批评王安石“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廷之事。”(《上神宗论王安石》)陈渊则批评他引荀子“擅生杀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来解释《尚书》“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是“劝人主揽权”(《尚书新义》卷七)。
这样,王安石当政后的蔑弃流俗,不恤人言,其实是用一种粗暴的方式否定了北宋的“祖宗家法”,并以“陛下当制法而不当制于法”歆动神宗(李光《论王氏及元祐之学》),由此造成了北宋精英统治集团的崩解局面。这是北宋最后哲宗、徽宗、钦宗几个时代党争延续的直接根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王安石变法的本意在于富国强兵,但却在客观上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把王安石说成是北宋灭亡的祸首固然未必,但却无疑可以视作始作俑者之一。因为假如没有宋神宗的最后决定,王安石变法是很难正式推行的。问题是,作为北宋士大夫师道精神的代言人物,最终反而成为私人性君权的捍卫者,如何从义理上解释这一现象?
理解这一问题,还是应该回到孟子。我们知道,师道精神的现实表征,首先是以道自任,这无疑体现了自任者铁肩担道的勇气。但假如勇气有余而证道不足,则以道自任难免成为以道自居的借口。这就是孟子所谓“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佛家称之为“我慢”,墨者自诩为“尚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举凡以剑传教之宗教家,及强人就己的各种意识形态,都是好为人师的表现。其师心自用、好为人师,好像是符合天道之“诚”,实则不知自反,终于陷入侮夺、自暴而不自知,走向了“诚”的反面。(拙作《〈孟子·离娄上〉讲疏》)《中庸》所谓“不诚无物”,信然。
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方面贡献。但其性格中的刚愎峭拔,其学术上的“好使人同”,经过政治权力的放大效应,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政治走向。假如重新思考北宋灭亡的历史原因,那么王安石主政时期,以“祖宗家法”名义存在的政治共识之被打破,无疑是不可忽视的角度之一。
《王安石全集》(全十册),王水照/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第一版,88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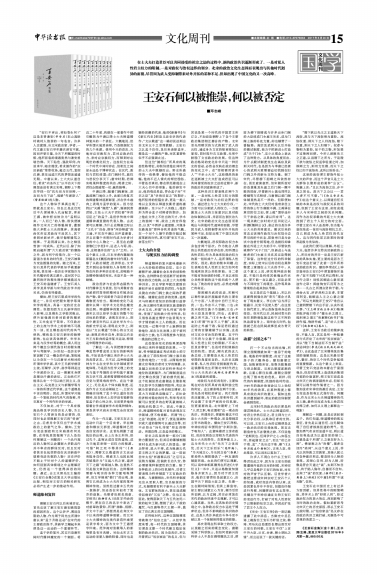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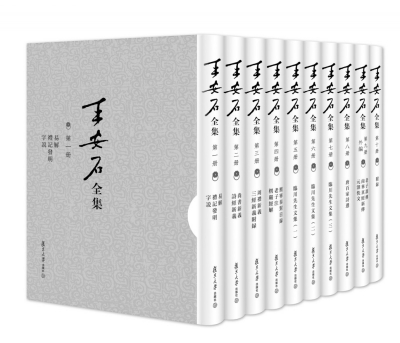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