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2006年《温州学院学报》宋立堂署名文章“《醒世姻缘传》黄注辨疑——与黄肃秋先生商榷”,心中惆怅。即使截止2006年,黄肃秋也逝世十七年了。与谁“商榷”呢?于是,使人想到了学术成果的影响以及与这些成果相关联的学者的性格、人品。老先生们,一生都有许多劳绩,往往持续发酵,产生影响。无论对他(它)们是赞扬,还是批评,也许是兼而有之,只要没有堕入别有用心的恶毒攻击或投其所好的溜须拍马之末流,均能沾溉后昆。这就如同对孔子的评说,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属于进行态。
一、从茅盾题签书名说起
黄肃秋于1979年在群众出版社出版了由他今译的清人朱逢甲所著《间书》。图书出版之前,社方请茅盾题签书名,茅公说:“我与黄肃秋很熟悉,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在一起工作了。”于是,欣然命笔。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肃秋的恩师郭绍虞介绍他去台湾师范学院国文系担任副教授,讲授中国古典文学。他的左翼文化思想不容台湾当时的政治环境,在“四六”事件中,他为了营救学生,被校方解雇、当局通缉(笔者按,凤凰卫视网上,有人介绍一位晚年生活在上海的台湾人朱实,说他“当年的老师叫黄肃秋,从他那里,朱实知道了鲁迅。他将黄肃秋比作藤野先生,如饥似渴地吸取着这位文坛巨匠的养分”。朱实就是因“四六”事件而从台湾流亡大陆的)。《金陵春梦》的作者唐人(严庆澍)在香港介绍他去北平工作,叶以群在北平前门火车站接车。之后,他的组织关系放在中央统战部。黄肃秋担心自己跟不上新中国的思想、形势,主动要求去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了一段时间,被周扬选调文化部艺术局编审处,在茅盾、周立波的领导下编辑中国第一部《新文学选集》。编辑图书的过程中,黄肃秋与艾青、赵树理、何其芳、李广田、洪深、丁玲、叶圣陶等人有密切地书信交往,这些人大抵是《新文学选集》选目的作者们。由于他工作认真努力,茅公曾奖励他三百元钱,但几十年后的茅盾记忆产生了误差,以为黄肃秋是编审处的副处长呢。
《新文学选集》的编辑活动,产生于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之前,这是许多人不知道的事情。
黄肃秋的文坛本色是诗人。他年甫弱冠,便与青年哲学家何培元一起参加了左联。1932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爱与血之歌》,由李苦禅设计封面。这本书的版权页镌刻细致:第一个长方块署有“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付印民国二十二年六月出版”字样;第二个长方块署有“爱与血之歌实价大洋五角(外埠酌加寄费)”字样;第三个长方块署有“有著作权印玺(黄肃秋)”字样;第四个长方块署有“著作者黄肃秋发行者北平宣内大街人文书店”字样。反映出民国时期出版物重视出版流程和版权的特点。当时的图书馆尤重作者题签赠书,国立北平图书馆就藏有黄肃秋于1933年6月赠予该馆的亲笔题签《爱与血之歌》。后来,黄肃秋又出版了《漂泊者之歌》《死城》《寻梦者》等诗集。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琉璃厂的雷梦水给群众出版社来电话,说,在整理民国旧籍时发现黄肃秋的诗集《寻梦者》。黄肃秋的公子黄岳和我便把这本诗集从琉璃厂取回来,“完璧归赵”。《爱与血之歌》的作者题签本,也在改革开放之初由北京图书馆检出。
也许是个人偏好的缘故,我更喜欢黄肃秋的旧体诗。
1972年初,黄肃秋在文化部的五七干校做烧锅炉给干校同学灌暖瓶的工作。他身体强健,干活麻利,但待得实在烦闷,遂口占一绝:
雪压冬青大地春,云开远岫楚天亲。端居耻坐丹江叟,愧尔东西南北人。
诗中用了孟浩然“端居耻圣明”和郑板桥“任尔东西南北风”的熟典,反映出诗人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深刻观照。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黄肃秋又口占一绝一律:
亿万银星满树栽,花环谁见越重台。长安道上人如织,一片哀声动地来。万艘东风腹内撑,任劳任怨过平生。斯民有泪浇泉壤,当道无人洗罪名。三载斗争说儒法,一身勋业贯公卿。临终频嘱焚冤骨,水水山山葬不成。
诗不用旧典,淡化了书卷的雅味,益显“我手写我口”的挥洒,而且颇有一番深意。可以从中体味作者的内心生活和社会真相。
诗酒从来不分家,黄肃秋颇喜饮酒。以至黄夫人张秀莹抱怨道:“都是跟老金头学的。”老金头,指清朝睿亲王多尔衮的后裔金寄水。黄肃秋从干校回到北京后,曾与金寄水一起在人民卫生出版社校点《本草纲目》。俩人“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互相推重。
黄肃秋自云崇文门附近豆谷胡同的寒伧居所为“两间堂”。大的一间屋子的北墙上,便贴有金寄水的词作。我不记得具体内容了,学的是宋词婉约一流,落墨极清丽蕴藉。小的一间屋子的北墙上,则贴有学者、书法家徐无闻赠其“两正”的诗作:“无复惊涛拍岸容,游人犹唱大江东。先生已脱沧桑劫,却道人生似梦中。”
黄肃秋偶尔用一种抑扬顿挫的调子吟唱这首诗。他经常唱诗,尤其是唱音乐气质较好的诗,已养成了习惯。笔者听他唱得最多的还是王昌龄《春宫曲》(昨夜风开露井桃)、《出塞二首其一》(秦时明月汉时关)和韦庄《台城》(江雨霏霏江草萋)。
黄肃秋的诗人气质决定了他具有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的特点。这一特点必定升华到骨鲠之气的流露和爱憎分明的理性上。
他尊师,臧否人物一般不涉及老师。我问他对郭绍虞、刘永济、孙子书等人的评价,他说:“师辈,不议。”尤其郭绍虞,那是黄肃秋在燕京大学国文系读书时的系主任。他的“两间堂”南墙上,贴有郭绍虞赠予他的对联“星长拱北 川自向东”。书法端庄雄健、苍老遒劲。我多次见过黄肃秋坐在沙发上凝望着这幅对联出神,足见珍爱之至。黄肃秋在民国期间的所有工作都是郭绍虞帮助他找的,郭绍虞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都是黄肃秋介入安排的,并请郭先生为一些著名出版物题签。当他听到郭绍虞去世的消息,大哭一场。对我说:“郭先生与我份是师生,情同父子。”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的前夜,黄肃秋的工作单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他对我从不隐瞒他对某些同事的看法。他说某同事在蒋介石六十岁生日时“供奉蒋委员长长生禄位”。他说某同事品质恶劣,到北京图书馆窃善本书,真给读书人丢脸。他说某同事自吹是某个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其实纯属骗子。黄肃秋一言以蔽之:“魏无牙门下客——无耻(齿)。”
黄肃秋对党的意识形态管理者和对他治学有教益的人,经常念叨其好。他说胡乔木给他校勘注释的《西游记》提了许多中肯的意见,连细小的标点符号都给予改正,治学态度颇为严谨。他说赵朴初帮助他注释《西游记》中的佛教术语。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他尊敬冯雪峰,佩服巴人。巴人1957年发表杂文《论人情》,强调文学作品中的人性问题,受到批判。黄肃秋挺身而出,为巴人说话。他对20世纪50年代因胡风事件在改革开放之后被知识界诟病的舒芜则十分羡慕:“舒芜比我有才,二十岁时就写出了《论主观》这样的文章。”“两间堂”的楼下邻居便是舒芜。我亲眼见过黄肃秋轻轻地用脚跺破旧的地板,得意地说:“我把舒芜踩在脚下。”启功造访“两间堂”,打趣道:“你踩楼板轻一点,楼塌了,别砸坏了舒先生。”
有一位对黄肃秋多有教益的好朋友——萧涤非。他俩都酷爱杜诗,黄肃秋给萧涤非的《杜甫诗选注》当责任编辑。萧造访黄宅,谈洽甚欢,
屁股一沉便不想走,在门外的出租汽车司机发怒了:哪有这样的顾客,让我傻等几个小时……
对师辈,黄肃秋也不是绝对不议。有这样一件事:20世纪50年代,黄肃秋陪同俞平伯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平老叮嘱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有关《红楼梦》的一些珍贵资料,不要借给周汝昌这些人。黄肃秋当时不便说什么,事后表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垄断资料恐怕有失风范。
二、与钱锺书的一桩公案
钱锺书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了他的名著《宋诗选注》,一开始便遭到了同行的批评。这些批评有褒有贬,旷日持久,在改革开放之后,形成了一本书的学术史。笔者手头没有《宋诗选注》,但读过《文学遗产》2008年第六期王友胜署名文章“五十年来钱锺书《宋诗选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下简称王文)和2016年《文学评论》第六期李松署名文章“钱锺书《宋诗选注》的诗学困境与‘十七年’文学批评”(以下简称李文)。王文征引史料似乎稍微多一些,李文征引史料则较为详细。他们都征引了黄肃秋于1958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署名文章“清除古典文学选本中的资产阶级观点——评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
李文作者明显年轻,欠缺人物和历史知识。他征引了三个人的“负面评价”:胡念贻、黄肃秋、周汝昌。并云他们属于“文学所晚辈学者”。实际上胡念贻也不年轻了,黄肃秋则与钱锺书同辈,周汝昌的年龄介乎于胡、黄之间。除了胡念贻工作单位是文学所,其他两人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李文还说这三个人对钱锺书“以‘钱先生’相称,并未将对方视为思想上的敌人”。在学术界乃至全中国、全世界谁曾把钱锺书作为“思想上的敌人”?不称呼其“钱先生”又称呼什么呢?至于李文所述“这些批判文字带有某种应付、表态的意味”,我可以负责任地讲,黄肃秋对钱锺书的批评是真心实意的,并且九死而不悔。
徐公持在《胡、曹、陈、蔣四位学长印象记》一文中,谈到胡念贻的“学术适应能力”时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他“虽然不是主导者和中坚人物,但他能够‘随大流’地写出符合当时运动需要的文章来”。胡念贻以研究中国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为己任,无论写立论,还是写驳论,都是拿手戏。况且与钱锺书同事,不排除事先通过气,从而演出一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好剧。黄肃秋则与钱锺书素不交往,他擅长对古籍的编选、校勘、注释,《西游记》校注、《醒世姻缘传》校注、《史记选注》《唐人绝句选》《杜甫诗选》等等,都是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留下的作品。长于比次考索的黄肃秋也写过不多的论文,即20世记60年代在《新闻战线》上发表的四篇《文心雕龙》创作论。他还想写一篇“论论辨”,但未完成。论辩包括驳论,但“论论辨”就只能是立论了。他这辈子写的驳论仅此一篇——批评钱锺书。尽管黄肃秋十分尊重钱锺书,在他睡榻旁的小桌上,摆放的书就有《谈艺录》和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经常翻阅学习,从中受益。
黄肃秋祖籍山东,生长在东北。九一八事变后,他便有家难归了。在《爱与血之歌》中唱道:“我来自那迢迢的远方,白云深处有我的家乡。父母都被敌人杀戮,兄弟们也都从此流亡。噙着眼泪,背着行囊,担着家国走向四方……”这首作品是诗人在北平大街上的讲演朗诵稿。诗中所蕴含的悠长悲伤的爱国主义情怀,渗透到他的性格深处,与更具阳刚之气的文天祥《正气歌》《过零丁洋》的精神意脉相通。拜托李文,我知道了黄肃秋对《宋诗选注》之不满,不在该书的评与注,而仅仅在选目上,即不选以上述文天祥的两首名作为代表的一系列充满了高度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的诗篇。李文把黄肃秋的旨意看得很清楚,黄称赞《宋诗选注》之处恰恰“来自他对爱国主义诗歌的重视”。仅以文天祥《正气歌》和《过零丁洋》为例,黄肃秋认为这是宋诗的大广告,体现了中华民族集体意识对宋诗的认可,亦反映出历代选家集体意识对宋诗的认可,不选便“没有充分注意到作品的思想内容”(黄肃秋语)。他在晚年曾对我说,即便是一个只选一百首宋诗的小选本,至少也应该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吧。这不是什么艺术标准或审美趣味不同的说法就能搪塞过去的,就如同杜诗的选本,《三吏》《三别》一首不选,《秋兴八首》一首不选,再不选《北征》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在选目上脑筋出了问题是一眼便可得知的。
据王文讲,钱锺书在1981年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说:“这部选本不很好,由于各种原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正气歌》和《过零丁洋》显然不属于“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的作品,而是钱锺书从来就要舍弃的作品。我曾仔细阅读过王文和李文,《宋诗选注》学术史的发展过程中,连燕堂在《读书》1980年第八期上发表署名文章,支持当年黄肃秋的观点,认为“以气节著称的郑思肖、谢枋得”的作品均应选录。王水照在《文学遗产》2006年第四期发表署名文章,回护钱锺书的批评立场,认为钱氏不选《正气歌》体现了他以文学为本位,并从结构与立意上的模仿(笔者按:这难道就是钱氏所云“优孟衣冠”?其实,他的《谈艺录》《管锥编》之体式也是有所借鉴的,还是用借鉴这个词好)、“中间逻辑亦尚有问题”等角度,佐证其依据之坚确。我理解,王氏的文学本位说与黄肃秋当年批评钱锺书“艺术至上主义”,当属同义语。这柄双刃剑,当年可刺向钱锺书,今天可刺向黄肃秋。还有一个叫小川环树的日本人,为钱锺书不选《正气歌》做出了“正面评价”的解释:“钱氏发现,文天祥被蒙古军抓捕以前和被捕以后的作诗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诗是平凡的,被捕后的诗则多有情感沉痛的好作品,会不会钱氏认为《正气歌》虽然沉痛,却还算不上好作品。”《正气歌》“算不上好作品”的说法倘能成立,中国人能答应么?这个日本人的推测是在给钱锺书抹黑。
还是黄肃秋的老朋友吴晓铃慧眼。
黄肃秋和吴晓铃是“学长”和“学兄”的关系——前者从燕京大学毕业,后者入学进校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科学院文学所工作的吴晓铃和黄肃秋业务接洽较多。他们都属于经常与郑振铎直接交往的人物。记得,两人都对《金瓶梅》研究感兴趣,20世纪80年代,河北大学的朱星教授向吴晓铃请教《金瓶梅》的方言问题,吴晓铃说:“你去问黄胖兄,他懂《金瓶梅》的方言。”1974年3月18日夜晚,吴晓铃给远在一千公里之外的黄肃秋写了一封信。
肃秋兄:……
我连已有其芳、平伯、世昌、子书四人退学返京。你的对头钱锺书是邮递员,每天念洋文字典,十八天写给老婆“鬼子薑”廿二封信。与我合作烧锅炉时从未碰过一次炉子,只是在我晚间封火时通一个火眼时连连叫“好”不止而已。我这才认识到什么叫做“顽固不化”了。
匆匆,希时赐好音!
吴晓玲的这封信写于“斯文扫地”的时代。吴氏幽默在短短的几行字中尽显。我通过这封信解读钱锺书:任何时候都不忘记外语的作用——《谈艺录》《管锥篇》《七缀集》的作者自当如此;与杨绛夫妻关系敦睦;对俗务不屑或不为,轻灵地躲开;对外部世界则进行会心地具体评判。笔者隔岸观火,通过一个人的生活细节瞭望其治学风貌。是的,钱锺书面对黄肃秋耿耿于怀的《正气歌》和《过零丁洋》,采取鹤立的超然姿态,而且“顽固不化”。
对于王文和李文所述“极左”的政治语境,笔者仅举一个旁证予以说明之。黄肃秋在古籍刊行社成立后撰文呼吁影印古籍:“古典文学的研究资料,有不少是所谓‘海内孤本’,一经垄断,即成了少数人的‘奇货’,他们固然可以根据这些资料写文章,当‘专家’,而更多的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研究工作者,和这些资料却无缘相见,这就大大限制了、妨碍了这些珍贵资料发挥它们的更大效果。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作风吗?”这段话批评学术界垄断资料的不良现象,虽然使用了“资产阶级作风”的政治术语,但不能不说它所涵笼的旨意却十分正确。一旦廓清历史的阴霾,人们都会与时俱进的,选择新的对话方式进行学术争鸣。
三、《间书》的出版及其他
《间书》为清咸丰年间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的产物。当时,除太平天国反抗清朝统治的起义,贵州也绝非等闲之地,爆发了苗族和各族人民的起义,持续时间较长,直到清同治十一年(1872)才被镇压下去。《间书》的作者朱逢甲参与了对贵州农民起义的镇压活动。他为了给朝廷的这种镇压活动出谋划策,收集了古书中经史子集大量材料,对我国历史上的间谍活动概略地加以评述,是为《间书》。换言之,实乃一部深蕴战略学遗产的中国古代间谍史话。
群众出版社出版的《间书》是黄肃秋翻译的。直到《间书》出版了将近四十年的今天,我依然只看黄肃秋的译文,而不读原著。古文今译的学问很大。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的余冠英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搞了一些古典文学的选本,但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在《诗经》今译上的成就。所幸陆石夫人赵中认识黄岳,通过黄岳找到黄肃秋组稿。时间大约在1977年底1978年初,比赵中到中华书局索要《我的前半生》的旧型时间稍早。此时,黄肃秋正在搞《西游记》补注,延宕了一段时间,由黄岳承担校勘注释、黄肃秋今译的《间书》于1978年11月交稿。
黄肃秋对《间书》似乎并不介意,从来未跟我提及。他经常跟我提及的是至今已经累积印行三千万册《西游记》。但是,就是因为《间书》的出版工作启动,给黄肃秋带来意想不到的机遇。其时,李文达已由群众出版社调入刚刚从中国政法专科学校升格的国际政治学院担任教务长。他顾“两间堂”的茅庐,诚邀黄肃秋去该校任教。1978年12月16日,李文达致黄肃秋一封信:
肃秋同志:
我部副部长兼校长凌云同志,想和您见见面,谈谈,同时见面的还有罗大冈同志(法文)杨善荃 同志(英文)等。时间:下星期二(十九日)下午,地点可能是北京饭店,到时我去车接您。
在干校劳动时,黄肃秋自云:“五十青春去不还,如今六十正当年。”然而人民文学出版社令其退休返京,给他打击很大。他的档案曾被退回街道,又被启出移至国际政治学院,居然复职了,而且直到去世也未退休。这让他当年的许多老同事,看在眼里,心里酸酸的。
国际政治学院(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前身)为公安系统的第一所本科院校。当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还是中央政法干校。黄肃秋是国际政治学院最早的三五个教授之一(记得还有一位报告文学作家黄钢),而正是靠着这几个教授使得国际政治学院在教育部申请获得了国家重点院校的资格。公安部领导求贤若渴,这是多么值得人们怀念的改革开放之初一所草创院校生命中那时光。而对于群众出版社而言,《我的前半生》《金陵春梦》《程一鸣回忆录》《间书》《福尔摩斯探案集》《点与线》等书的相继出版,确定了恢复之后的出版社出书的特色和方向。
黄肃秋先生对我厚爱有加,曾题签赠送我一本他编选的《杜甫诗选》: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此朱熹《鹅湖联句》诗也,录为向荣老弟学习一助。
黄肃秋喜欢“穿着破皮鞋”的诗人裴多菲和“麻鞋见天子,衣襟露两肘”的诗人杜甫。但作为走南闯北之人,他在古稀之前没有去过成都。当他第一次拜谒杜甫草堂之时,欣奋激动,口占一绝:
皓首皈心拜草堂,斯人遭际实堪伤。疮痍满目无归处,独有文章千古香。
这是黄肃秋平生最后一首诗。他对杜诗和文天祥诗的尊崇从来都依据知人论世的原则而不用唯文学眼光。他曾经向我背诵文天祥《集杜诗·自序》中的话:“……子美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性情同哉?”是的,伟大的诗人性情是相通的,而他们的性情又遗传给黄肃秋。还是艾略特说得好:“一部作品是否为文学诚然全靠文学标准来决定,一部作品的‘伟大’与否则不能单靠文学标准来决定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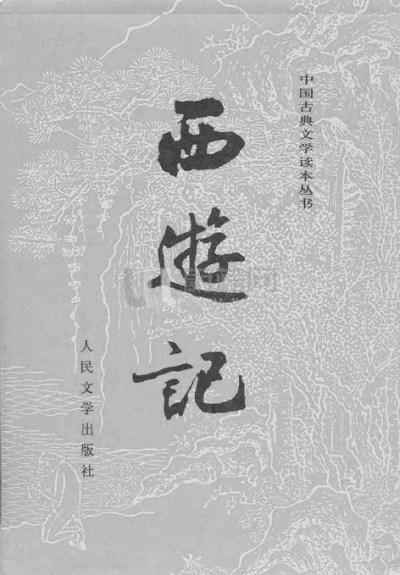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