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选的临近,法国的政治空气变得更加诡谲。右翼思想家的声音引人注目地占据了上风。左拉那样的知识分子过去是百里挑一,如今已是凤毛麟角,甚至九牛一毛。
人们心目中的“法国知识分子”死了吗?在七十岁的以色列历史学家什洛莫·桑德(ShlomoSand)看来,是的。
从恐犹症……
《洛杉矶书评》2月10日发表该刊历史版编辑和加缪专家罗伯特·扎列茨基(RobertZaretsky)的文章,介绍桑德在法国出版、引起广泛反响的新著《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从左拉到韦勒贝克》(Lafindel’intellectuelfrançais?DeZolaàHouellebecq)。
桑德致力于剥下法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披在身上的英雄外衣。如果法国知识分子的标准是献身真理和公义,那为什么他们中的大多数非要落井下石,坚定地置德雷富斯上尉于死地。每有一个为德雷富斯挺身而出的左拉,就有几十个为军方立场辩护的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Barrès)和夏尔·莫拉斯(CharlesMaurras);每有一张发表左拉《我控诉……!》的《曙光报》,就有几十张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反犹主义加油助威的主流报纸。桑德还引述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夏尔(ChristopheCharle)的研究指出,包括批评家莱昂·布卢姆(LéonBlum)和诗人夏尔·佩吉(CharlesPéguy)在内的法国文化界的先锋派并不仅仅出于良心才为德雷富斯辩护,他们还要以此挑战束缚文学创作的保守势力。
桑德认为,法国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兴起源于犹太人恐惧症的爆发,而它在一百多年后的衰落与瓦解则与伊斯兰恐惧症的勃发直接相关。今天的法国知识分子无法摆脱方兴未艾的伊斯兰恐惧症。许多头面思想家表现出的反穆斯林情绪,甚至比罗贝尔·布拉西亚奇(RobertBrasillach)、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勒(PierreDrieuLaRochelle)、塞利纳和莫拉斯等人当年所持的反犹思想更为阴暗。
1945年2月,因为通敌,作家布拉西亚奇被执行枪决。作家德里厄也因为与纳粹合作而获判死刑,但他在牢房内自杀,从而逃脱了行刑队。“我一生都在奉行心目中知识分子的责任。”德里厄说。
今天,部分由于无处不在的电子屏幕的缘故,小说家米歇尔·韦勒贝克(MichelHouellebecq)、哲学家阿兰·芬基尔克罗(AlainFinkielkraut)和记者埃里克·泽穆尔(ÉricZemmour)等名人已非传统意义上“知识分子”,而更像已故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所说的“提供文化快餐的快餐式思想家”,但桑德认为,这些人端出的精神食粮不只快,而且有毒。
在他看来,韦勒贝克2015年出版的畅销小说《屈服》(Soumis⁃sion)描写了伊斯兰势力控制法国政治、文化和社会大权的令人不安的前景,在某种程度上俨然爱德华·德吕蒙(ÉdouardDrumont)1886年的反犹主义巨作《犹太法兰西》(LaFrancejuive)的翻版。芬基尔克罗的《不快乐的身份》(L’IdentitéMalheu⁃reuse)和泽穆尔的《法国的自杀》(LeSuicideFrançais)虽有风格上的不同,却对所谓国家的“自杀”做出了一模一样的诊断,即大规模移民将导致穆斯林统治法国。他们不知疲倦地哀叹法国知识界和文化界的衰落。桑德指出,“他们的书虽然平庸但一直大获成功,证明了这种观点〔知识分子的衰落〕并非完全的虚言。”
2015年11月13日的巴黎屠杀发生过后,韦勒贝克刊文指责当局过于松懈,桑德视之为以强烈的道德感参与公共事务、总是站在无权者立场上发声的“巴黎知识分子一个漫长周期的既悲且喜的终结”。这一传统始于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而或多或少止于布尔迪厄和福柯。
……到伊斯兰恐惧症
去年8月,桑德告诉瑞士的法语日报《时报》:“当一个知识分子对警察、军队和国家力量大唱颂歌的时候,那么他与伏尔泰以来的法国历史就不再合拍。韦勒贝克指责政府在军国主义上做得不够充分。我们怎么能想象站在对立立场的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说当权者不够‘强悍’呢?看到统治今日辩论的知识分子如何反对移民、反对外国人、反对弱者,非常令人惊讶。这是一种新生事物。过去有过德吕蒙、巴雷斯、塞利纳和德里厄·拉罗谢勒,但他们不是支配性的。”
桑德说:“韦勒贝克过去确实写过有意思的东西,但他的新作〔《屈服》〕没有文学价值。现在美国已经没有大学的课程以他为研究对象了,就算在以色列也是如此。法国文化面临的真正威胁并非来自移民潮,而是来自媒体领域,以及它的全球化。”
他对《时报》说:“在我的书里,我强调说有不只一次德雷富斯事件,而是两次。在1898年左拉的《我控诉》之前,有三年时间,媒体被我们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统治着。有三年时间,从德吕蒙到巴雷斯,加上各类恐犹症的记者,几乎没有一个人为德雷富斯说话。所有人都是反德雷富斯者,让·饶勒斯(JeanJaurès)也包括在内。”
桑德说:“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不仅有恐犹症,还有法国南部的意大利人恐惧症。看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们能发现天主教徒恐惧症——许多波兰裔的矿工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对犹太人的憎恨仍然是最强烈的。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我们所说的‘穆斯林现象’。但我认为我们所说的大多数穆斯林并不是穆斯林。他们是伪穆斯林,因为他们失去了自己父母的阿拉伯或柏柏尔文化……整整一代年轻的穆斯林只有空洞的身份,正如某些自称犹太人的巴黎知识分子的身份也是空洞的身份一样。今天的伊斯兰恐惧症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我为此忧虑。伊斯兰恐惧症不仅是一种身份危机,它也是一种由经济衰退和社会问题引起的症状。”
罗伯特·扎列茨基认为,《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一书虽然火力十足,但偶尔忽略了法国伊斯兰恐惧症兴起背后的社会复杂性,尤其是萨拉菲主义的成长和吉勒·凯佩尔(GillesKepel)在新著《六边形国土上的恐怖:法国圣战源流》(Ter⁃reurdansl'Hexagone:genèsedudjihadfrançais)一书中所考察的“伊斯兰的激进化”问题。
在《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一书最后,什洛莫·桑德警告说,没有人,“无论是共和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甚至受迫害的少数群体及其后代,能够免于这种由拒绝和恐惧他人所形成的传染性的瘟疫。”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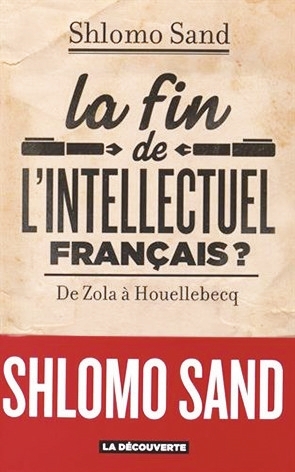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