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颖的影像札记在《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连载时曾追读过。文字看似闲适实则意味浓郁。结集成《貌相集》,不少篇什应该是重读了,却依然新鲜,宛如初识。看来再精编细作的报刊也多少耗散、折省了作者的思想与神韵。
秦颖曾任《随笔》主编,《貌相集》是他与文化界老作家名学者工作交往的副产品。品尝副产品后,伴随而来了犹疑:秦颖到底是职业出版人还是人像摄影家抑或随笔作家?该书到底该定性于“摄影记”还是类归为“随笔集”?现代人总是身份重叠难辨,《貌相集》的魅力就在于影像与札记融汇。
《貌相集》里被貌相的老人45位,我都有所了解,不少还有交往。读《貌相集》,熟悉的陌生人纷至沓来,会心的惊喜,蓦然回首的惊异总让我不由自主地掩卷沉思:老人不老,老人们总洋溢着思想的活力行动在秦颖的镜头里,雕塑般站立在《貌相集》里静观默望,似乎总有一种走出书页以参与社会引领社会的冲动。近年看图文书颇多,如此阅读体验则是第一次。这陌生化效果由何而来?因为我与秦颖熟识?因为我与书中人物相识或似曾相识?因为熟识的秦颖推送了一群相识而未必熟识的心灵。
人不可貌相乃常识,众人皆知,于有思想有成就的名人尤甚。秦颖偏偏把自己的文集取名《貌相集》,湖南人的那股霸蛮劲终于藏匿不住。身躯苗条得近乎弱不经风,说话轻声细语的秦颖或许早被不明真相的朋友排除出湘籍。长期从业于花城养成了他的外在自由与内心豪放,多年求学于上海且专攻历史学培养了他的细腻情感与精致作风,好好的一个湖南人就这样被“海风港雨”改造成以精神摄影为思想者造像的影像传媒人。
掌镜之前,细思漫想过;拍摄之中,思想激烈碰撞过。因而秦颖的“貌相”是他思想的产物,而不是镜头的产品,被摄者体态总比日常丰腴,精神饱满,神情自然而又将本真原型典型化;画面构成光影充沛、层次丰富、表现细腻,主体特征既鲜明突出,又与背景浑然一体,背景虚而不空,烘托有力。秦颖就这样在平角和凝视中洋溢着对智者人生的温情与敬意。平角拉近与造影对象的人际距离,凝视则求解、传达对象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典型特征。
影像的实然与应然乃人像摄影的两重境界,《貌相集》不止为一代智者的晚年留影,更为时代需要的思想者造像以唤醒时代激励后人。这是该书的文化价值所在。
我不知道以后的历史工作者如何认知评价秦颖为王元化、曾彦修等人的造像。那是秦颖的得意之作,得意者从历史走向未来之意也。于曾彦修那帧,我凝视良久,又良久端视。这是我见过的那个曾老吗?端着白底红字的大搪瓷缸侃侃而谈,红字乃“抓革命、促生产”,思想文物就因此成为曾老留存我脑际的标志记忆。曾老晚年沉浸在对过去岁月的沉思中。秦颖所造正是那个曾老,尤其是那眼镜背后眼眶里的泪珠。那盈盈泪珠就是为历史含而不流。于秦颖,有貌相在,不用明细说透,委婉地说一句“较真儿还带着些许天真”就够了。这个新湖南人,在历史的关键处不再秉笔直书了。文字难以珍藏历史的秘密,秦颖用影像而不是文字书写历史。不由赞叹《貌相集》的影像语言比文字语言更为犀利更为丰富。这不仅因为两者话语意涵、表达方式有别,更因为秦颖深谙图文传播之道而在人像摄影中更为自觉自为地摄人心魄,作为职业传媒人,他运用文字语言作为辅助手段解说人物造像时不由自主地遮掩留白。
《貌相集》副题“影像札记及其他”之“其他”是什么?如何“及”?由哪“及”哪,彼此何在?那种像外之像、意外之意就全交给读者了。不知“影像札记”是否已成型为一种文体,亦不知该文体的起始、传承、要素构成及发展态势如何?更不知它今后该如何从影像之“图”和札记之“文”互动互释中构建话语风格?秦颖影像札记的叙事风格是以影像犀利地“扎”在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变迁的痛处,记忆着思想与文化的遗存,以日常的老人“貌相”唤醒着国人。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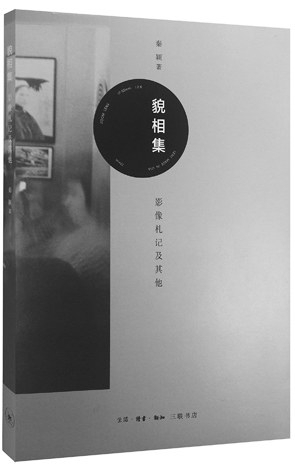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