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宋太祖的时代,很多割据的军阀都认为天命降临到了自己的头上,但是他们所理解的,显然只是天命的第一重含义。只有宋太祖“领悟”和“体贴”出了天命的第二重含义。
负土成坟
就在太祖收复湖南、湖北的同时,占据两广的南汉国,乘此乱局,想要大捞一把,派兵进入湖南南部,攻城略地,抢劫财物。当时李处耘和慕容延钊还在湖南北部清扫周氏残余,一时腾不出手来。太祖就委命山南西道节度使兼中书令潘美前往湖南,担任潭州防御使,负责湖南南部防御军务。潘美一到,便将南汉入侵军队打回了老窝,夺回了被南汉侵占的江华等县。
因为湖南地区一直处在战乱之中,生产荒废,民生艰难。太祖下令免征湖南地区一年茶税,其他税收一并减轻。太祖同时诏令:取消当年湖南潭州给朝廷和皇室已成惯例的土特产品供奉。
湖北江陵府也是一样,从本年开始,税额减到过去荆南国时的一半。湖南、湖北士兵,愿意回乡种田的,听任自便。地方政府负责帮助这些“复员转业军人”修缮房屋,提供必要农业生产用具。
太祖同时颁布命令:湖南、湖北地区,从今而后,使用统一度量衡标准,以免地方官吏利用不同标准克扣百姓钱粮。
在一个薄雾刚散的早朝上,太祖收到了一份老驸马张永德(周太祖郭威女婿)的奏章。奏章请求废除唐州(今河南唐河县)、邓州(今湖北邓州)旧时鄙陋的休妻习俗。
晚唐、五代时期,河南唐河和湖北邓州一带有个很不好的习俗,家中若是有人生病,尤其是已嫁女子,婆家人不仅不予求医治疗,还可以乘机将女子休遣回娘家,然后自己重新再娶。在张永德四岁的时候,张永德的母亲马氏,就因生病被休回了娘家。父亲又另娶了一位刘氏夫人。
要说人家张永德,那可真是个好人。父亲过世后,把生母又接回身边。修建两堂,分别给生母和继母居住,每天东西两院问安。因为自己母亲的不幸遭遇,想到天下母亲的艰难,于是上奏朝廷,请求以行政手段,坚决禁绝此种恶习。太祖感叹,挥手朱批:“准奏!”还在下面用力打了两道红杠杠。
批完张永德的奏章,太祖顺手又拿起下一份,是山东莱州掖县来的,要求更改县里的一个乡下村庄名字。这个乡原本叫做崇善乡,村庄的名字叫辑俗里。现在要改成义感乡、和顺里。理由是本村出了一个叫徐承珪的小官,从小没了父亲,全靠老娘把兄弟们拉扯长大成人。徐承珪做官外任,就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奉养。一年前,老娘过世,徐承珪又把母亲的灵柩运回乡里与父亲合葬,既没有使用公车,也没有动用公人。为了表达孝心,兄弟几个各自用身体背土,在家乡的村落旁边筑起了一座高大的坟丘。史书上叫做“负土成坟”。大约是几位兄弟的真诚孝心感动了上天,他家的庭院里出现了“瓜和蒂”“木连理”的奇特植物景观。莱州府觉得应当表彰提倡,于是就上了这样一份奏章。
太祖看得眼睛有些湿润,提起笔来写下“立即施行”四个大字。太祖被感动得忘了这是自己“准奏”或者“准”之后,中书门下省向下传达圣旨的公文字头。
太祖有感人间逆子忘记父母养育之恩,还下了一道特别的命令:全国各州郡长官,如发现民家父母生病,子女不为之寻医问药的,严惩不贷。
梁周翰的奏章
太祖稍得闲,偕同相关要臣一起,视察京城修建的“武成王庙”。
“武成王庙”的庙主,是佐助周武王定天下的太公望。原本姓吕氏,称吕望,也叫姜尚,据说其人字子牙,所以民间都叫姜子牙,或叫姜太公。因为佐助周朝文、武两王定国安邦的功绩,一直被后世崇尚。唐宋以前的各个朝代,都在京城为姜太公建造神庙,供奉这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唐肃宗李亨考虑安史之乱以后,国家需要杰出的武将和谋士来重新振兴,就追封姜子牙为“武成王”。唐肃宗还在京城里建造武成王庙,以汉代韩信、张良和战国时期秦将白起等历史上的七十二位武将和谋士,列在两旁配享。宋代开国之初,太祖一样需要安邦定国的人才,于是就委派朝臣在京城建造了这座武成王庙。朝臣奉旨行事,照搬唐肃宗时的情形,未做任何改变。
太祖走到白起的塑像旁边,举起手中的玉杖,指着白起的塑像,冷冷地说了一句:“白起杀降,不武之甚!”“这种人,是没有资格站在大宋朝的神庙里配享祭祀的。”太祖命人将白起的塑像撤出武成王庙,随后又将其他武将重新升降,诏令将齐相管仲的塑像树于庙里的堂中,添加魏西河太守吴起的塑像,放在庑下。经过太祖的调动,加之后世的修改,后来的“武成王庙”里,就只有六十四位配享者了。您可能要问:太祖一天日理万机,管这点儿小事干什么?
这种事情说小,其实也不小。历史中曾经的各色人物,在“本朝”受尊重还是遭唾弃,实际上表明的是当下政权的价值取向。而任何一个政权的取向,不仅表现了当下政权的性质和品格,也预示了这个“值日”政权的前景和未来。
太祖的这个举动,引起个别朝臣的非议。秘书郎兼史馆编修梁周翰上奏称:“臣闻天地以来,覆载之内,圣贤交骛,古今同流,校其末年,鲜克具美。”他说:从有天地以来,地球上面就慢慢有了圣贤,但是到了后来,很少能有没有毛病的纯粹完美之人。梁周翰还说:像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都曾经遭人非议,后世对他们也有不同看法。何况武将?他又接着说:“比如说诸葛亮、张飞、关羽等,哪个身上没有毛病?如果非要因为他们身上的一点毛病,就倍加指责,谁人背后不被别人说三道四?如果有点毛病,就从庙里撤出,那恐怕非撤光了不可?”他又说:“伏见陛下方励军戎,缔创武祠,盖所以劝激武将,资假阴助。”除去白起等人,会使两廊空无,“似非允当,臣且惑焉。”“今之可以议古,恐来者亦能非今。”这话的意思是:刚建武成王庙,就急切地把白起等人去掉,弄得两廊空空,好像有些不妥。这种做法,使“微臣”感到有些迷惑不解。假使我们今天可以随意评判古人,那么恐怕将来的人们也会说我们的不是。
梁周翰在奏章的最后说:“愿纳臣微忠,特追明敕。……”希望太祖接受他忠诚的建议,赶紧收回废除白起等配享武成王庙的圣明的敕令。既是圣明的敕令,干嘛还要追回?其实您不要太在意这个小问题,这是臣子们跟皇帝讲话的技巧,总不能说“请赶紧收回你错误的命令”吧?
梁周翰写了一大篇漂亮的骈体长文,自以为得意,太祖却未予理睬。他根本就不了解太祖的真实用意,这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太祖废除秦将白起配享姜太公庙的资格,撤了死人的官爵,不是在白起身上吹毛求疵。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在长平之战中,把已经投降的赵国兵将四十万人,全部活埋。手段之残忍,用心之毒辣,几乎毫无人性可言,创下了没有吉尼斯纪录时代的世界残杀之最。
太祖撤的是白起,张扬的是仁爱的政治理念。而正当大宋朝行进在统一祖国途程中的关键时刻,军事行动一定不会很少。太祖爷这样的做法,对于大宋朝的全体官兵来说,不啻为一个提前警告:“杀人的不要,仁爱地统一!”人性中原本都有极其残忍的一面,杀人的戒律一开,嗜杀就会成为习性,天下的生灵,都会成为案板上的鱼肉。太祖撤掉白起的配享资格,就等于宣布了一条戒律:本朝(本届统治者)非但不提倡杀人,而且以杀戮为罪孽!
太祖视察武成王庙,撤掉白起配享资格的小小举动,实在有着超乎寻常的人道主义意义。梁周翰以为这是在古人身上挑刺,其实是不了解太祖仁德的用心。但是梁周翰的奏章却有另外的意义,满朝没有不同的声音,那就不是一个像样的朝廷。
人命关天
太祖正在视察武成王庙,江州奏报:防御使马全义过世了。太祖很喜爱这位将领,既能打仗,又善于体贴兵将辛苦。马全义生病期间,太祖不断派人问候,希望他好生养病,病愈之后,准备授予他江州节度使。不想马全义终于不治,太祖伤心落泪,追赠马全义为镇国军节度使。
马全义的事情刚了,陕西又有奏报送上:凤翔节度使王景病故。
太祖派礼官前往致祭,同时委命枢密学士高防出任凤翔府知府,顺势将文官担任州郡长官的措施,进一步向全国各地推展。
高防是个很优秀的官吏,在不同州县为官,都给百姓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太祖本想让他把陕西的地方风气改变一下,可惜高防刚刚上任又病死了,太祖伤心,下诏抚慰家属。
湖南来报:战乱之后,常德等地闹起了瘟疫。太祖下令免费发放药物,务必送到千家万户,不能遗漏。地方官吏立刻行动起来,四处分发药物,有效地阻止了疫情的进一步发展。
湖南虽然没有发错药物,太祖家里却因用错药物出了人命。
太祖皇后王氏生病,医官王守愚用药不慎,皇后病情急剧恶化,没撑持几天就一命归西了,年仅二十二岁。王皇后是太祖于后周祖显德五年(958)所娶,当时十六岁。依本书作者推测,评书《杨家将》里面的那位八贤王赵德芳,大约就是王皇后所生,不过没有绝对可信的文献说明。《宋史·后妃传》只说王皇后生有三个子女,都早夭了。
朝臣们闻听此事,义愤填膺,异口同声地要求杀掉王守愚!
这种事情无论出在中国历史上的哪个王朝,或者哪个时代,只要还是家天下政治,王守愚就是上天入地折腾八个来回,求菩萨告阎王,都不会发生任何效用。一句话,“死有余辜”!太祖既难受,又气恼,但考虑王守愚只是失误,并不是故意谋杀,同时也不是一贯玩忽职守,这次只是一时疏忽……诏旨:免死,流放海南岛。
在传统的社会里,没有比这样的医疗事故更严重的了!王守愚早已不怀生的企望,每天只是一个心思:等死。忽然听说免死流放,几乎傻了。他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用力扒拉了好几下,确信听到的是免死的消息。
“苍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快走吧,郎中,以后给人家瞧病,尽心点儿,好生留神!王守愚仿佛听到太祖在身后的声音,就一路高呼吾皇万岁,一路泪流满面地向海南岛赶去。
家里的事情还没处理完,外面又出事了:
山东登州府上奏:高丽国王遣使前来上贡,乘船从海道前来,赶上大风浪,船翻了,船上近一百人全部淹死,只剩下一个使臣叫时赞。太祖赶紧下诏抚慰,指示登州府,负责死难者安葬和善后事情处理,同时派遣使臣,给高丽国国王送去慰问诏书。这位高丽国的国王,名叫王昭,给太祖送去了价值两亿元的礼品,连同一百位送礼兵民,全都海祭给龙王爷了。不过这次可不像不久前韩国的翻船事故,不是船长玩忽职守,而是台风的猖狂肆虐。那时候没有天气预报,海上航行的危险性随时存在。
海上死人的事情还没处理完,陆上又死人了。
安陵隧道塌陷,二百多施工人员和守护兵丁,都被压死在隧洞里。
太祖的父亲赵弘殷,当年与太祖一道,跟随周世宗攻打南唐国,归来路上生病过世,葬在汴京东南数十里外。后来太祖称帝,追封老爹为宣祖,将当年葬地建造成安陵。乾德元年(963)十二月,太祖听信堪舆先生的话语,准备改葬到西京洛阳下辖的巩县西南四十里处的邓封乡南訾村,由礼官先去卜地。之后,任命宰相范质负责督办,开始全面施工。皇家讲究,风水先生说,棺木转移要先走一段地下通道,不能直接在露天地上挪移棺材。移陵之前,先挖了一条修长的隧道,山体滑坡,隧道坍塌了
……
嘿!这到底是什么兆头,是好是坏?太祖已经无心先想这些,赶紧打发人前去处理事情,抢救生者,埋葬死者,优抚死难者家属。
改换年号
太祖要改年号了,要求不能跟历史上的任何朝代重复。这还不容易,起个怪怪的,像今天的家长给孩子取名字一样。那可不成。不能求怪,不能求繁,还得求“硬”,还得求精。
太祖还没请,赵普自己就先来献策了:“叫乾德。”这位曾经的村学究,现在是枢密使——大宋朝的国防委员会主席。
乾德是什么意思,就是乾龙之德,就是《周易·乾卦》中的龙德。赵普说:咱们这几年蒸蒸日上,皇上把天下治理得顺畅和谐,大宋朝正如中天的太阳,光照寰宇,正好与《乾卦》的九五爻“飞龙在天”的意思相合。
太祖问赵普:“有没有别的什么朝代或者皇帝叫过这样的年号?”赵普不容置疑地回答说:“绝对没有”,“他们也不配叫这个年号!”赵普接着说。太祖听了很高兴:“好,就叫这个年号。”
公元963年12月4日,按照中国的农历纪年,是宋太祖建隆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甲子。这一天,大宋朝国都汴京城的南郊彩旗飘飘,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太祖皇帝昂然庄重缓步拾阶,走上高大的祭坛。
祭拜天地之后,宰相范质宣布改元乾德,同时宣布诏令:大赦天下。因犯重罪而被处斩的,还有未及处斩自己死在死囚牢里的重犯,允许家属运回家乡埋葬。这些罪犯从前所侵吞的、当时仍在追缴的公物,一律免除,不再由家属承担。同时将建隆开国以来为国事而死难者的嫡长子孙,录一人公干。就是给这些“烈士”们的遗属安排工作的意思。
公元963年这一年,既是宋太祖的建隆四年,又是宋太祖的乾德元年。您要是看到史书或者书写历史的书籍,把这一年叫做建隆四年,或者叫做乾德元年,那都没错。但实际的情况应该是,十一月十六日之前叫建隆四年,之后才改叫乾德元年。建隆四年十个半月,乾德元年只有一个半月。不过为了纪年方便,很多史书多半将这一年叫做“乾德元年”,咱们大宋朝杰出的历史学家李焘,在写作《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时候,就选取了这样的纪年方式。
陶谷诬人
李昉被太祖从湖南衡阳召回,回朝担任给事中。翰林学士陶谷,从前与李昉有过节,总想伺机报复。刚好今年李昉跟吏部尚书张昭一道,负责本年官员考核任免。陶谷想从李昉身上直接找瑕疵,以便加以陷害。但是一时间没找到,就想从李昉的身边人下手。听说左谏议大夫崔颂,跟李昉关系密切。于是就上言诬陷,称崔颂把自己的亲戚托付给李昉,让李昉帮忙搞个东畿令干干。东畿令是个什么官?大约就相当于今天北京市东城区区长之类的官职。当然,北京市有很多区,而大宋朝的都城,只有东西南北畿,而且没有区委书记一职。
诬告了别人,又怕皇上不信,就把张昭扯上,说是张昭最了解这件事情的原委。
陶谷大约是想着:一旦皇上发问,张昭不敢说自己不知道,如果他说不知道,也得跟着一起吃瓜落。
这就等于把张昭也给告了,因为如果张昭真是知情不举,就等于欺君!这可不是个小罪名。张昭毫不知情,街坊间有关这件事的传言,很可能也是陶谷派人故意散布的。
太祖把张昭找去询问,张昭顿时火冒三丈,忘记了在皇帝面前的礼数,把帽子摘下来,大声对太祖说:“陶谷罔上!”
什么意思,说陶谷撒谎,欺骗皇上。太祖很生气,又找其他可能的相关人员询问,都说不知道。
半月以后,宰相府上奏称:陶谷引张昭为证,张昭拒绝承认。说张昭在朝堂之上,肆意喧闹,惊扰了圣躬,有失大臣之礼。“事涉李昉、崔颂等,宜行责遣,以儆效尤。”有诏:李昉,责授彰武行军司马;崔颂,责授保大行军司马。
张昭见陶谷得逞,心里咽不下这口恶气。同时责罚了李昉和崔颂,就等于陶谷说的是事实。而自己当着皇帝的面奏称“陶谷罔上”,自然也应当受到责罚。皇上虽然没有直接责罚自己,可是自己又有什么颜面这样低三下四地干下去?于是就连续三次上章,请求退休。太祖准奏,张昭就这样,以吏部尚书(《宋史》本传称“以本官致仕”,就是在原来的官位上退休的意思)身份退休了。
朝臣在皇帝面前甩掉帽子、大声喧嚷,虽然“查无实据”,但肯定“事出有因”。为了维护朝廷尊严,必须对“违礼”大臣进行责罚,要不然朝廷就没了规矩、没了尊严。
陶谷呢?诬陷完别人,自己就没事了吗?暂时没有证据证明诬陷他人事实,留任翰林学士承旨。陶谷这次虽然没有明确被责罚,但太祖在心理上一直看不起陶谷。
当年陈桥兵变,太祖回师东京,禅位仪式上缺少禅位诏书,陶谷顺手从长袖中取出说:“已经写好了。”
陶谷当年的那份禅位诏书,根本没人指使,而是听到传言,说是太祖兵变了,赶紧回去撰写,因为手快,禅位之前就写好带在身上了。他的做法,显然已经表明,其人是个行险侥幸的功利之徒。
不过陶谷还是不了解宋太祖,太祖爷不喜欢阿谀权势、攀附新贵,出卖旧主,同时也出卖自己尊严的人。从那天他拿出那份诏书开始,太祖就不愿再正眼看他。太没有操守,也太会见风使舵了。真让人瞧不起了,太祖心里早就对他蔑视透顶了。但是陶谷确实博学多才,国家刚刚建立,缺少这种人是不行的。不懂行的上来,一定会乱搞一阵。这是治理国家,不是任气使性子。所以,太祖也只能忍耐着,依旧使用这个人。
张昭,原名张昭远,五代老吏。从后唐开始为官,历经后晋、后汉、后周,一直充任朝廷要职。后汉时为了躲避刘知远的名讳,把远字去掉不叫了,只称张昭。宋初一直担任吏部尚书,官职和权力都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官员任免、升黜、考核、督查之类。张昭为官,尽职尽责,撤出白起配享武成王庙的资格,以及其他武将、谋臣的升黜,都是太祖委命张昭召集大臣们讨论商量之后,才最后决定下来的。
张昭还将晚唐、五代以来的选官制度、考核制度等整理分类,为大宋朝的官员选拔、官员政绩考核评估、官员升等黜降、奖励责罚等规矩的确立,提供了有效的参照。为宋朝官制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那就这么让张昭退休就完事了?那不是宋太祖的风格,太祖是古今帝王中绝少有的讲情谊的人。太祖让张昭退休,一方面也是张昭年纪大了,当时张昭已经七十一岁。太祖封张昭为“陈国公”,张昭七十九岁过世。过世前,太祖有重要事宜,还派遣身边近臣亲自到张昭家里询问。张昭跟范质、王溥、魏仁浦等官员退休之后,都成了大宋朝的“顾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张昭临终前告诫两个儿子:“我在好几个朝廷中都做过官,我死以后,不要向朝廷为我请谥,这样会加重我的罪孽。”
“请谥”是什么?就是跟皇帝要一个“谥号”。世称范仲淹为“范文正公”、胡安国为“胡文定公”、朱熹为“朱文公”、周敦颐为“周元公”之类,这里面的“文正”“文定”“文”“元”字样,都是谥号。谥号是用来表彰大臣们的内在人品和行为风格的,谥号都是大臣们过世以后,由子女或者朝廷中的其他大臣提议,礼部审核、讨论之后,交给皇帝审批。得到皇帝认可之后,再由朝廷下发“红头文件”确认,请谥的过程就完成了。
张昭不让儿子为自己请谥,说是自己在好几个朝廷中任过职,伺候过不同的主子,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张昭离任退休才几个月,老宰相范质又过世了。
范质生病期间,太祖不断亲自探望,甚至亲自调药。
范质临终之前,也说了后来张昭过世前类似的话语,告诫儿子范旻,不要为自己请谥,不要立墓碑之类。说自己在几个朝廷中都任过职,这件事张扬出去并不光彩。
五代时期的宰辅们,多半都毫不吝惜地收受地方节度使的供奉,家资巨富。范质从周世宗时开始任宰相,入宋以后还一直担任宰相,家无余产,家庭用具简单,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都很俭朴。据称五代以来,宰相不贪,宰相家庭不富,是从范质开始的。
后来在一次朝臣聚会的时候,太祖想起范质,还感慨地说:“朕闻范质居第之外,不置资产,真宰相也!”说他家里家外,没有多余的资产,什么多少亩田宅,多少间房,跟人家范质一点关系都没有。真正是个好宰相啊!
太祖闻听范质噩讯,痛惜不已,赠范质中书令,赐绢五百匹,粟、麦各一千石。
孟老夫子说过:“耻之于人大矣。”人生是否有节操,很多时候都得从是否有羞耻心上看。在风气醇厚的社会里,大家都害羞怕耻;而在风气混沌不堪的氛围中,人们的羞耻之心也就荡然无存了。五代时期社会风气的混沌不堪,通过五代时期文武官员和社会大众的无耻心态和无耻言行中,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而从大宋朝建立以来,那些在五代的大染缸里,浸泡得比泡菜还彻底的官员,开始讲究廉耻,开始顾及自己的声誉和影响了。这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伟大变化!为什么会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会发生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
太祖的做法和取向是最重要的导引风向标。太祖怀仁爱,行正道;孝亲敬长,善待友朋;不提倡贪功冒进,不喜欢阿谀逢迎;不急切于事功成就,不怠惰于日常事务;慎思明辨,沉稳持重;开朗直率,诚信待人;不吝赐人而自奉俭约。太祖的做法,首先感染了周围的大臣,进而又通过身边的大臣,影响到周围更广大的人群。大宋朝开国不久,社会的风气,就已经悄然不觉地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风俗的改变,首先靠的是在上位者的表率。太祖虽然原本读书不多,但是他的一身正气和两袖清风,务实肯干而不急功近利,在大宋朝刚刚建立之初,就为身边的大臣们做出了楷模性的示范,并通过身边大臣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普通大众之中去了。正像南宋时期的大儒胡五峰先生所说的那样:要想彻底改变世间的不良风俗,首先得彻底改变君主的心术。
从宋太祖的执政风格和宋初社会风气的骤然好转,我们可以深深地相信,胡五峰先生的话真正是改造社会风俗的金玉良言。
因为范质和张昭们对大宋朝的贡献,他们过世以后,家庭和儿孙们都受到了太祖相应的关照。
大宋朝的新生政权刚刚有点规模和样子,朝廷里却闹翻了天,国内外什么事情也都出来了。太祖心里想着:“这当皇帝,确实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本文摘自《大宋真天子:一代仁君赵匡胤》,江南提学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第一版,定价:58.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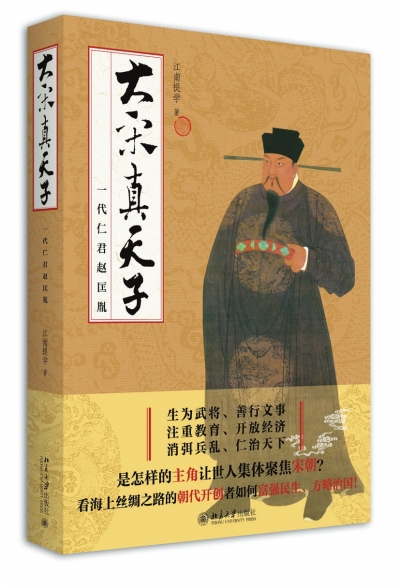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