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4日,因领导发动“英属印度”联合省农业区的抗税运动,国大党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889-1964,印度开国总理)被殖民地政府判处两年“严厉监禁”。自1921年至1945年,尼赫鲁先后9次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而身陷囹圄,此系第6次。同日,圣雄甘地也遭当局逮捕,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团体,全印度进入戒严状态,第二次全国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渐入低潮。在狱中,尼赫鲁埋头阅读和写作,并以书信的形式为自己15岁的女儿英迪拉(1917-1984,曾两度担任印度总理)写了一部《世界历史之一瞥》(Glimps⁃esofWorldHistory,中文版《爸爸尼赫鲁写给我的世界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通读之下,这部近百万字的“世界历史家书”绝非古往今来的故事汇,更不是世界上下五千年的流水账,而是一部饱含着父爱的启蒙之作、反思民族独立运动的发愤之作,以及关怀人类前途命运的忧患之作。
遭逢反殖民斗争受挫、法西斯势力登台的艰难时世,尼赫鲁的历史书写带有强烈的现实意识和时代色彩。通过全面考察从原始社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历史进程,尼赫鲁试图贯通东西方文明的“古今之变”,解开人类历史的“斯芬克斯之谜”:东方文明为何腐败衰亡?何以浴火重生?西方文明何以蓬勃兴起?为何又走向失控与疯狂?人类将何去何从?
这些大问题的解答,取决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充分把握,对时代矛盾的深刻洞察,以及对人类理性和良知的坚定信念。归根结底,取决于一种学究天人、道贯古今的博学,一种慈悲为怀、仁爱及物的博爱。
一
这种博学首先体现在对孤芳自赏的历史观的摒弃。尼赫鲁一开始就告诉女儿,写这些信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落入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陷阱:“相比其他国家的历史而言,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国家的历史远比其他国家的历史更加辉煌灿烂,更值得去研究和学习。”熟悉和热爱自己国族的历史本是人之常情,但因此轻视其他国家的历史却是不可取的。孤芳自赏很容易变成唯我独尊。在尼赫鲁所处的年代,陷入这一思维陷阱的并非印度,而是满世界大行殖民主义的西方列强。尼赫鲁擅于以古鉴今,在讲述罗马历史时,笔锋一转,戳穿了大英帝国骄傲的假面:“罗马帝国被认为是统治着全世界的伟大帝国。然而,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帝国或国家能够统治整个世界。……大英帝国经常被拿来与罗马帝国相比较——英国人通常这么做,由此得到极大的满足感。所有的帝国差不多都是相似的。他们都是通过剥削他人来发展自己。然而,罗马人和英国人之间有一个极为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他们都非常缺乏想象力!他们都自以为是、沾沾自喜,认为全世界都是以他们的利益而存在的,他们的一生都不会遇到任何不确定因素或困难。”读到这里,不禁联想到如今的“新罗马帝国”——美国继承了这种不可一世的优越感,以一种“缺乏想象力”的道德自负逞其霸权,成为这个地球上的麻烦制造者。然而,当年的“日不落帝国”今何在?
“缺乏想象力”是博学的反面,是无知的名片。我们对于这种孤芳自赏的历史文化心态也不陌生。曾几何时,无论是“天朝上国”的迷梦,还是“风景这边独好”的幻觉,带给我们的只是灾难。而这种泡沫心态一旦破灭,又很容易滑向文化自卑的泥淖。自我欣赏导致自我迷失,这种吊诡的身份认同危机,也是我们并不久远的记忆。
只有跳出孤芳自赏的怪圈,才能开眼看世界,从文明交流的角度认识自己。从古代世界开始,尼赫鲁就注重考察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与互相影响,尤其关注宗教这一古代世界精神内核的发展演变。贵霜帝国就是尼赫鲁考察的典型案例。贵霜帝国是一个佛教国家,鼎盛于约公元前100年至公元200年,相当于罗马共和国末期和帝国初期,西邻罗马、东接中国的汉朝、南连印度,处于文化交流的枢纽位置。贵霜人将佛教传播到了中国和蒙古,同时也受到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宗教上呈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特点。在印度婆罗门教和希腊文化的影响下,贵霜帝国的佛教分裂为大乘和小乘两大派系;经过持续了数百年的辩论和竞争,大乘佛教占据了北印度,小乘佛教占据了南印度,最终都为印度教所吸收同化;经过一番移植嫁接,如今大乘佛教盛行于中国和日本,而小乘佛教则盛行于斯里兰卡和缅甸。
对于基督教的传播,尼赫鲁也提到一个重要的史实:基督教传入印度远早于传入欧洲:“在耶稣死后的百年里,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漂洋过海来到了南印度。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并得到了传播他们的宗教信仰的许可,这与他们在罗马的境遇完全不同。”在中国唐朝,统治者对于佛教、景教(基督教一支)和伊斯兰教也都一视同仁。佛教自不必说,景教和伊斯兰教也都在中国建立了修道院或清真寺。西方直到启蒙运动时期才倡导的宗教宽容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出现在东方,后者包容开放的文化心态与同时期欧洲的狭隘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此,尼赫鲁又将目光转回现代,痛陈现代所谓“耶稣的追随者”实为帝国主义的马前卒,相形之下,“圣雄甘地的思想与耶稣教义反而更为接近”。
二
博学不同于驳杂,必贯之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身为宗教国度印度之子,尼赫鲁的思想却鲜有宗教色彩。在其另一部狱中完成的著作《印度的发现》中,尼赫鲁写道:“我所关心的根本是现实和今生,并非什么别的世界或来生。是否有像灵魂这样的东西,或是否死后还有生存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些问题虽关重要,丝毫未使我有一点烦心。……但是,作为一个宗教信仰,我不相信任何这些或其他的理论和假想。”在给女儿的信中,他也强调自己“非常偏爱一切科学和科学的方法”。可见,尼赫鲁的博学是人间的、经验主义的,既没有独断的先验色彩,也没有宗教的启示录意味。这种博学与其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现实体验结合起来,赋予他强大的历史理解力,如同一双历史的千里眼,以全球视野洞察东西方文明的循环消长。
公元1000年后,希腊的光荣与罗马的伟大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但仍有两颗明星点缀着欧洲中世纪的午夜。在西端,处于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走向全面繁荣,独占欧罗巴鳌头;最东端位于欧亚交界处的君士坦丁堡,仍是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发挥着文化交流的桥头堡作用。与此同时,亚洲的中国和印度正处于中古时代的鼎盛期。在东西方文明昼夜悬殊的表象之下,尼赫鲁看到了古老的东方文明的衰退:“精美的艺术在蓬勃发展,奢侈享受变得越来越精致;与此同时,文明的脉搏却在减弱,生命的气息似乎也越来越微弱。”这正是文明衰退的标志,“因为生机与活力的标志是创新,而不是重复和模仿”。而半文明半野蛮的西欧国家,却开始在罗马的废墟上搭建新的文明。对于欧洲的复兴,尼赫鲁与后来的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见略同。后者在《全球通史》中分析,由于西方古典文明比其他文明遭受了更彻底的破坏,无法复原,才可能被一种崭新的东西所代替,使西方超过了东方。
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世界又表现出“西落东升”的迹象。“欧洲具有了一种愉快、繁荣的面貌。这种令人愉悦的文化和文明,至少在表面上看,似乎会永恒、进步,从胜利走向胜利。但是,如果你透过表面,向下窥视一眼,就会看到奇怪的骚动和许多令人不快的景象,因为这种繁荣的文化主要只是属于欧洲的上层阶级的,而且它是以对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剥削为基础的。你将看到我说过的一些矛盾、民族仇恨和帝国主义狰狞残酷的面目。……虽然有人在大肆谈论健康和进步的问题,但是衰退正在吞噬着资产阶级文明的重要器官。崩溃在1914年发生了。”与此同时,长期积弱的亚洲再现生机,尼赫鲁断言:“毋庸置疑,亚洲再次崛起了。”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辩证地看,西方虽然开始衰落,但她所开启的现代革命却蔓延到全世界,激活了包括亚洲在内的其他文明。
三
对于文明或国家的兴衰隆替,希罗多德总结为三个阶段:胜利、由胜利导致的自大和不正义、由自大和不正义导致的衰落;中国则有贞下起元、“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佛家有“成、住、坏、空”之论;现代历史哲学也各有各的解释。但这些说法往往都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对原因的分析或规律的揭示。布罗代尔曾把原因归结为理性主义的系列效应(当然既包括其成功也包括其失败)。
尼赫鲁并没有推演出一套历史哲学来回答上述问题,这已超出了“人间的博学”的范畴。但他用另一种方式去回应它,那就是“人间的博爱”。这里的“博爱”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理解:一是从李泽厚先生“情本体”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归于历史之本体;二是从狄尔泰生命哲学注重“体验”(Erlebnis)和“理解”(Verstehen)的角度来理解,归于对历史的认识;三是从陈寅恪先生“了解之同情”角度来理解,归于治史之方法。一句话,历史不是通过推理来解释(interpret)的,而是通过“博爱的同情”来理解(comprehend)的。以西方理性主义的解释范式来研究历史,无疑是一种普适性僭越。如果说博学意味着科学的精神和方法,那么博爱就意味着对人类共同情感的把握,二者构成了尼赫鲁思想的两个面相,统一于健全的“历史意识”之中。正如尼赫鲁对女儿反复叮咛的:“如果你想了解过去,你就必须带着同情和理解来看待过去。要了解一位历史人物,你就得深入地理解它所处的环境,即他的生活状况以及他的思想。那种用现在的情况和思想来判断历史人物的做法是十分荒谬的。”
然而,在殖民主义的压迫和法西斯主义的威胁面前,这种博学和博爱是无力的。或许正是因此之故,尼赫鲁对马克思主义表达了高度的同情,并结合时代形势,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简要而生动的述评。尼赫鲁提醒女儿:“印度处于英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我们用尽全力与英帝国主义作斗争。但是我们不应该责备那些身处印度的、支持这个制度的英国人。他们只是一台大型机器中一个个不起眼的齿轮,他们无力改变整个机器的运转。”这一认识同马克思的分析是一致的。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两篇文章中,马克思指出,不管英国在印度犯下多大罪行,她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以完成其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但尼赫鲁承认自己“越来越倾向共产主义的理论”,它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时代的社会现象,指出行动和规避的方法”(《尼赫鲁自传》p674)。十九世纪以来的历史占了全书三分之二篇幅,阅读这段历史,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尼赫鲁的影响。
总的来看,尼赫鲁思想的两个面向各有其源头。其博学的一面来源于西方(特别是19世纪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尼赫鲁自传》p673),而博爱的一面则来源于印度的非暴力精神——佛教与慈悲哲学(参《走向人道世纪——谈甘地与印度哲学》),二者构成了一种体用关系:博爱为体、博学为用,不妨用“东西贯通的人文主义”名之。在这位印度独立和复兴运动的领袖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人文主义的巨大能量。尼赫鲁东西贯通的人文主义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也有隔代知音,那就是以《东方学》奠定后殖民论述的萨义德(E.W.Said),另一位博学的知识分子。后者在演讲《人文主义的范围》中指出:“人文主义的本质,就是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不断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实现的过程,这不仅对于我们,作为白种人、男人、欧洲人、美国人,而且是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也就是根本什么都没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别的传统,有别的文化,有别的精神特征。”
作为一位关爱女儿精神成长的父亲,尼赫鲁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去传达自己对真善美的追求、对正义的信仰,以及对自由的礼赞。书中从容引用了东西方大量诗歌,为这部历史作品增添了诗意。这种优雅的博学于我们久违了。
时过境未迁,尼赫鲁所批判的孤芳自赏心态在今天依然存在,甚至演变为盲目和狂热。在“印度三部曲”中,奈保尔写道:“在社会领域,年轻人缺少历史分析的训练,在激进思想影响下猛冲猛打,他们对解决方式的了解多于对问题本身的了解,多于对自己国家的了解。”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与方法相背离、“体用两层皮”的现象,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博学与博爱的缺席。今天,阅读这部写于殖民主义时代的世界史,对于后殖民和全球化时代认同政治和多元文化的建构,能起到某种正本清源的作用,有助于我们认清自身的境遇以及这种境遇之由来,获得一种健康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而不至于沦为奈保尔笔下后殖民主义的堂吉诃德。毕竟,对历史的无知是最大的无知。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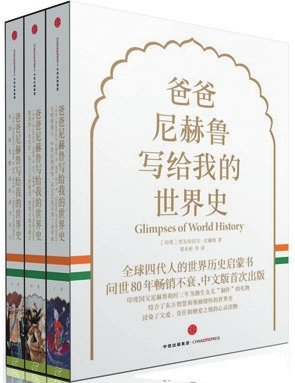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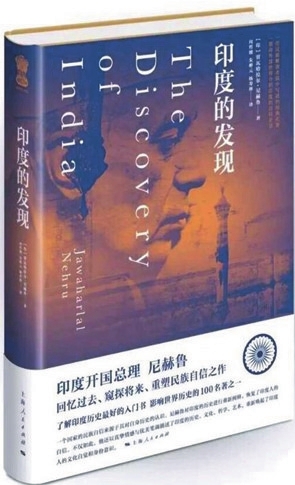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