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时乐府工作人员采诗不仅包括黄河、长江两流域的广大地区,还很注意吸收北方少数民族的乐调,可考者有鼓吹曲和横吹曲,鼓吹曲配器用箫、笳,横吹曲用鼓、角。歌辞现存者仅有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其中有些大约是翻译成汉语的少数民族的民歌;有些可能是汉族文人的依声填词之作。据说李延年曾经“用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古今注·音乐》),可惜到魏晋时代已经失传,这“二十八解”是只有曲调还是兼有歌辞已不得而知。汉朝人乐于吸收少数民族音乐,表现了一种开放的胸襟。
“乐府”是汉代的一种官署,上属“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的少府(《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是一个典型的御用部门。乐府之负责人为少府辖下的十六令丞之一。这个机关的任务是采集民歌,整理配乐,同时也为某些文人的作品配乐,形成艺术歌曲,以供皇室享用。经过他们加工的诗,称为“歌诗”,亦通称乐府诗,又往往简称为乐府。
西汉时代还有一个管理音乐文学的机关,称为“太乐”,太乐令隶属于“掌宗庙礼仪”的太常。郊庙之乐是正规祭祀时演唱给神灵和祖先听的,带有很强的礼仪性,所以一定要严肃、高雅;而少府所属的乐府是为当今皇上服务的,由这里提供的作品不妨以至必须带有更多的娱乐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汉代前期统治者的心态,他们对古老的音乐虽然相当尊重,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兴趣,他们欣赏的是流行的近俗的东西。这种分别用两手抓的态度,对中国音乐和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
一
乐府过去一般认为是汉武帝搞起来的,其实它的组织体制可以上溯到秦朝。1977年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秦代错金甬钟,钟柄上有“乐府”二字,少府原是秦官,见于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杜佑《通典·职官》亦称秦汉少府属官“并有乐府令、丞”。
汉代乐府的工作方式与汉高祖刘邦的关系很大。刘邦出身于社会下层,对于民间的歌舞十分欣赏,《晋书·乐志》说:“汉高祖自蜀汉将定三秦,阆中范因率賨人(今湖南、重庆、四川一带的古少数民族)以从帝,为前锋。及定秦中,封因为阆中侯,复賨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后使乐人习之。阆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组织专业的音乐人才来学习民间的特别是少数民族民间的歌舞曲,而不管其原来的歌辞如何,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头。此后乐府的工作,始终与吸收少数民族的音乐歌舞结不解之缘。
汉王朝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政权以后,刘邦在文学艺术方面抓了几个方面的事情,一是让叔孙通等人依秦乐改编和创作了《宗庙乐》《昭容乐》《礼容乐》,这些庙堂音乐属于所谓雅乐,尽管汉初的这种雅乐其实并不怎么古老,但到底也是有传统依据的东西,可以借以表明新建的政权具有合于法统的权威性。二是让唐山夫人用楚声写了《房中祠乐》,此举表明汉代音乐文化与楚地深刻的联系;三是在舞蹈方面新创一种,改编两种:“《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汉书·礼乐志》)既继承传统,又有所创新,用艺术形式肯定并歌颂新兴的大汉王朝。
至于更古老的雅乐,这时已经失传了。汉初有一位乐家制氏,曾捧出秦以前的“雅声”来,但连他自己也已经“但能纪其铿鎗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汉书·礼乐志》),未被采用。事实上中国的“雅乐”以及其他被认为是雅的东西,往往仅因其历史相当悠久,它本身原来很可能其实也是俗的东西,但资格一老,就成为雅的了。
刘邦还亲自组织了汉王朝最早的音乐歌舞班子,这恐怕就是后来“乐府”的雏形。《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诸儿皆和习之。”这场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型演唱由刘邦一人主唱,众人和之,用打击乐安排节奏,这正是南方民间演唱歌曲的最常见形式。宋玉《对楚王问》有云:“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百人。”在这里“客”是主唱,国中有多少不等的人属而和之。后来乐府中的所谓“相和歌”也正是这么一个唱法,只不过属而和之者是有组织的,并且以器乐来伴奏。
上述一百二十人的唱诗班本来是一个临时性的班子,到惠帝时变成了固定的班子,《高祖本纪》继续写道:“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后有缺,辄补之。”这样就有了固定的编制。汉代的“乐府”正是在这一编制的基础上形成的,《史记·乐书》说:“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以增加,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这里提到“乐府”,可知在惠帝时已经很明确地有这么一个机构了。由于当时“大汉初定,日不暇接”(班固《两都赋·序》),早期乐府做的事情不是太多,主要只有以下几件:惠帝时为《房中祠乐》配上了器乐,更名为《安世乐》;文帝时新创了《四时舞》,“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汉书·礼乐志》),为政治上的稳定服务;景帝时对《武德舞》作了若干加工修改。
二
到汉武帝刘彻(前157年~前87年)时,国力强盛,内政外交都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元狩三年(前120年)扩建乐府,为了“观风俗,知厚薄”(《汉书·艺文志》),指定乐府派员到民间采诗,这是乐府建立以来的一大变化,因为这样一来,宫廷的音乐生活就不仅具有政治意义,也不仅仅与高祖刘邦之故乡沛这一个地方有联系,而是大大加强了与各地民间音乐文学的联系。此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汉书·礼乐志》说,武帝时“乃立乐府,采诗夜(绎)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一手抓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和加工,一手抓文人创作,都取得长足的进展。武帝十分重视乐府的一大原因是为了筹划郊祀大典,为此准备音乐方面的素材,但客观上却使民间的东西包括音乐方面和文学方面的元素大举进入了宫廷,产生了出乎预料的重大影响。
这时候乐府已大大超过一百二十人,而且变得越来越庞大,这一点可以从后来的若干举措中看得很清楚。《汉书·宣帝纪》载本始四年(前70年)的诏书说:“今岁不登,其令乐府减乐人,使归将农业。”乐府成为精简机构的重点,其庞大可知。据《汉书·礼乐志》的记载,到哀帝解散乐府时,这里的工作的人员有八百二十九人之多,其最盛时恐怕还要不止此数。例如据桓谭《新论·离事》所说,他在成帝时为乐府令,手下“有千人之多”。
乐府所采得的民歌,见于《汉书·艺文志》记载的,有一百三十八篇,来自全国各地,包括现在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甘肃、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乐府工作者不仅记录歌词,而且记录乐谱,当时称为“声曲折”,例如《汉书·艺文志》著录河南周歌诗七篇,另有河南周歌诗声曲折七篇;有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另有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据《宋书·乐志》等提供的信息可以知道,汉代采集的民歌大抵是“街陌歌谣”,只能唱诵,没有配乐(清唱),等到乐府工作人员将这些民歌民谣连同其“声曲折”采集来之后,由著名音乐家李延年等“略论律吕”,配以笙、笛、节、鼓、琴、瑟、琵琶等器乐的伴奏,成为更高级的艺术音乐作品,水平大大高于先前的民间原生状态了。
武帝时乐府工作人员采诗不仅包括黄河、长江两流域的广大地区,还很注意吸收北方少数民族的乐调,可考者有鼓吹曲和横吹曲,鼓吹曲配器用箫、笳,横吹曲用鼓、角。歌辞现存者仅有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其中有些大约是翻译成汉语的少数民族的民歌,如《上邪》《有所思》《战城南》等等;有些可能是汉族文人的依声填词之作,如《朱鹭》、《上之回》等等。据说李延年曾经“用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古今注·音乐》),可惜到魏晋时代已经失传,这“二十八解”是只有曲调还是兼有歌辞已不得而知。汉朝人乐于吸收少数民族音乐,表现了一种开放的胸襟。一部中国音乐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不断吸收少数民族和外国音乐以丰富本土主流的历史。
这时的表演,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无歌辞的歌舞,一种是有歌辞的演唱。后者以唱为主,局部配乐,例如汉代最流行的“相和歌”,表演的情形就是“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宋书·乐志》),持打击乐(节)的歌手主唱,另有乐队伴奏,但弦乐和管乐只是在“和”的部分才演奏。所谓“和”,就是在主唱者歌唱的某些部分,另加若干人一起去唱,这些地方应是高潮部分,器乐的伴奏也就加在这里,帮助形成高潮。现存汉代乐府民歌的大部分就是这种相和歌辞。
相和歌曲调很多,主要的有三种,即清调曲、平调曲、瑟调曲,通称为“清商三调”。大曲和楚调也属于汉的清商部。清商乐(也可以简称为清乐)是汉代最为流行的俗乐,后来就成了俗乐的代名词。《宋书·乐志》著录“清商三调歌诗”三十五曲,其中有汉代的相和歌和汉魏之际曹操等人的作品。《隋书·乐志》说:“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到曹魏以后,音乐方面的情况已经有了若干变化,这里无从多说。(可参见顾农《建安时代诗-乐关系之新变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隋唐以后,燕乐兴起,流行已久的清乐就显得古老了。就唐代而言,燕乐是最新流行音乐,清乐则是曾经流行的音乐;就汉代而言,清商乐是当下最流行音乐,与此相应的,《相和歌辞》是汉代民歌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有些汉乐府歌辞弄不清原来属于什么曲调,《乐府诗集》另行归入《杂曲歌辞》。现存汉代乐府民歌,收在《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中的,一共约有五十首左右。
汉武帝刘彻在宫廷中常常享用的就是这些从民间和少数民族那里拿来并经过加工的音乐文学作品,此即所谓“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汉书·礼乐志》)。刘邦时代郊庙还是用雅乐的,到这时也被俗乐所取代。刘彻其人气魄极大,敢于藐视传统。守旧的人物对此是不以为然的,例如董仲舒就否定乐府,淮南王刘安、河间王刘德先后献出雅乐,要求朝廷采用,而武帝都不予理睬。
三
雅、郑之争后来一直未断,经常有人弄出古老的雅乐来希望朝廷承认并采用,但在实际生活中不起太大的作用,“至成帝时……郑声尤甚”(《汉书·礼乐志》)。到绥和二年(前7年),汉哀帝解散乐府,情况发生重大逆转。哀帝的诏书道:“郑声淫而乱乐,圣王所放,其罢乐府!”(《汉书·哀帝纪》)他所要取消的实际上只是采集民歌并进行加工的工作人员,而“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汉书·礼乐志》)。根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人建议,罢去四百四十一人,保留三百八十八人,归入“太乐”。从此,雅、俗两个音乐机构并存的局面被取消了。采集民歌的工作一度中断。
俗乐虽然在哀帝的朝廷上失去地位,仍然十分流行,被遣散的乐工流入民间,很可能恰恰增强了俗乐的传播,使之产生更大的影响,《汉书·礼乐志》说:“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沉湎自若。”这也正表明了汉哀帝的彻底失败。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也非常欣赏“郑声”,例如著名学者桓谭就是一个典型,详见其《新论》及《后汉书·宋弘传》。
乐府机关虽不复存在,其成果与影响却决不是一道圣旨就能取消得了的。
东汉未立乐府,但有一个新设的管理民间音乐的“承华令”,主管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之所用焉”(《隋书·乐志》)。这时表演的还是相和歌、铙歌之类“郑声”而非雅乐。东汉时代黄门鼓吹乐与大予乐主管的雅声并立,实际上恢复了哀帝以前雅俗并存,以雅乐装点仪式门面、以俗乐为日常实际享用品的局面。
东汉朝廷也曾经派人到各地采风,如光武帝刘秀“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后汉书·循吏传叙》),汉和帝刘肇“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后汉书·季郃传》),直到汉末的灵帝刘宏还有类似的举动。但这时没有像西汉乐府那样的机构,也不是通过黄门鼓吹乐来做此事,采风的政治意味甚浓,重点在于通过各地的歌谣了解情况特别是地方官的优劣。尽管这种特使活动的主要目的并不在音乐文学方面,但意义仍然非常重大,现存的乐府诗以东汉时代的为多。
四
汉代有些采集来的歌谣没有为之配乐,还有些歌谣不是朝廷采集而是从其他途径得到记录的,严格地说这些作品因为未入乐而不足以称为乐府诗,但也是很重要的材料,如果从文学的角度看,它们与乐府诗并没有什么原则的差别。《乐府诗集》收录这些作品入《杂歌谣辞》。
与此相反,可能有若干乐府诗虽然曾经入乐,后来却脱离音乐,失去标题,于是就被泛称为“古诗”。这些诗中往往还保留着曾经入乐的痕迹,例如有些句子带着歌人口吻,有割裂和拼凑的痕迹,运用乐府套语等等,有些“古诗”前人引用时往往迳称为古乐府。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些诗也确实可以视同乐府诗。“古诗”中有些是民歌,有些是文人之作,有些是经过文人加工的民间作品。《孔雀东南飞》(原题《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即属于第三种情形。
但“古诗”中也有些是与音乐没有什么关系的所谓徒诗。由于那时乐府诗影响很大,所以诗人有时也会采用一点歌者口吻,外貌有点像乐府诗,而实为徒诗,《古诗十九首》应属此种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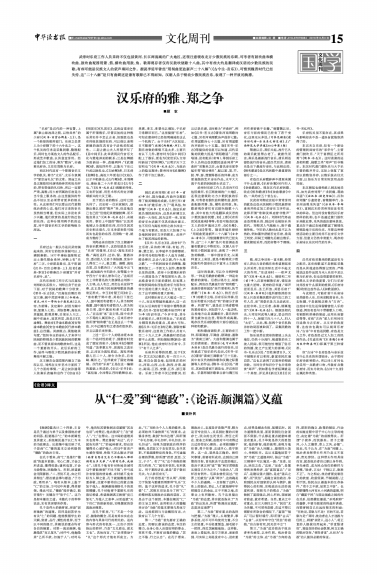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