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冠英先生(1906~1995)是著名的文学史家,也是当代成就最高的人文学者之一。余先生学生时代喜欢创作,常用“灌婴”等笔名发表散文、小品和新诗,已引起文坛的注意。吴组缃认为他是最能代表清华园文风的作家,说他的委宛冲淡处近于朱自清,轻快趣味处像周作人、俞平伯,而纤巧绮丽处则是他自己的。(《谈谈清华的文风》)1931年余先生从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此后一直专门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1945年起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调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现在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之前身)为研究员,一度任副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余先生的著作有《汉魏六朝诗论丛》《古代文学杂论》两本论文集,上世纪六十年代主持编撰了文学研究所三卷本的《中国文学史》,是全书的总负责人和上古至隋这一部分的主编。新时期以来,又担任十四卷本《中国文学通史》的主编(后因年高多病改任首席顾问)。这两套文学史乃是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具里程碑式意义的重大成果。由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撰的《唐诗选》也是在他主持下进行的。
更为一般读者所知的是出版比较早、由余冠英先生个人署名的几本古代诗歌的选本:《诗经选》(后将曾经单行的《诗经选译》一书并入)《乐府诗选》《三曹诗选》和《汉魏六朝诗选》。这些书原先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陆续出版的;现有中华书局2012年的新印本,均以余先生生前的最后修订本为底本,印刷和装订都相当朴素而考究。
在这几部书中《乐府诗选》是解放后最早出版的古代文学作品选读本,书中出于余先生研究心得的新意很多,行文深入浅出,是公认的经典性选注本。该书前言中又有从中国文学史全局着眼的大议论道:
《诗经》本是汉以前的“乐府”,“乐府”就是周以后的《诗经》。《诗经》以“变风”、“变雅”为菁华。“乐府”以“相和”、“杂曲”为菁华。主要的部分都是“感於哀乐,缘事而发”的里巷歌谣。都是有现实性的文学珠玉。诗经时代和乐府时代隔着四百年,这四百年间的歌声却显得很寂寞。并非是人民都哑了,里巷之间“饥者歌其事,劳者歌其事”还是照常的,可不曾被人采集记录。屈原曾采取民间形式写出《九歌》、《离骚》等伟大诗篇,荀卿也曾采取民间形式写了《成相辞》,而屈、荀时代的民歌却湮灭不见,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因此我们更觉得汉代乐府民歌能够保存下来是大可庆幸的。(中华本,第10~11页)
传世之汉乐府民歌的价值由此得到了深刻的说明和估计。余先生又写道:
中国诗史上有两个突出的时代,一是建安到黄初,二是天宝到元和。也就是曹植、王粲的时代和杜甫、白居易的时代。董卓之乱和安史之乱使这两个时代的人饱经忧患。在文学上这两个时代有名自的特色,也有共同的特色。一个主要的共同特色就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为时为事”是白居易提出的口号。他把自己为时为事而作的诗题做“新乐府”,而将作诗的标准推源于《诗经》。现在我们应该指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但是发展成为一个延续不断的、更丰富、更有力的现实主义传统,却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中华本,第12~13页)
这样就把中国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也一并讲得很清楚了。余先生不是一般的选家,而是胸罗全局、见识极高的文学史家。至于他对乐府诗具体文本的注释讲解每多新意,平易通达,引人入胜,更是有口皆碑,被引用的频率很高。余先生其他几部诗选,也都具有既脚踏实地又高屋建瓴的优点,所以多年畅销,为广大读者所爱重。
余先生将古老的《诗经》翻译成白话文,水平同样大大高于流俗。他本来就是诗人,又是《诗经》专家,遂能做到以诗译诗,以歌谣译歌谣,不仅译得很准确,而且词汇、句法皆取自口语,念起来上口,听上去顺耳,达到一种“化境”。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如果我们把《诗经选》《诗经选译》《乐府诗选》《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选》《唐诗选》整个地通读一过,把入选作品读懂,并能理解余先生的有关议论,那么我们就算是把中国文学的一半弄清楚了。
今年是余冠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我学生时代得到过他的指教,一直深为感激(参见顾农《追怀余冠英先生》,《散文》1999年第11期;又收入《听箫楼五记》一书,东南大学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而认真读他的遗著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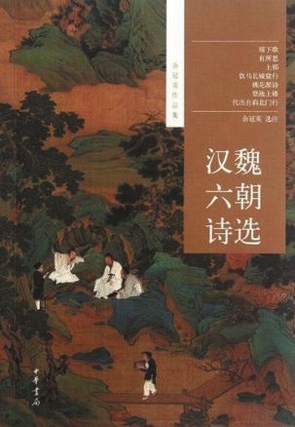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