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不知道,与冯先生死生契阔、执子之手、相携终老的姚先生,在课堂上娓娓道来、授业解惑时的形象又是怎样的温婉而绰约?或仅仅是“努力作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教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生史、课程史或教师史的研究或许可以更形象地复原那已经远去的历史场景,让我们回到那个生气盎然、星光灿烂的遥远年代。
在中国的德语文学学科史上,姚可崑(1904—2003)是一个不该被忘却的名字。作为本学科重要建立者——冯至——的夫人,姚可崑当然是时常被提及的,但如果将其作为一个女性教师、翻译家与学者来定位,其实更值得特别开掘和表彰。
姚可崑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学生,她与冯至的中介是冯至的好友杨晦(1899—1983),因他其时正执教于此。两者相识,乃有“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佳话。
对德语教学史的贡献
就德文学科史来看,1950年代之后的院系调整,乃是特别值得关注的教育史事件,因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姚可崑的角色日益吃重。按照我的判断,这是在现代大学—科学院模式之外的另一种二元体系构建,即综合大学—专业学院模式。北外—上外的建立,构成了中国现代外语教育的另类模式,优劣姑且不论,至少就大学和学科发展而言,确实丰富了其构成。作为北外德语学科的创建者之一,姚可崑的意义自然不容低估。
开创一个新的专业,困难之大,自然可以想象。按照姚可崑的回忆:
当时由北大弄来几本柏林大学附设德语速成班的教材影印本作教本,进行教学,同时设有翻译与翻译练习课,练习材料选自仅有的几张德文报纸。50与51年都有人去东欧及民主德国,由苏联带回一批德语教科书,德文组于是选用了一本苏联大学用的德语教科书作教本,在使用时作了一些适合我国国情的修改。后来与北大德文专业合作编写过我国首次出版的德语教本。
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北外德文学科的最初建设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的,而作为中国德文学科鼻祖的北大,作为近邻者,自然成为求师学艺的对象;而姚可崑和冯至(其时执教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的关系,也许就是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切入点。
以蔡元培的北大时代为开端的德文学科建设,乃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的一个重要事件,而这种注重学术含金量、以高起点为平台建设标准的思路,随着1950年代的时代风云的展开,并没有被完全抹去,而是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继续延续着。北大—南大系统作为综合性大学,合并了相关地区高校的学科和专业,前者合并了如清华、辅仁、南开等校的德语专业,后者则容纳了同济、复旦的德语专业;而北外—上外系统则以崭新的方式展开了新建过程,走的路子是社会主义的“外语专业”培养模式。
姚可崑的角色,似乎一直掩在幕后,但随着烟尘散尽,场景复原,我们可以从材料中一点一点追溯到那个在历史风尘中一路走来,仿佛弱女子、但却很执着的女学者的模样。在我看来,她至少有三点值得表彰:其一,作为一名德语教师,姚可崑始终坚守在了教学岗位上,并对中国德语教育的外语学院模式之开辟有所贡献。这一点并不自北外时代起,早在沪上的吴淞时代,她就“被安排在同济附设高级职业学校教德语,作兼任教师,每星期八小时”;随冯至漂泊西南天地间的时候,她也曾在一些学校教授德语,积累了颇为丰富的教师经验,譬如曾任职于中山大学、中法大学、北大医学院等校,在北平师范大学还教过国文等课,甚至差点就成了同济大学的德国文学教授。所以到了建立北外德语专业的时候,她自然也就得心应手了。
其二,作为开创者之一,她参与和领导的北外德语系的创建工作,在德文学科史上是值得肯定的。当然,是否建立起一个有益的、有发展性的模式,那是另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姚可崑当过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教研室主任,说来也是独当一面了。关于此期的教师生涯,姚可崑曾有过描述:
负责筹备德文组的是李遇安,和我同时到德文组的另一位教师是李康,他们都是留德同学。我到校的那天就考新生,一共十四人,全被录取了,都是男生。程度相差很大,从九十八分到二十一分。因为有人是同济大学附中毕业,入了同济大学,上海一解放就参加革命,德语相当有基础;有人只在大学选修过第二外语德语。我和李康从4月4日起始在外校授课。十四名程度不齐的学生编成一班,教课相当困难。我们从头教起,让同学们各显神通,成绩突飞猛进。一个善于幽默的同学说出一个比喻,他说,“德”字就体现了德文组当前的情况。两个教员是双立人“彳”,十四个学生是“(十四)”,一条心是“(一心)”,我们师生不就是这样共同努力前进吗?这班同学的年龄相差也很大,大的四十七岁,有长期的工作经验,小的不到二十,刚入大学;有老党员,有新党团员,还有群众,大家亲密相处,互助互爱,砥砺切磋,都一心一意地为革命学习。德文组搞得很红火,这一班学了一年半就毕业了。可是正式毕业时,只剩下四名学生,其他十个人都为了工作的需要在学习的中途陆续被调走了。
其三,在教材编写、词典编纂方面,姚可崑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譬如,她主持编写了《德语》(1—4册)全国统编教材,参与编写了《新汉德词典》,也审定过张才尧编写的《实用德语语法》这类教学用书。1994年,弟子伉俪叶本度、刘芳本为姚可崑九十寿诞写过一张“苦中乐”的贺卡,“烧饼+咸蛋育才几十载,徒子+徒孙脚踩五大洲”,中间是“一颗赤诚之心”,可以见出姚氏在教学和教材编纂方面的努力和贡献。这些都是中国德语教育史上非常重要的、具有奠基性意义的知识大厦积累工作,同样值得充分肯定。
北外德语系的发展,有其特殊的模式,相比较北大的思想自由与兼容传统,北外自然以服务现实自诩,说到共和国驻德语国家系统的大使、参赞之类的官职多少很是引以为荣,这虽然与大学的高端定位相去甚远,倒也能体现出新建学院的现实功能。
翻译贡献与留德规训
对姚可崑这样的女性,显然不能简单地以一个模式来限定她。其实,就本职工作德语教学之外的成绩来说,应该承认她是一个有贡献的翻译家。她翻译的若干著作其实还是可圈可点的,稍作归纳,包括《引导与同伴》、《卡拉尔大娘的枪》、《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与冯至合译)、《楼兰》、《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牺牲行》、《忆果戈里》等,可以说不但颇为丰富,而且都是有颇高的文学和学术价值的。
姚可崑作为文学翻译家的成绩,确实值得重视。在文学作品方面,与冯至合译的《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乃歌德的经典小说,其价值毋庸赘言;而《卡拉尔大娘的枪》是布莱希特的名剧。卡罗萨的《引导与同伴》,乃是很有意味的作品,其在纳粹时代的内心流亡与坚守,是相当有象征意义的(可惜至今仍未得到中国学界的充分关注),可见姚可崑的眼光和水平。在《译者序》中,她这样写道:“在德国现代的文学界里,自从里尔克和盖欧尔格先后死去,托马斯·曼流亡国外后,卡罗萨以他深沉而谦虚的努力渐渐固定了他所应得的地位——变乱时代里一个最纯洁,最真实的诗人。他的著作并不多。”这话是何其地熟悉,自然让我们想到冯至的语言,简洁而深刻,有文学史的通识却又融于叙事关注之中。
至于像《楼兰》这样的著作,可归之于敦煌学著作了。而在1940年代,姚可崑还翻译了尼采的《历史对人生的利弊》,也是很有学术价值的。之所以能在一个相当高的文学、学术和知识平台上选择翻译文本,显然和夫君冯至勾连起的知识网络有关。这不仅在日后通过徐梵澄、陈铨等人表现出关联性,而且是从最初的“德国伴读”时就开始了。她作为留德学生,在海德堡大学课堂同样也与一代大哲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1883—1969)有过“亲密接触”。冯至曾说过:“我在德国Heidelberg大学听过Jaspers的课,一门课讲Kant,一门课讲Nietzsche,他讲课时也常常提到Kierkegard,我博士考试时,Jaspers考过我的哲学课。”1935年5月27日,冯至把论文送至布克教授处审阅;6月22日进行第一次口试答辩,主考为指导教师布克教授、古德语教授潘采尔;6月27日进行第二次口试答辩,主考为雅斯贝尔斯教授和美术史教授戈利塞巴赫。相比较夫君作为博士生较为刻板的考试型叙述,夫人姚可崑的回忆要更加自在和清晰些:
我们都是哲学院(即文学院)的学生,他(指冯至,笔者注)的主科是德语文学,副科是哲学、艺术史;我的主科是哲学,副科是德语文学、艺术史。我们选修的课程大致相同,其中以亚斯丕斯(Jaspers)的课程最多。亚斯丕斯当时在德国是与海德格尔(Heidegger)齐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为人和蔼可亲,讲课深邃洞彻,听他课的人总是挤满了大教室,后边还有人站着听。我经常是早去占座位。听讲时,我有许多地方不懂,笔记更记不下来,冯至比我听懂得多一些,但是笔记也记不全。幸而后来有一位德国同学,名登克曼(Denck-mann),他常常友好地把他记得很详细的笔记借给我们参阅,自己有一种不该有的优越感,如今轮到我依靠旁人的笔记了。实际上这不只是语言问题,主要是我哲学的根底太浅。
通过她的这番描述,我们仿佛置身于雅斯贝尔斯海德堡授课的大讲堂中,重温那代人的求知之乐。不仅如此,姚可崑和雅斯贝尔斯还有过师生相对的“亲密接触”,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按照姚氏的回忆:“德国的大学生都要在选修册上填写选修的课程,学期开始时请教师在上边签名。我选亚斯丕斯的课,去请他签名时,他总是含笑地望着我,管我叫‘小姑娘’(dieKleine),他给我的印象很深。”不仅如此,即便在多年之后,雅斯贝尔斯还能记起这个昔日选课的中国女孩:“战后我们的朋友鲍尔去拜访他,他还向鲍尔问那个‘小姑娘’近况如何?”女性之绰约风姿,自然是让人易生亲近之心而印象深刻,而姚可崑的窈窕少女的留德时代也真是可以纪念。
较之冯至,姚可崑无疑是雅氏更忠实的学生,据她自己回忆,选修过的课程有八种之多:“哲学逻辑”“尼采”“现代哲学史”“从康德到现代的哲学史”“基尔克郭尔”“康德研究”“哲学引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研究”等。从姚可崑在海德堡大学的“学业手册”(Studienbu⁃ch)来看,她虽然在海德堡大学不过两年时间,但选修课程确实不少。这其实也反映出姚可崑求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兴趣广泛、广种薄收:
那时我精力旺盛,自以为德语已掌握得差不多了,想扩大语言范围,学古代语言。登克曼极力劝我学古希腊文,说希腊文的文学哲学太丰富了,一生享用不尽。我就在大学选修古希腊语课,还在外边找一位私人老师每周学两小时,果然我学得还好,能借助注释读些浅近的希腊文学作品了。我非常兴奋,在准备回国时,买了几种古希腊文学书籍,如英国牛津版的《柏拉图全集》等,以便终生研读。谁知回国后哪里用得到希腊文,那些书束诸高阁,一放就是十多年,后来都被冯至捐赠给图书馆了。而我在病后记忆力衰退,把希腊文忘得一干二净,现在只想得起来教本第一页上的第一句。当时冯至不赞成我乱搞,说我不踏实,不切实际,我反而嘲笑他“十载专攻德意志”。其实他并不死守一门,他常围绕一个课题广泛而深入地阅读许多书籍。他的视野比我宽广得多。
这种不求甚解的现象,也不仅是某个个体的情况,可能在国外留学者或多或少都存在,比他们还早些的张君劢(1887—1969)在谈到他们那代人面对西方学说时的盲目曾这样说:“好像站在大海中,没有法子看看这个海的四周……同时,哲学与科学有它们的历史,其中分若干种派别,在我们当时加紧读人家教科书如不暇及,又何敢站在这门学问以内来判断甲派长短得失,乙派长短得失如何呢?”显然,冯、姚二人所经历的颇为类似:
在1934年至1935年冬季学期,我因为选修雅斯丕斯的“康德研究”,费很大的力气去读康德的《纯理性批判》。我一字一句地细抠,仿佛懂了,其实并没有懂。但我很有耐心,竟这样读下去,读完全书。这是我生平潜心细读,不烦不躁精读的一部“没读懂的书”,也是对我的一次考验。我也和冯至共读过一本康德较为易懂的书《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从这本书里懂得多了一些。冯至考博士时,副科口试《纯理性批判》,雅斯丕斯还给了他“良”的评语。我不知道他究竟懂了多少。
但也正是因为这些在德国大学里“艰苦读书”打下的扎实基础,无论是读康德的艰深哲学,还是与雅斯贝尔斯的幽默对话,都使得姚可崑有底气日后去面对各种艰难的挑战,也为她日后展开的翻译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因为知识系统从本质上来说是相通的,并没有真的学而无用的知识。说其是个“名声显赫”、“成就卓著”的翻译家或许太夸张了,但她毫无疑问应该是翻译史中一个不应被遗忘的,坚实前行、踏实工作、自得其乐而默默奉献着的普通人!
琴瑟和谐,与留德学术群相得益彰
要更加客观地评价姚可崑的学术成就,也就不能狭窄地看待她的一生,而是应将其家庭生活和学术共同体结合起来考察。郑敏(1920—)曾回忆她与冯至夫妇的因缘:“1939年,我在西南联大哲学系攻读的是西方古典哲学,选修了冯至先生关于歌德的课,并读了冯至先生翻译的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这些都对我影响非常大。”学生回忆老师,多半褒扬备至,但我们这里看重的是记录的历史细节:
我就曾在某晚去冯至先生在钱局街的寓所,直坐到很晚,谈些什么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冯至先生、姚可崑先生(冯至先生的夫人,北京女子师范学院毕业)和我坐在一张方桌前,姚先生在一盏油灯下不停地织毛衣,时不时请冯先生套头试穿,冯先生略显犹豫,但总是很认真地“遵命”了。当时师生关系带有不少亲情的色彩,我还曾携冯姚平(冯至先生的长女)去树林散步,拾落在林里的鸟羽。但由于那时我的智力还有些混沌未开,只隐隐觉得冯先生有些不同一般的超越气质,却并不能提出什么想法和他切磋。
不愧是诗人手笔,文字之中充满了温情和诗意,这里展现出的不仅有师生间温馨的亲情关系,也表现出诗人冯至作为老师的那种诗性本质。而郑敏作为弟子辈的诗人代表,对冯至代表的现代中国的德诗流脉是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的。
不仅有师生相通的知己之谊,还有友朋问学的求知之乐。姚可崑在《历史对人生的利弊》翻译过程中曾明确致谢:
这部《观察》是一篇生力充沛的文字,在尼采早期的作品里与《悲剧的产生》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它出版后虽然不曾得到什么反响,但是它的意义与日俱增,后来在德国的思想界发生了很大的启示作用。就是在现在的中国,这本书可资借鉴的地方也不少。只可惜译者的能力有限,不能把尼采的丰富的、热情的词句表达出来,原文越是精美有力的地方,译者对于译文越感到不满。此文译成后蒙贺麟先生把它收入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丛书”中出版,并蒙杨业治先生校阅一遍,译者在这里谨致谢意。
从这段表述来看,我们至少可以由这本小书勾勒出一幅相当全面的留德学人群像来,不仅有冯至、姚可崑夫妇,还有贺麟、杨业治等。冯至自然不用说,作为夫君和“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日耳曼学整体修养与学力都是出类拔萃的;而杨业治作为专业同行,他虽“述而不作”,但学养上佳;贺麟的哲学家身份及其留学美、德经验,都使其在学界地位不凡。他们携手合力,乃能有尼采这部短小精悍的汉译著作的诞生。
学生回忆冯至先生的德语教学场景,也是让人感动。杨祖陶(1927—)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也是冯至当年课堂上的学生。日后,作为知名学者和哲学译者的杨祖陶这样回忆:
说到翻译工作,我不由自主地首先想起我跟冯至先生学习德语的情景。鉴于我对德国哲学的浓厚兴趣,除公共英语外,我一直盼望着能够学习德语。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1947—1948年度,冯至先生开设了一门德语专业班的德语课程,上下两学期,每周12学时。冯至先生是年轻学子仰慕的联大外文系的德语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22岁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的才华横溢的诗人。能在冯先生的课堂上学习德语真是有幸之至。冯先生课堂约有30余人,先生教学极其认真,对学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我记得,我们上第一堂课,他就是用德语讲授,营造一种语言环境。依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他用德语提问,也要求学生用德语回答。冯先生这种教学方式激起了我们这些初学者的极大兴趣与热情,但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对我们施加了一种学习压力。为了能听懂先生的讲课、特别是提问时不致落伍和尴尬,我们都要紧张地抓紧时间进行预习与复习,不敢稍有懈怠。德语的变格、主动被动态以及代词、冠词的应用都很严格,与英语不同,开始很不习惯。冯先生从不孤立地生硬地讲语法,而是通过课本的小故事生动地讲授各种语法现象,培养初学者的德语思维习惯,同学们都感到受益匪浅。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诗人和日耳曼学家的冯至形象,更是一个脚踏实地、平稳务实的德语师者形象,是一个丰富的、立体的、大写的真诚的师者。当初的学生闻山(后以诗人出名)也曾记录过他在西南联大时代第一次听冯至的选修课“歌德”的课堂场景:“1943年冬天,云贵高原一个天高云淡的日子。……在一个课室里,冯至教授正在讲《歌德》。他穿着蓝布大褂,戴着近视眼镜,脸方正,身子也宽大,声音沉稳、安详。他引导着听讲的人们进入一个遥远的诗的世界。”而这其中不仅有联大外文系学生,还有不少慕名旁听者,其中就有哲学教授沈有鼎。当年的学生赵瑞蕻(1915—1999)也有回忆,他听过冯至讲歌德的名作《魔王》(Erlkönig):“冯先生讲课生动有味,又踏踏实实,深入浅出,很吸引人。我虽然初学德文,但听冯先生讲解《魔王》,我居然大体上懂得。”确实还是使人十分向往。
真不知道,与冯先生死生契阔、执子之手、相携终老的姚先生,在课堂上娓娓道来、授业解惑时的形象又是怎样的温婉而绰约?或仅仅是“努力作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教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生史、课程史或教师史的研究或许可以更形象地复原那已经远去的历史场景,让我们回到那个生气盎然、星光灿烂的遥远年代。
(此文关于姚可崑先生的材料,颇多由冯姚平先生见赐;成稿后并蒙她审阅赐教,特此致谢。)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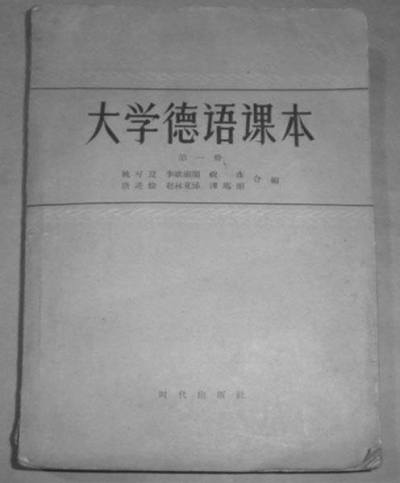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