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中间,我们都去哪儿呢?庙会。
庙会很有意思,我们先说它为什么叫庙会,它怎么不叫集会呢?就因为过去人头攒动、商贾云集的地方都在庙宇旁边,汇集在一起,所以叫庙会。
记忆里的北京城庙会
北京过去最有名的庙会是哪儿,你知道吗?是隆福寺。可惜隆福寺今天没了,隆福寺没了真是很可惜。为什么隆福寺没了呢?皇家大寺院,占地那么大,那么宏伟的建筑为什么没了呢?给拆了。它为什么被拆呢?就因为它占地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正是需要地皮的的候。小庙拆不出地方,所以一定要拆大庙,大庙本身前面空场就大,再把这庙全部拆干净,巨大一块地就出来了。拆完了隆福寺,隆福寺就剩了一个名。隆福寺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很红火,上小商品市场上服装市场。后来盖了个大楼,最后一把大火,歇到今天,它再也火不起来了。
与隆福寺遥相呼应的是护国寺。护国寺的寺院也比较大,但跟隆福寺比就差很多了。隆福寺的庙会是北京首屈一指的,商贾云集,到民国时期,连外国人都特别爱逛这个庙会。因为地理位置所致,隆福寺也称之为东庙,而护国寺称之为西庙,东西二庙是当时北京城区——内城城区里,两个非常聚集人气的地方。
今天各个城市都有超级大商场,各种品牌聚集在一起。过去没有,过去不提供这个场所,所以商业云集的地方一定是大空场和集市。这集市一到过年过节就更加热闹,所以就形成了庙会。庙会慢慢就演变成一个固定的词汇,指的是过节时期,尤其是过年这日子里一个攒人气的活动,大量的人要到那里去吃,去购买各种好玩的东西,再有就是买古董。你看看王世襄先生的很多回忆录,就讲当年很多东西发现于隆福寺庙会,这些东西今天都成为国之重宝。
春节期间,各地方都有庙会,有表演,有商品销售,主要是小吃,大家都不是为消费,就是为了一个乐,能在那里看到风土人情。我第一次逛庙会印象太深刻了。小时候逛庙会心里非常乐意,但实在是个灾难。有一个地方叫厂甸,就在琉璃厂那个地方,暴土狼烟,都是土地场,人挨人。我小时候印象深刻的就是视野可及全是大腿,全是各种人的腿,因为你个儿矮嘛。我爹给我买了一个巨大的糖葫芦,至少有个三尺长,我扛着,一直扛到家,舍不得吃,拿着玩。当时多少钱呢?巨贵,一块钱。
由于庙会人多,走道的人多,地上那个土都趟起来了。每回从庙会回来的时候,从上到下这衣服都得出去抽打。北京人谁家里都有一“抽打”。一顿抽,抽得到处都是土,抽干净了进屋。我小时候对庙会就有这样的概念,比如卖糖葫芦的肯定最多,什么捏糖人的,搞棉花糖的。过去那庙会啊,它实际上是逢五逢十就有,不是说一定要过年过节,过去的庙会就是今天的集市嘛,农村都是五天一小集,十天一大集。
大众庙会有文化
报国寺今天就是一个收藏品市场,我前些年还去逛过,也买过东西。地摊上买东西,跟商店是不一样的。人进商店脸皮薄,不好意思乱砍价,这东西人家开一个价,你还价也是有幅度的。但是去庙会集市上,尤其去报国寺,还价都是拦腰一刀,都算你是财主了,说你真有钱,上去就只给了拦腰一刀。不应当,该是在脚面上一刀,挨着鞋底砍价。人家说这东西要多少钱呢?要一千块。说那我给你三十行不行?那人说你能不能加点,说加五块,得,三十五就是你的了。备不住就有这事,所以那时候我就去逛报国寺。报国寺更多的东西是一种民俗的东西,比如一根烟袋啊,比如荷包啊,比如墨盒啊,都是一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今天你转过头再去想,很多鸡零狗碎的东西,如果你能把它收藏成系列,也非常有价值。比如墨盒,我喜欢古董时,北京到处都是。
过去你在庙会上,比如在报国寺那集市上,经常能看到一些铜墨盒。铜墨盒两人刻得好,一个叫陈寅生,一个叫姚茫父。过去我看到这都不当事儿,只是觉得,哎哟,这人刻得真好。你知道在铜上用刀刻出画,刻出书法,写的那蝇头小字,那不仅是腕力,那是一种功夫。今天如果说你收藏几十个民国时期的这种刻铜的铜盒,铜墨盒,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你再把这些人的画片,这个文字和这些刻铜的艺人都研究透了,出一本书,那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当时就没有顾及,也不觉得那是个事儿。墨盒这东西跟过去有一个极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它可以续墨。古人写字很麻烦,提前研磨,得研一个钟头,把这墨研出来写字,写字写到半截,如果吃个饭或打个盹,回来这墨就干了。清末到民国初年的时候,有人发明了铜墨盒,那铜墨盒都严丝合缝啊,里头有丝绵,把研好的墨倒进去以后呢,不用的时候盖严了,什么时候打开都可以用。
小时候描红还用过这墨盒,所以墨盒也是那一个时期的文化。我仔细想一想,铜墨盒尤其是那白铜墨盒的存在,上下都不足一百年,它第一个出现到最终消亡,都不到一百年。一百年的历史在文明史上,是很短暂的一个瞬间,如果这个瞬间存在的一件东西你对它有所研究,你知道它那时候对文化的一个贡献,那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馀味酸甜的眷恋
小时候到了庙会上,就是看人家怎么吃,看人家怎么做。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蘸糖葫芦,最早吃的糖葫芦晶莹剔透,鲜红鲜红的,冬天的日子里吃一口,又甜又酸,美得不行。
第一次看蘸糖葫芦,把我看呆了。这蘸糖葫芦跟今天有点不同,首先,过去糖贵,把糖熬成糖稀,这糖葫芦蘸进去以后,拿出来往哪儿放啊?放在一块青石板上。青石板冷却得快,冬天在院子里啪一放,一会儿就冷却,“叭”就拿下来了,这边还有点热乎劲呢,特有意思。后来这青石板没了,我再见蘸糖葫芦的,好多人是在木头板上刷一层油往上蘸,糖在高温下是黏的,很容易粘,只有那青石板特别光滑,蘸在上面特别有意思,一拔,“叭”。我小时候看着人家那个往下拔,一会儿晾满满一溜儿,最后就拔下来,往那儿一插,就开卖了。后来看卖糖葫芦的,都是自行车后面插一草垛子,插得跟那刺猬似的。糖葫芦是越做越精了,可我们对那个印象是越来越远了。什么叫越做越精了呢?小时候糖葫芦就是糖葫芦,就是山楂直接串一大竹条子。现在去了核,加上馅儿,里头又有山药,又有橘子什么的。这种改良的吧,既不好吃,又没文化。我觉得,山楂在中国北方的食品中,尤其在这果品中,是代表一种文化,它是一种典型的草根文化。在所有的水果里它最便宜,再甜它都酸,有多酸呢,就我说的这会儿就满嘴的口水,得不停地下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反应,我说不下去了,太酸了啊。这个要赶上一个酸的,你吃完了都睁不开眼,能酸成那样,但小时候就爱吃。
我去年冬天去北京西郊大觉寺,著名的辽代大寺院。那寺院很有意思,人家那门都冲南,它冲东。到那儿去,出了门的时候,看一农家老太太在那里卖山里红。我跟她聊了一会儿天,买了几斤山里红,老太太认出我来了,看着我说,您给鉴定鉴定,这是不是真的。
今天,山里红糖葫芦依然是庙会主角。它不仅仅是一个食品,更重要的是一道风景。你仔细想,今天庙会上什么东西卖得多呢?羊肉串。羊肉串没有观赏性。你想想我小时候,我爹给我买那大糖葫芦,一直扛到家,上面甭管落多少土,回家也吃了它,对吧?扛着,好看。这一小孩,扛着一个大糖葫芦,就是一个风景。你说我扛一羊肉串,弄一身油还不说,这东西回去也没法吃了。所以,在整个的庙会当中,什么叫文化?我们老说这人没文化,没文化,你举着羊肉串就没文化,举着糖葫芦就有文化。这个文化首先是颜色吧,红色是中国人认为最喜庆的颜色,在过春节这样的日子里,庙会中一定要有一抹红色。你看我,露一点红,为什么露点红呢?过节了。跟这道理一样。今天的庙会呢,显得更加商业化。
古代的庙会,清代的庙会,包括民国的,以及早年的庙会,它也很商业化。但它商业化中容纳了很多人情,这种人情是什么呢?就是我讲的生人要熟,每个人都是客人。那些掌柜的,招待每个人都是笑脸相迎。没有那个你爱买不买的意思,都是很热情地招待人。今天庙会上的生意,都做得过于急切。摊位费太贵,一旦有这种压力,生意做起来就没那么自如。我们很希望形成一种现代化的商业,就是既有商业,又有文化,还有人情。
(本文摘自《都嘟——马未都脱口秀1》,马未都著,新星出版社2015年11月第一版,定价:48.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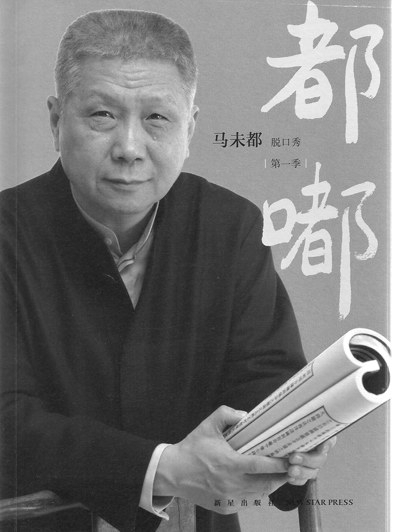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