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的新书全名《战争:从类人猿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和演变》,与前年同在中信社出的《西方将主宰多久》《文明的度量》实为三部曲。此书观点前言中就阐明了:
1.人类通过战争创造更大、组织更好的社会,减少了成员死于暴力的风险。
2.为此,战争几乎是人类迄今发现的唯一方式。
3.战争创造的更大社会长期来看也让人们更富有。
4.战争正在自我终结。
然而它们以前两部为基础,新读者易被误导,目光都落在了“是否美化战争”之类枝节上。譬如怎么衡量社会“组织更好、更富有”?如何评估作者以“利维坦”代指的强大政府之实力、间接推断暴力死亡率的下降?都离不开前两部引入的“社会发展指数”,由四项指标加总而成:最大城市规模、文字和计算系统、战争能力、能量获取;前两部的结论也常被直接引用。因此要把三部曲合起来评。
文明度量背后的李约瑟幽灵
作者先前就认为“东方和西方社会……文化特性并没有很大不同”;在新书里更多次重申“不存在特殊的‘西方式战争’(造就特殊利维坦)”。有的国人喜欢这样的预设,哪怕它会引出一堆难以解答的问题——这也可理解为一种意淫,因为每次解答的尝试都再次肯定了他们喜欢的预设。
假设东、西方文明真是同质的,就像两个同路人的步速、围棋手的段位那么可比,所谓李约瑟难题就不可回避了:(如果)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长期遥遥领先西方,为何近代科学却没在中国出现?莫氏指数的四方面毕竟都依赖技术;而他设计这套指数就是为了方便、更具“公信力”地做对比——显然他认为是可比的;这套译著面对的中国读者也听多了“落后就要挨打”等科学主义色彩的话语。先引述莫氏三部曲中一贯的比较结果如下:
公元83年,罗马的社会发展水平大体相当于西欧在18世纪早期的水平;汉朝……大约相当于16世纪晚期、莎士比亚开始出名时的水平;孔雀王朝……15世纪的水平。
总体上,西方从公元前1万4千年就领先东方。东方慢慢赶了上来,尤其前2000年后。公元前一千纪大部分时间西方领先优势都很小。公元前100年左右,西方再次将领先优势扩大。2世纪后同步衰退,但东方衰退浅而复兴早,到541年首次升到西方之上,但终未超过1世纪罗马的水平。东方保持领先到1773年。
为什么东方保持了一千两百年的优势还是丢了?前两部大体采用“煤炭-蒸汽机-工业革命”的解释思路(按:但中国用煤更早);新书中转而强调火器,如1594年欧洲人发明六排连续齐射战术,保持和扩大了火器优势(但中、日应用“三段击”也更早),蒸汽动力则退居二线扮演“摧毁欧洲商业最后壁垒”的角色。同样的发明为何只在欧洲起革命性作用?作者解释道,中国北方草原没有城池和移动缓慢的步兵可轰击——这却与同一页上强调“明朝也经历了多次规模更大的战争”(抗蒙、抗“倭”、援朝、平川)相矛盾。总之,每当要说明“欧洲的一连串幸运”时就显得勉强。
倘若作者很清楚“李约瑟难题”在科学史界为何多被视为伪问题,也许会作出更好的论述。借用吾师江晓原评陈方正《继承与叛逆》中的话:它的前提——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期遥遥领先于西方——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如果说有的话)和技术方面,所走的发展路径和西方大不相同……我们无法断言“向南走的人比向东走的人领先”……余英时采用了另一个比喻:不可能说“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作者试图解答的疑惑实与之同构:既然东方的利维坦曾长期强于西方,为何大英帝国和美国式世界警察却未在东方出现?这会不会更是伪问题呢?
特立独行的西式利维坦:与科学同步起伏
笔者认为确有特殊的西式利维坦,正如有特殊的西方科学;但两者都不是一直存在于地理意义上的西方。作者以黄河-长江流域和两河流域为源头地区来划分东西方文明,本为图个方便,却使“西方”地域太大而掩盖了特性。西式利维坦,简单说就是共和国,由各种议会统治;公民按所属等级行使大小不一的代表权,但内部平等。后来又出现“不论等级一人一票”的激进特例,被称为民主。
实际上作者也写到了共和国的特殊性,只是并未强调或意识到它有多特殊:
公元前73-前71年统治西西里的Gaius Verres曾开玩笑说,他在这个位置上需要干三年:第一年非法敛财让自己变成富人,第二年非法敛财让自己请得起好的律师,第三年非法敛财让自己能贿赂法官和陪审团……西塞罗在对Verres的指控中出名……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指控腐败官员成了年轻律师迅速出人头地的标准途径。
西塞罗的富有却源于他代理“谄媚谋夺老人遗产”类诉讼而受赠大笔谢礼;这等剧情常在18世纪伦敦上演,侧面印证了莫氏指数有一定可信度。律师、陪审团在治希腊罗马史的古典学者看来司空见惯,但同时期别的古文明却闻所未闻;同样陌生的“专业群体”还有议员、法学家、银行家、数学家,及哲学家——后者一大部分即今天所说的科学家。晚至19世纪,“自然哲学家”仍比新发明的“科学家”一词更受科学家欢迎。
相对于被其取代的王政,共和国是奢侈品:其公民多少都有政治权利,要认真行使难免荒废生计。民主更带来严峻挑战。若无银矿收入、奴隶劳动、盟邦贡金支持,代表十几万“雅典人民”的家长们如何能日复一日开会、判案?我们今天选个人民代表,居委会都要领误工费,正是2400多年前开创的先例。这种脆弱性使共和国或尚武或重商;但罗马介入东地中海后过于丰厚的战利品,终于摧毁了共和国的德性而被迫代以元首制:屋大维声称恢复的共和国,一件并非全然无用的外套,只在风调雨顺、来自商业利润的间接税还够维持和平时,才能阻止罗马世界滑向军人僭政乃至帝制——确实存在“西式战争”,主要特征却是以重装步兵为主的公民兵-雇佣兵制,其特性就一个字:贵。
但共和国有其用处;它们的长期存在塑造了特殊的文化惯性。阿基米德写信给国王介绍大数计数法和日心说时,语气与写给别的同胞公民无异;相比之下伽利略的口吻就近于奴颜卑膝。徐光启若无须跋涉“科举烂路”,科学成就何止于此?又,“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无需坎尼之败后元老院的坚强领导与决断,只要有一套哪怕不精巧不完善的投票表决机制,也足以避免靖康之耻。
东西方迥异的专业群体数百年劳作留下的文化遗产也大不同。古代中国没有类似《几何原本》、各种《光学》、五花八门的宪法、《民法大全》、托勒密《至大论》与《地理学》的东西,西人则没有《白虎通德论》。作者写到哥伦布时,称受过教育的欧洲人都知道地球是圆的——这是意外发现新大陆的前提;但两百年后,梅文鼎用了一年之功也未能说服张雍敬接受西方地圆说。哥伦布远航前至少细心读过5本书,其中唯一的地理类著作就是托勒密的《地理学》。
最后,东西利维坦的区别不仅表现为王政/僭政与宪政的对立,还向外扩展为不同的“世界秩序”。作者提到托勒密八世、阿塔罗斯三世出于对内战和邻国的恐惧,立遗嘱将国家赠与罗马——罗马人则激烈辩论该不该接受。这与秦汉的统一大相径庭。1世纪的罗马帝国是一个国际秩序,同时有“公民法”与“万民法”。罗马假装自己仍是城邦,以武力威慑确保所有城邦、属国、盟国间的和平,拒蛮族于境外——只要它们能履行条约义务、不危及税收,罗马无意干涉内政。这是惹人嫌的世界警察大英帝国与美帝的前身,而不是秦汉皇朝的同类。
共和国与希腊科学皆在3世纪危机后渐归沉寂,只活在典籍中。但企图否认古今共和国的联系,也像否认现代科学的希腊源头一样难。一起蛰伏四百年后,它俩都在9世纪初“枯木逢春”:希腊科学始复兴于阿拉伯人,威尼斯取得事实独立。随后兴起的一批共和国仍是城邦规模;直到全球化贸易所壮大的市民阶层使荷兰、英法等民族国家有可能和必要确立议会统治时,仍要为复兴古代政体付出惨烈代价:独立战争、内战或大革命。作者却一笔带过它们,只看作火器发展史上国王们不择手段为越来越昂贵的军队融资失败的反面教训,将所有利维坦的崩溃都归结为外因(游牧民迁徙、传染病等)——这样的史观失之偏颇。用黄仁宇的话说: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
有可能写出令人信服的世界史吗?
笔者也许过于苛责。写一部论述透彻、以理服人的世界史,不仅要通晓古典学、军事史和一般史学,还要熟知中国史,科技史“科班出身”更佳。莫氏基本忽略了科学史;引述中国史多有细节错误而由译者改正。但“全球通史”类著作多有类似问题:这简直不是凡人能干的活。莫氏三部曲至少在比较那些可比较的特征时,得出不少发人深思的成果。
作者敏锐地指出,公元后最初13个世纪,在“蛮族反建设性战争”打击下,亚欧大陆诸帝国平均面积总体在衰减,幸运纬度变成了不幸纬度;而当火器的发展最终逆转这一潮流时,欧洲却没能像亚洲那样重回“塑造更大利维坦”的建设性战争中:依然小国林立的欧洲反实现了全球扩张。西式利维坦有适合自己、随时代而异的规模尺度,打造大清那么大的共和国对它们并不是“建设性”的。只要再往前一步,作者便可用这一洞见否定前半本书里不能成立的预设:东西方利维坦都是“以暴制暴”的维和工具,没有本质区别,只有大小强弱不同。
实际上作者的第一章最末节“怎样才能变成罗马”已自我削弱了这预设。他引用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说,丹麦是一个“传说中的地方,它拥有良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它稳定、民主、和平、繁荣、包容,政治腐败程度极低”。整本书都在讲“利维坦通过战争走向丹麦”的故事,但这故事有结构性缺陷:只有西式利维坦走到了丹麦。将罗马比作古代版丹麦也不妥,因为罗马和英、美同样扮演世界警察。秩序输出者固然比秩序接受者能收获更多和平红利,却必然以输入混乱、危及国内宪政为代价。这解释了相隔两千年的罗马和美国都不时闹一阵孤立主义,英帝国干脆自我放弃。美国远非理想国,反恐战争已直接威胁到国内公民权利;而真正接近理想的丹麦,人口不过五百多万,和现代城邦一个量级。
还是借徐光启停译《几何原本》时心有不甘的话结束本文吧:续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书以俟焉。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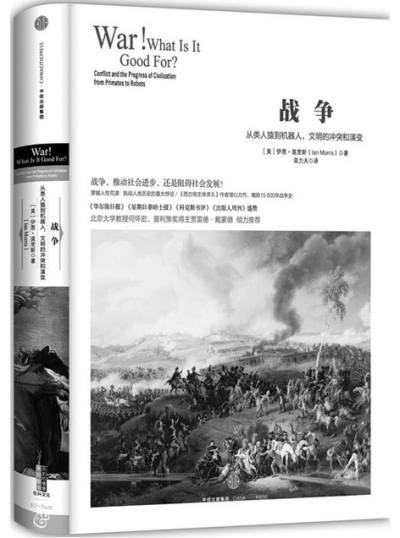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