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说里如果有诗意、温情和浪漫,可能与我的文学导师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海明威、福克纳、赫拉巴尔、库切等作家有关,我总是试图写出“妙从衷来,滋味怡然”的语言。
十年前采访陈继明时,他是“宁夏三棵树”之一,是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十年之后再访,自称为“边缘人”的陈继明已经喜欢上了在珠海并无优越感的状态。
他说,这可能正是一个作家应该有的生活。你周围的人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这个世界上好像压根没有写作这回事。但是,“有一个傻瓜在写作,”陈继明说,这是求之不得的。
“三棵树”之一的陈继明“移植”到珠海后,他的写作和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陈继明说,十年,对他来说是极大考验。他曾经有过放弃写作的念头,但是好在都挺过来了。在珠海的十年,重塑了他的精神世界,让他变得更加坚强,也让他和写作的关系更加本真。
读书报:能谈谈“三棵树”的来历么?
陈继明:写作让我没去经商、没去做官,写作始终把我摁在书桌旁,这其实是一件相当惊险的事情,貌似自然,其实惊险,所以我要衷心地感谢写作,尤其是在宁夏的写作。在宁夏,和石舒清、金殴三人赢得了“宁夏三棵树”的美誉。这个名称是敬泽先生发明的,他先有一篇文章发表在《文艺报》上,叫《两棵树,在远方》,是谈我和石舒清的,后来加上金殴,就成了“三棵树”。非常感谢李敬泽,他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我们,随后又热情洋溢地写文章推介我们,还起了“三棵树”这么好的一个名字。
读书报:2006年您从宁夏到了珠海,若以此为分界线,到珠海之后的写作风格是否发生了变化?
陈继明:空间会带来变化,时间也会带来变化。作家自己在成长,文字也会跟着成长。另外,我本人也需要变化,如果我必需始终写“邮票大的地方”,我就不写作。我对成为什么样的作家没有预期。另外,人们之所以认为我现在的写作和过去不同,是因为,我过去的写作只被外界看到了狭窄的一部分。“三棵树”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描述。我们的写作,在相当程度上,被描述了。外界会故意忽略另外的一些作品。其实,从一开始我的写作就有相当的个人性,个人主义的兴起是现代小说兴起的主要原因,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我就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并以此为最根本的写作信念。在写作中,任何大于个人的东西,我都警惕。时代,乡土,先锋,在写作中,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大于个人。我反感明显的外在的先锋模样。我不喜欢《尤里西斯》和《变形记》。卡夫卡的小说,我更喜欢《乡间的婚礼筹备》《在流放地》这样的篇什,这类小说的基本特点是,外表平和,气质先锋,人物不失真,人物是叙事的旨归。这也是我的写作理想,只可惜我做得没那么好。
读书报:您的语言很有诗意,是否之前写过诗歌?如果有过这方面的训练,为何由诗歌转向小说?
陈继明:上大学的时候,满校园都是诗人,我也是其中一员,曾经创办过油印诗刊,后来被强迫停刊,有半夜转移油印机的经历。大学毕业后,因为相信自己缺乏写诗的才华,转向写小说。写小说的过程中,其实才渐渐懂得了诗。诗,是更内在的一种品质。真正的诗是看不见的。写小说,其实也在写诗。只不过,那是一种更加隐蔽和曲折,无法目睹的过程。小说在文体上距离诗越远越好,但在内里,可能殊途同归。现在我偶尔也会写写诗,但很少发表,计划一辈子出一本诗集的,不知能不能做到。
读书报:2011年,中篇小说《北京和尚》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多家选刊转载,引起了很大反响。这部作品重提信仰的力量,也能看出您对佛教教义的理解。愿意谈谈这一中篇小说的创作背景吗?它在您的写作中是否有格外的意义?
陈继明:《北京和尚》,可能是我走向中年写作的一个标志。中年写作,非分之想少了,写作气质可能更沉静,更宽阔,更持久。这种气质,应该会转化为文字的气质。《北京和尚》其实在写一个和尚的不安。没信仰怎么都可以,一旦有了信仰,则可能事事难安。这个和尚的出和入,在佛门内外的再三摇摆,有史无前例的时代意义。而和尚的身份,以及涉及佛教的内容,都出自“写实的需要”。我对佛教一知半解,这个小说发表后,很多佛学界的朋友找我谈佛学,我总是赶紧申明,我不懂佛学,真的不懂。
读书报:我也喜欢《芳邻》中的灰宝、《圣地》中的小羽等作品中的人物,他们离我不远,那么亲近、真实,似乎触手可及。作品很短,却一波三折,尤其《圣地》悬念丛生。您的素材来自哪里?在写作之前,已经设置好故事的脉络和走向?还是顺其自然?
陈继明:灰宝是一个真人,名字都没变,几乎没有虚构。这个时代,真有这样一个人,拒绝成为富人,旁观人们的忙碌,他还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他真的在阅读《论语》和《本草纲目》。现实中的他,甚至被人们看作神经病,曾两次被派出所抓走。但是,在我的小说里,人们对他有适度的理解和礼遇。《圣地》中的小羽,虚构的成分较多,但我在大学任教,熟悉小羽这样的人物。写这个小说前,我专程去武汉做过调查。《圣地》这篇小说,设置了逐渐解开悬念的结构,是一次向通俗小说学习的尝试。
读书报:从1982年开始写作,三十多年来,您的长篇并不算多。当然长篇并不是评价作家创作成就的主要标准。我想知道的是,在很多作家急于用长篇证明自己的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陈继明:实际上我已经有三部长篇了,只是都没写好,主要是没下够功夫。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是《一人一个天堂》,讲了“文革”时期发生在某麻风院里的一个故事。这部小说一直有一些民间声誉,花城出版社每年都能卖掉许多书,不少大学的课堂上研讨过这部作品,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几年前把它列入了翻译出版计划。近期没有写长篇小说的打算。门罗获诺贝尔奖之后,必需写长篇的焦虑的确少了很多。
读书报:很喜欢您的作品中景物的铺陈以及心理描写。能谈谈您对于写作技巧的理解吗?您的文学创作,受哪些人影响较多?
陈继明:我倒是向来偏爱心理学,我认为,好小说必需有足够的心理学含量,写动作的时候,找不到心理学依据,我就会停下来不写。雷达老师曾说我的小说是“心理现实主义”,我喜欢这个说法。我的文学导师是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海明威、福克纳、赫拉巴尔、库切等作家。这些作家没有明显的先锋姿态,不装模作样,也不守旧,不陈腐,语气肯切、平和、谦逊,妙从衷来,滋味怡然,我非常愿意成为他们那样的作家。
读书报:您的小说中,尤其是散文,除了诗意、浪漫还有温情。愿意分别谈谈不同文体的创作,于您来说各自意味着什么?
陈继明:我出版过一本长篇散文《陈庄的火与土》,除此之外,很少写散文。最好的散文令我敬畏,令我缩手缩脚。常见的散文多显做作,令我反感,因噎废食,也便不写。我的小说里如果有诗意、温情和浪漫,可能与刚提到的几位导师有关,我总是试图写出“妙从衷来,滋味怡然”的语言。我曾有计划,一辈子出一本诗集,两本散文集,三本小说集,现在,小说集已经超过三本了,散文集和诗集距离目标还很远。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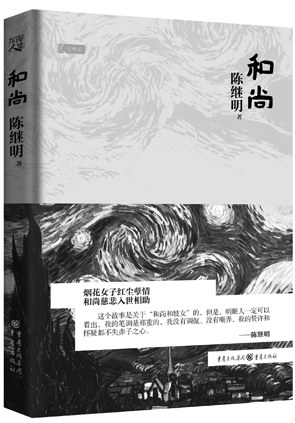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