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都到北京:傅吾康的中国大学教师经验
1946—1948年,傅吾康(Fran⁃ke,Wolfgang,1912-2007)在成都的华西大学任职,担任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研究教授。不要小看这个研究所,它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出版两份刊物,即以西方语言出版的《汉学研究》(StudiaSerica,SS)、主要以中文出版的《中国文化汇刊》(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BCS)。而按照傅吾康的说法,“我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编辑这两本杂志和为其撰稿,这也符合我本人的愿望。此外,我还有一堂课,给中文系学生讲英文汉学文献精选。不过,他们的英语知识相当贫乏,大部分学生由于受到传统的中文训练,因而很少接触现代科学思想进程与辨析的教育。”由此看来,华西大学对傅吾康的聘用,确实不是简单的聘任教师而已,而是希望能发挥所长,即他的西学知识和背景,譬如这里凸显的英语知识。不过傅吾康在成都的教学一开始并不顺利,胡隽吟则给他提了很好的建议,她这样回忆道:“因学生德文根本不通,英文程度太差,他很发愁。我劝他:在课堂如在家全说中国话时一样,可用中文讲。学术上的术语,以文字向学生请教,或校正口语字音,青年们一定很欢迎。这就是教学相长的原理。他就首次起始用中国话讲课,很成功高兴。”
虽然在国学方面或许已经登堂入室,但对于傅吾康来说,选择在成都任教两年,其实更多是一种出于家庭原因的考虑。他此前与胡隽吟(1910-1988)结婚,胡是四川人,其父亲与萧公权(1897-1981)交好,而萧氏当时在成都,正是通过萧的推荐,傅吾康获得了华西大学的职位。所以一旦北京有召唤,傅吾康自然就毫不犹豫地回到北京。在华西大学期间,傅吾康“得到了现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教研室的教授兼系主任冯至的邀请,担任他教研室里的教授职位”,这种专业变迁也是值得考察的一个有趣点。冯至当初在西南联大之际颠沛流离,连从事自己的专业德文教学都不可得,只能教教公共课,但却充满了重建一个中国德文学科的理想,所以给自己的德国友人鲍尔(Bauer,Willy)写信:“这学期开始我在为设立德国语言文学专业而奔忙。这事我已办成。你有兴趣到我们这里来吗?你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欢迎你来。不像过去在同济,我们在北京大学是不会失望的。”但可能师资的获得也并不太容易,鲍尔终究没有再次来华;这次之所以希望聘请傅吾康,也是此职位因卫德明去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而空缺。
傅吾康应聘是在1948年,“北大的教学活动于10月1日开始。我记得,我必须借助教科书教二年级的德语课,并为程度高一点的学生讲德语阅读,我们阅读《浮士德》(Faust)第一部分;第二年,在学生们的要求下读了尼采的《查拉图斯如是说》(Zarathustra),其实我自己对尼采并没有什么兴趣。此外,我自愿给郑天挺(1899-1981)担任系主任的史学系开一门课,讲明朝时期的中蒙关系,学生极少,这门课只在1948-1949年的第一学年讲授过。”看这段叙述,能感受到北大时代的傅吾康应是很愉快的,因为他其实生活在“双重精神世界”之中,一方面因为本职工作的需要,他必须借助自己的母语优势重温德文经典,譬如这里提到的《浮士德》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确实是一种深度接触德国文化经典的经验。这种选择显然与冯至的学术兴趣相关,他早在西南联大时代就在不断地讨论与浮士德相关的话题,譬如1943年的讲演《〈浮士德〉里的魔》、1944年的讲演《从〈浮士德〉里的“人造人”略论歌德的自然哲学》、1945年夏所作的《歌德与人的教育》等。他同样用诗性的语言描述尼采:“尼采是一片奇异的‘山水’,一夜的风雨,启发我们,警醒我们,而不是一条道路引我们到一座圣地。”如果想想其发言时的历史语境,就可以意识到这平静话语后的“振聋发聩”了。也就可以理解,冯至为什么要盖棺论定:“我们要随着他想,随着他动,但是不要模仿他。”冯至对歌德、尼采的兴趣不但表现在文字上,也表现在对学生的指导上,譬如闻山就回忆说:“他指点我该读哪些书,并且不用我开口借,就把他的书借给我。(后来我才知道那些书是他的宝贝,当时要找一本好书是很不容易的)于是我就从冯先生手里拿到好些世界名著,如纪德的《地粮》、尼采的《查拉杜斯屈拉如是说》和歌德、里尔克的作品,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北大的德文专业课程不是随便就可以开设的,一般多是建立在老师较为长期的坚实的阅读与研究基础之上的。1948—1950年间,其实也是冯至所主导的北大德文学科重建的重要时期,要想在此时当好德文系教授,必须跟上冯至的学术思路与视域,对付歌德、尼采这样一些德国文学史、思想史的经典人物,显然也不是一般人应付一下就可以做到的,傅吾康虽是德国人,但也会是一个相当的挑战。其实胡隽吟说了一句实话:“在北京大学所任德语课程,不是本行的中国历史这门工作,缺少兴趣。”另一方面,傅吾康毕竟是汉学家,而且是研究历史的,希望能施展所长,到历史系去兼课,这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北大历史系终究非一般的地方,能在此开坛授课,没有学术专长与人际网络的辅助都是不太可能的。郑天挺曾任北大秘书长,是历史系教授兼主任,他不但是大家人物,而且也拥有实际权力,所以能安排傅氏授课。傅吾康所讲授的明代中蒙关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但由于相对专门,所以学生不多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让我们看到汉学家的特点——即便是任职德文学科,却也不忘自己的本色当行,始终借助任何可能来推进自己的专业研究,这正是德国学者的特点。所以,1950年傅吾康选择接受汉堡大学的邀请,出任中国语言文化系主任兼教授,就是很在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德国汉学界的代际承继及其侨易经验
卫礼贤、艾锷风与傅吾康基本上正代表了德国汉学界的三个年龄层次的人,即1870、1890、1910年代出生的代际人物,而也正与中国现代学术创立的同代人差相仿佛,我们可以列举出的代表是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而就中国的德文学者来说,则大概找不到太合适的比方,如果一定要列举的话,则王国维(虽然不是专门的德文学者)、杨丙辰、冯至可以勉强提起。
卫礼贤的主要贡献集中在德译中国经典,但他对德国文化和思想的经典显然是熟悉的,就其在北大德文系时代开设的课程来看,应该说涉猎相当广泛,非有相当德国国学修养而不能为。艾锷风则初在哲学系,日后则迁地任职外文系,其学养通识也非常人可比。傅吾康则在历史系、外文系同时任职,略觉乏味。德国汉学家在中国大学德文系任教的当然还可以举出一批人,譬如洪涛生(Hundhausen, Vincenz,1878-1955)、鲁雅文(Rousselle,Er⁃win, 1890-1949)、卫德明(Wil⁃helm,Helmut, 1905-1990)等,他们都曾有过长期的留华经验,对于中国文化更是情之所钟,终生事之,习而不倦。如果将辅仁大学这类学校纳入则更多了,如谢礼士(Schier⁃litz, Ernst, 1902-1940)、鲍润生(Biallas,Franz Xaver,1878-1936)等都是。可以看出,在中国的德文学科的早期发展过程里,汉学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学术群体,他们因为娴熟汉语、了解中国、别有钟情,所以很容易进入到中国学术语境里,这是他们显而易见的优势。当然在德文学者角度来看,可能会更关注:这批以汉学为研究对象的人物,究竟对本学科能产生怎样的实质性影响?这两者难免有其出发点上的差异,但就学术本质而言,并无太根本性的不可沟通的鸿沟,关键还是在于大家如何相互理解、易地而处、取长补短、推进学术。
但无可置疑的是,以上诸君日后都以汉学研究而出名,都是颇有声名的汉学家。而我们此处考察的他们在中国大学里出任德文师资的行为,究竟能说明什么?或者更直接地问,他们究竟仅仅是为稻粱谋而临时谋职,或者多少也沾染了德文学科的资源便利,并进而能开拓出新的区宇?遗憾的是,似乎这方面的例证并不多见,卫礼贤的成就或许可以被特别举出,他尤其在讨论歌德与中国、歌德与老子、歌德与孔子等论域颇有著述;可其他汉学家在中德关系领域的研究中突出者毕竟相对较少。
那么,中国的德文学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惠于他们的在华授课经验呢?毫无疑问的是,就培养中国学生的专业能力,尤其是德语水平方面,他们显然是有功绩的;在传授学生、开拓视域、唤醒兴趣方面,他们也都各有不同成就,譬如冯至对中德文学与文化关系的兴趣就应当或多或少受到过卫礼贤的影响,因为他至少帮卫礼贤翻译过歌德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同样艾锷风虽然对那些古代器物如宝塔、家具都更感兴趣,但他对荷尔德林、凯勒等人的选择兴味,却深刻影响到中国德文学科的若干人物,季羡林的那篇本科论文是颇有价值的,而田德望对凯勒的兴趣则保持了终生。傅吾康的德文学科弟子们还有待考证,即便再普通,这种“异国师生交流”仍有其知识史的价值。但有一点感受则是,德国汉学家的德国学养似乎并不呈上升趋势,甚至相反。卫礼贤是很明显的那种对德国文化传统非常熟稔和自觉皈依的,所以他谈论歌德、康德等是有感染力的,即便在行文之中也有潜移默化的自觉;而艾锷风也能对荷尔德林别有发覆;可到了傅吾康这代就有些不同了,他虽然也在北大讲歌德、尼采,但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归总言之,我觉得汉学家的中国大学德文系任职,大致可做这几点判断:其一首先是容身之所的功用。无论是卫礼贤还是艾锷风、傅吾康等,他们都是首先希望获得一个合适的教职,以维持基本的在华生存需要,毕竟是要首先养家糊口的,所以物质生存仍是首要的,我们不能脱离资本语境的基本限制而去讨论“高大上”的问题。其二是汉学家的知识和学术兴趣的“此长彼消”可能。作为汉学家,他们的主要兴趣和目的仍在汉学专业,所以德文系的工作实际上表现出“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功用。需要注意的是,德国汉学家在中国大学的德文系里不仅教书,也还学习,他们在这里能获得些什么呢?除了面对中国学生和同事,所谓如傅吾康式的改用汉语教学的“教学相长”之外,德文系必须面对的是德国对象,对汉学家来说涉及一个“返观自我”的问题,在这里主要是如何开掘德国知识资源本身。这些汉学家都是德国人,他们本来当具有很好的德国学养,但察其实际则未必尽然。所以如何借助他者镜鉴而返观自我,其实是一个很值得细究的大问题。就我们这里涉及的个案来看,除了卫礼贤较为善于利用此点,他对康德、歌德与孔子、老子等人的思想比较,虽然还不能算很学术,但确实已经上升到比较哲学层面,而这与其注重德国资源以及北大德文系授课内容是不无关系的。可总体来说,借助这种进入新学科而提升自我的机遇把握和自觉意识仍呈下降趋势,这点在傅吾康那里显得更明显,虽然他是德国汉学这代人中的翘楚和代表,但其学术气象仍相对有限,这与其德国传统学养不足是有很大关系的。当然这么说并非否认其学术贡献,他们的学术视野总体来说还是开阔,而即便是傅吾康,他后来对海外华人的研究也是开拓出新区宇的,但这里强调的是自身的学养建构和修得的重要基础性“国学根基”。遗憾的是,越往后一代人,这种专业兴趣越是凸显,而资源增鉴意识越是趋弱。其三是一个中德文化场域与网络的形成及交互作用。在这些人物之间,彼此关系有复杂的交错。譬如卫礼贤是有留德背景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任的,而其时的德文系主任杨丙辰则是其在青岛创办的礼贤书院的学生。商承祖是北大德文系的学生,卫礼贤、杨丙辰都当过他的老师;而商承祖是傅吾康在德国上学时的汉学系教师,而此后则任中央大学的德语教授,傅吾康到重庆之后曾与其重逢。福兰阁、傅吾康是父子关系;蔡元培、商衍鎏是朋友关系;商衍鎏经由卫礼贤推荐,而被汉堡首任汉学教授福兰阁聘为中国助教;商承祖随父亲商衍鎏在汉堡居留,日后更在汉堡大学攻读了博士学位,同时在汉学系任教。中德文化之间的交互渗透和深度互动,或许正是借助这样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人际网络而落到实处的,所以大学里的代际承传其实有着太多的文化意义和符号意味!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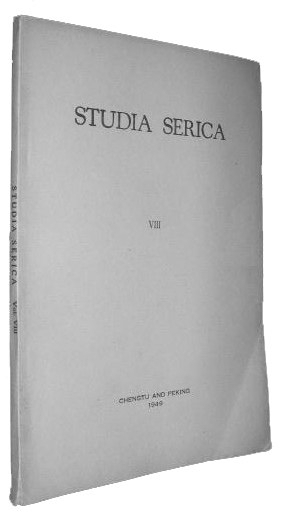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