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博物学热起来了,相比以前在历史、哲学、传播等领域中只有数理科学一枝独大来说,这是件好事。但这样的热度能够保持多久,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其实还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比起数理科学发展带来的雾霾,博物学中的野草闲花不是更令人向往吗?
江:刘华杰教授近年大力提倡博物学传统的复活和振兴,成绩斐然,可喜可贺。不消几年,冷落已久的博物学居然重新进入大众视野,出版了不少博物学方面的书籍,而且在这种努力中,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次第加入进来。是华杰提倡之功,不可没也。吴国盛教授近日在他的博客上写道:(华杰)“现在很烦对博物学、博物这些被他炒热的术语进行严格界定”,足见他也认可华杰在此事上的提倡之功。
当然,对于在现阶段是不是很需要对这些术语进行严格界定,可以见仁见智。诚如吴国盛教授所言,“作为学者,这些工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联想到十几年前,“科学文化”这个术语被我们几个“反科学文化人”在媒体上“炒热”之后,田松就提出先不必对这一术语严格界定,看她能长成什么样子再说。记得当时我们都同意他的看法,事后看来,这个策略也是有益的。所以,即使是不可避免的工作,根据情况留待下一阶段再做也未尝不可。
这本《博物学文化与编史》分为三编,其中作为理论建设的篇章,集中于第一编。特别是“博物学编史纲领”一篇,让人记忆犹新。这是五年前我们三人的对谈,当时发表时署名是“崔妮蒂”,取义于“三位一体”。这次我重温这篇长文,怀旧而外颇感自慰——原来当年我们对于这方面的理论建设,还真有点“殷勤周至”的劲头呢。
刘:出版界目前确实出现了博物学类图书的出版热潮。应该说,华杰在此当中也确实功劳很大。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地写作出版了多本一阶、二阶的博物学著作,也参与了多种博物类丛书的策划,为许多博物类图书撰写序言。在他所带的学生中,现在几乎也都是在博物学研究的领域中做其学位论文。围绕着刘华杰教授,几乎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博物学研究和传播与实践的核心群体。前些天,他在北大组织的博物学论坛,虽然与北大吴国盛教授的首届全国科学编史学论坛“撞会”,被分流了许多人,参会者却仍济济一堂,这也可以算是当下博物热的另一表现吧。
当然,这并不是说华杰是这场博物热的唯一推动者,图书出版这样的热点选题的形成,肯定还有另外一些潜在的时代和市场需求,但就现在的博物热潮来说,像华杰这样大张旗鼓、全身心投入,实践到研究并行而且做出了这么大动静的人,却几乎是唯一的。
形成了热潮,从学者的习惯来说,思考其理论基础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其实,华杰在其平日的工作中,并不缺少对博物的理论研究,他自己对博物学的热爱和执着,也自有其理论依据,否则岂不成了盲目的热情?但我觉得,你开头提及的话题,其中对所谓的“理论建设”似乎还另有更专门的特定所指,不知我这种感觉是否对?如果对的话,那么其特指的理论建设又是指什么呢?
江:就一般意义而言,理论建设当然可以包括多个方面。我的理解,华杰迄今为止在提倡博物学方面所做的理论建设,主要表现在阐述和拓展博物学在当下所能发挥的功能。先说阐述,比较显性的,比如可以支持环保的主张;比较隐性的,则有“充当科学主义的解毒剂”之类。我之所以将这些称为“阐述”,是因为这些功能或者是比较容易想到的,或者是别人也提出过。
但华杰更重要的理论建设,我觉得可以称之为对博物学在当下所能发挥的功能的“拓展”。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华杰设想了一种博物学编史纲领下的新科学史。在这种编史纲领指导下撰写的科学史,将与以往习见的科学史大大不同。这一点也是当年“崔妮蒂”对谈中的重点之一。我记得你还模仿了波兰大科幻作家莱姆采用过的“虚拟书评”之法,为一部尚未问世的、想象中在博物学编史纲领下产生的新科学史写了一篇书评。在这样的新科学史中,牛顿也许只占很小的篇幅,而另外一些人物可能被大书特书,而某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也可能获得相当可观的篇幅。
当然,这样的新科学史,华杰还没有写出来。但是,我们对此有厚望焉!我不止一次兴奋地遐想,这样一部新科学史一旦问世,将产生多方面的效应。例如,它可能遭到来自科学主义方面的强烈抨击,认为这是一部荒谬的科学史;而对这种抨击的回应及后续的争论,必将成为科学史编史学上的历史性事件。又如,一部这样的新科学史,必然具有相当的阅读娱乐性,纯粹从图书出版的角度来说,也是非常值得尝试的。
我愿意在这里负责任地宣传一下:如果华杰真写出了一部这样的新科学史,如果担心在别的出版社通不过选题审查,请将它交给我,我愿意将它纳入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主持的“ISIS文库”中,正式出版。
刘:从我个人的理解来看,你说的是一种未来的可能性,但就目前来说,华杰在博物方面的理论建设,一是还不止你说的那几点,二是我觉得写那样一部科学史,即使是他的目标,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更何况我觉得他现在主要的兴奋点,也许还不在此。即使真的要写出这样一部新的科学史,还需要解决许多基础性的问题。
例如,目前,关于博物的理解和定义,就像你在这次的对谈一开头所说的,是目前有所争议的一个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出发点和立场的问题。我注意到,在华杰的博客上,贴出了一篇前几天他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文章,其中对此是有直接回答的。他说:“谈论博物学的忽然多了起来,就有人在追问:何为博物学?针对此问题,按西方学术的传统习惯,要给出一种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揭示,要透过现象和命名找到数千年来不变的本质。一旦找到了,指给大家看:这就是博物学!我本人反对本质主义的处理方式。即使宣布找到了背后唯一的本质,意义也不大。说博物学只对应于naturalhistory,而那是西方的玩艺,于是就证明中国没有;……这样的学术没有什么吸引力。”
他还认为:“说中国古代无博物学,那么中国古代还有什么?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的学问极为丰富,但主要是博物层面的。用‘国学’很难全面代表古人的文化遗产。……从建构论的眼光看,博物学在历史上存在过,似乎也没有完全中断,每个时代都在建构不同特色的博物学。”因而我觉得华杰现在一是在带着学生以新的编史学立场重新梳理博物学的历史(所以他的书名中才会强调“编史”这一概念),而且他所采用的立场和方法,更接近于社会建构论。这正是他在博物学研究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工作。其二,是他也同样更加注重在当下“建构”和传播博物学,并关注其意义的彰显。
江:看来华杰真的很烦那些“本质主义的处理方式”。
我基本同意你的分析。不过,我还是认为理论或概念上的模糊性,至少在某些阶段是可以容忍或搁置的。这也许和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例如,当明清之际西方的天文学体系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学者中就有人产生疑问:天空中真的有“天球”这样的球体吗?真的有行星的“轨道”吗?而在中国传统天学中,这样的问题是不会被提出的。在漫长的古代时期,中国天学家只要能够和西方人一样计算出天体的位置,即可完成他们的职责。在这样的问题上,理论或概念的模糊性并不会造成困扰。
说到天学,或天文学,还有一点可以和博物学发生联系,或许值得说一说。有不少人认为,博物学“过气”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它是描述性的,缺乏精密的数理,而谈到精密的数理,天文学经常被拿来说事,比如推算出哈雷彗星的轨道之类,所以天文学被认为是精密科学的典型代表,就连只是用到天文学作为工具的星占学,居然也沾光被誉为“最古老的精密科学”。然而,如果我们尝试用博物学眼光来审视天文学,那么即使是现代天文学,也仍然有着非常“博物学”的成分——天文学家编制的各种恒星表、彗星表、星云表、类地行星表……所有这类依靠观测收集而成的表,其实在本质上都和博物学家的工作如出一辙。所以,半开玩笑地说,在那种我们上面想象中的以博物学编史纲领写成的新科学史中,编制这类星表的天文学家,或许会获得比现今的科学史中更加重要的地位呢。
我说华杰致力于拓展博物学的功能,还包括将博物学的眼光或视角,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例如本书中“公众博物学:关于那些无用而美好的事物”一文,试图向公众介绍一种博物学的眼光,用这种眼光来看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会看到一些以前被忽视或误解的事情。当然,这篇谈话录的标题稍有不妥,冒号后面的那句话,不仅冲淡了主题,而且会让读者误以为又要谈论野草闲花的审美意境了。
刘:我也基本同意你的看法。一个学理概念,就像你前面列举的那些例子一样,定义精确有精确的好处,限定模糊也有模糊的好处。在后一种情形下,可以包容更多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说,那种追求精确定义的做法,似乎也是数理科学的典型特征之一。
此外,在一种范式下的“精确”,未必就可适用于另一种范式。例如,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博物学这一问题,就像问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一样,即是一个涉及科学定义的问题,也涉及科学范式的理解问题和立场问题。如果我们在关于何为科学的问题上可以持一种多元的立场,那么在涉及博物学的问题上,为什么不能也持一种多元的立场呢?我们在现实中所关心和追求的博物学,其实未必就与历史上曾有过的博物学完全一致。
尤其是,在涉及历史研究时,这样的问题会更加突出。预设了一种博物学的定义,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就会按此定义去寻找相关的材料,当发现历史对象与此定义有所不同时,就会更加关注是因为缺失了什么因而导致这种不同(科学史中的“李约瑟问题”便有这样的倾向)。其实历史研究也还有另一种立场,即更关注研究不同文化、不同国度中博物学的差异,关注的是在这些差异的背后,实际上又存在着什么不同的东西。这样,则可以带来对于历史多样性的更充分的认识。华杰目前正带着学生做有关中国古代博物学史的研究,我希望他们也能在基于这后一种立场的历史研究中有新收获。
现在博物学热起来了,相比以前在历史、哲学、传播等领域中只有数理科学一枝独大来说,这是件好事。但这样的热度能够保持多久,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其实还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比起数理科学发展带来的雾霾,博物学中的野草闲花不是更令人向往吗?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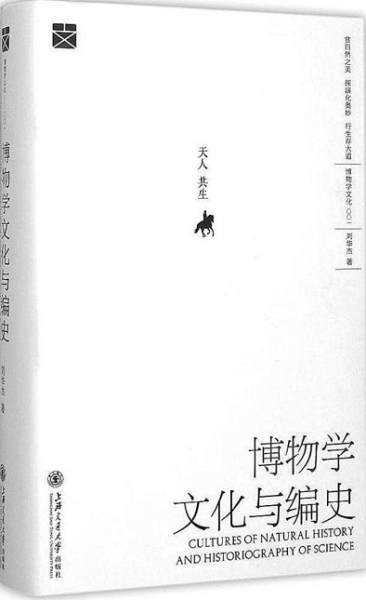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