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期,《史记》法文全译本首次在巴黎问世,本刊特邀中法出版人、译者及专家学者,回顾这套鸿篇巨制出版的前前后后。
■主持:董纯(法国《欧洲时报》资深编辑)
■嘉宾:潘立辉(巴黎友丰书局[EditionsYouFeng]创始人)
雅克·班岜诺(JacquesPimpaneau,法国作家、翻译家,《史记》法译本主要译者)
贝尔纳·布里赛(BernardBrizay,法国作家,资深记者)沈大力(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教授)
董纯:《史记》全套法译本在巴黎面世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潘立辉先生主持友丰书局出版这套巨作,想必很有感触。
潘立辉:俗话说:太阳难见。最显明的事实往往被忽略。实话讲,中国有几个人读完了《史记》?原文的长度是“全译本”最大的障碍。只翻译一篇古文都很难,何况是《史记》这样的经典巨著。在法国,《史记》的翻译与研究经过几代人接力。诸多专业词汇经过审慎、反复的推敲。左宗棠的曾孙、著名旅法学者左景权先生写过一部学术著作《司马迁与中国史学》,书中比较中国史学家司马迁与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并且专门对各种术语做了列表分析。雅克·班岜诺先生于1988年至1989年期间在友丰书局推出法译《史记》两卷本,作为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古汉语教材,又于2009年在友丰书局推出《史记·列传》译本。这三本书中都附有专门的术语索引表。像“太史公曰”这样的用语,如同西译佛经中的“如是我闻”一样,各家学者意见趋同,即采用“太史公”官职名的来源翻译。西汉武帝设史官“太史公”,汉宣帝迁“太史令”。“太史公曰”意译为:“最权威的皇家史官如是曰”。可见西方汉学家的认真态度。
在法国这样严格的法制社会,版权是要重视的。友丰书局最终组织完成《史记》全译本,经历了极为漫长、繁琐的版权申请过程。最困难的事完成了,也是最让人欣慰的事。所幸,凡涉及的机构,最后都友情转让给了友丰版权(当然,并非不付费)。各大权威学术机构,如法兰西公学(Collègede France)、巴黎大学(Sorbonne)等处的汉学研究所负责人,都明确表示希望巴黎友丰书局来组织,最终完成这项有意义的工作。这也是《史记》本身的价值和法国汉学界的重视使然。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史学的奠基性著作,其纪传体成为二十四史的文体楷模。另外,沈大力先生谈及,司马迁的史学意义重大。《史记》的史学意义,就是友丰所做工作的意义。首译者沙畹(Ed⁃ouard Chavannes)是法国乃至欧洲汉学的奠基人。他英年早逝,未完成的部分值得我们来完璧。有位老先生说,这项艰巨工程,由我们这些漂泊异乡的海外华人最终促成,意味深长。
董纯:您预想的读者,主要是哪些人?
潘立辉:主要在法国。法语是最严谨、规范、优美的西方语言,出现这样的西文译本,意义自不待言。《史记》全译本不仅在法国是第一次,在西方也是第一次。为了确保严肃性,友丰保留《史记》九卷完整版,不出简易版。《史记》法译本解决了最核心的难点,即汉语的考证阐释,最终将促进英、德、西、荷、意其他西方语言的转译,为整个西方世界敞开五彩斑斓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窗。
董纯:您能否讲讲自己在异国从事出版的经历?
潘立辉:我家祖籍广东潮州,父母在柬埔寨开了那边最大一家中药铺。我是长子,要学中文。我长期住在柬埔寨和法国,要进入当地人的圈子,说他们那儿的话,使用汉语的机会有限。1968年,我在法国巴黎大学读书,听到一些法国人在谈李白的诗,自己感到遗憾,读中文更加心切,我被中华文化深深吸引,最终萌发了开一家中文书店的想法。
我从开书店到办出版社,从卖中文书到出法文书,如同从演员到制片人,基本上实现了我心中在西方传播中华文化、加深中法文化交流的理想。创办巴黎友丰书局,确实是:“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
董纯:从1976年到现在,友丰经营了近40年。1997年您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2005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给您颁发“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13年您又荣获中国文化部、国务院新闻办和国务院侨办的“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称号。您有何体会?
潘立辉:中国有句话,“要成功,一定得有人相帮”,我的家庭很和美,太太体贴支持我,才有了今天。如果没有太太和孩子们的帮助,我的书店也不会开到今天。法国等一些国家很骄傲,都认为他们的文化好,其实中国的文化很优秀。友丰书店已经翻译、出版的法文书籍中有500多种传播中华文化的书籍。越给我奖励,压力越大,一定要做得更好。国内出版的介绍中国的书,有时候法国读者接受不了,认为是宣传品。我们在外国出版关于中国文化的典籍,需要按照他们的方式,考虑本地阅读习惯。翻译质量尤为重要,书翻得好,发展就会好。《史记》这次的完璧工作,就是由著名翻译家雅克·班岜诺先生承担的。
董纯:班岜诺教授,您承担翻译《史记》的《列传》占全书将近一半篇幅,是什么激励您投入这样艰巨的工作?
班岜诺:在众多已译成西方语言的中文著作中,司马迁的《史记》一度曾被忽略,是一件让人奇怪的事。除去一些零星散译,具有规模的《史记》译作仅出现过两部。一部是沙畹的法文译本,但译者当年因忙于其他事务,译至《世家》之后便中断,余下占全书一半篇幅的《列传》始终没能译出。另一部是华兹生(BurtonWatson)的英语译本,但它仅涉及汉朝部分。我听说美国方面在翻译全套《史记》,任务交托给整套专家班子,但译本至今尚未完成。
此项工程浩大,形成译者空白。这或许也应归咎于西方的学术倾向——把对中国文明的研究权专门保留给西方人——致使我们无法了解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过去持有何种观点,这令人十分遗憾。另一个困难是,如果译者不懂日文——这正是我的情况——翻译过程中就没有任何既存译文可以参照。不过,《史记》在中国已有许多注释十分翔实的版本,还有白话本。没这些资料作参考,我是不可能译好《史记·列传》的。
既然没有比本人更合适的同仁,我决定自己动手,完成沙畹的未竟之业。这其中,我收入了吴德明(YvesHervouet)的《司马相如列传》译文和另两位精通中国医学者翻译的《史记》第四十五篇《扁鹊仓公列传》。不才并不自认具有翻译这部巨作的资格。我不是历史学者,全无前辈沙畹那样的满腹经纶,只不过是一直对文学感兴趣而已。本人不愿接受“汉学家”的头衔,因为自己阅读中文时经常还需要借助词典。浮泛地夸耀自己是“中国通”,是我们这个时代畸形的反常现象。我所做的,仅仅是一项翻译工作,目的在于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译文没有专业人士所需求的全套注释。
我只是希望通过个人努力,帮助读者通过一部巨著在两个方面理解中国文明。第一个方面,《史记》记载了自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的整个中国历史,人们能从中得到比《左传》、《国语》和《战国策》等更早期作品更趋完整的知识。第二个方面——它也是激励我投入翻译《史记》工作的动因,在中国历史上,《列传》是许多文学作品取材的源泉。说书人、小说家、戏剧作者都从这些传记里广泛汲取创作题材。遗憾的是,对于书中所叙史实,他们没有从不同角度和更广泛的范围来审视,而是全盘照搬,后来又变成正统观点的史学家判断。因而,我在拙作《中华烈女殉情史》里,有兴致地采取了维护女权的立场,批驳那些充满儒家狭隘理念的历史学家一味斥责某些女罪犯、拒不考虑可以减轻她们罪孽的情节。
董纯:您怎样评价《史记》法译本出版的影响?
班岜诺:凡想真正了解中国文明的人,都应该知道一些有关经典,诸如《水浒》《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等出自口头传说的所谓民俗名作。像法国人从电影接触司汤达、雨果和巴尔扎克的小说一样,许多中国人以看连环画来熟悉一个民族的大众文化。可是,那些小说除了描写一个时代的民俗外,还反映出以往的人的精神面貌,影响着今人的思想。一个西方读者如果只限于看浅易读物,就不可能认识中国的历史特征及其演变。
我们应该读《四书》,尤其是孔子的《论语》和孟子的书,以及《道德经》《庄子》等最早由耶稣会士们译出的经典。但《史记》这部记载了从华夏起源到作者生活时代的中国历史,必须细读,不然我们的知识就会陷于片面。与《左传》不同,司马迁不局限于编年史的简单嬗变,他独创了一种纪传通史体例,包括三皇五帝的本纪、各朝代年表,记载昔日礼仪、音律、天文日历和贸易的八书,以及擅权的帝国世家和篇幅最大、最精彩的名流列传。《史记》的纪传体为尔后的“二十四史”继承,由本朝书写前朝事,成为一种传统。
历史在中国占有特殊地位。伦理,特别是公众伦理,乃是一个政权持久必不可少的条件。西方伦理基于宗教,而中国伦理却出自历史教训,旨在表明儒家观念的有效性。我们需要在这一基本思想启迪下,来读司马迁的《史记》。现在友丰书局有勇气出版首部用西方语言翻译的全套《史记》,的确有助于法国读者真正了解中国。
友丰书局值得人们称道。在当今出版界面临物质条件如此艰难的情势下,将吾侪《列传》译文加入沙畹译著,终于推出了司马迁全套《史记》法译本。唯愿爱好学习的读者诸君能有兴致移目此鸿篇,从容开卷。事实上,尽管《史记》全书卷帙浩繁,各章故事都是自成篇章,完全可以分开独立阅读的。
董纯:沈大力教授,《史记》法文版问世,您陆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文艺报》撰文,为何如此关切这件事?
沈大力:作为一个《史记》的普通读者,我有感于这部巨著全套法文版在巴黎问世,写下一首七言绝句:“仰天观七月流火,苍龙腾越六角国。忍辱受刑谱华章,《史记》辉映塞纳河。”以此表达一个炎黄子孙为华夏文化能向世界文坛奉献如此瑰宝的自豪。
少年时代,我读了《司马迁》一书,深为太史公逆境中发奋修成《史记》、坚韧不拔的精神所动,买来这部中国古代史学巨著线装本翻阅。当时年轻,兴趣仅在《列传》故事性强的部分上。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找到了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翻译的《史记》五卷本,与中文对照阅读了几篇,不禁为这位已故汉学家热心传播中国经典做出的可贵贡献叹服。
沙畹早年远赴中国山东登临泰山,发表法文译著《史记·封禅书》,接着埋头深入研究《史记》,着手继续翻译和注释司马迁的鸿篇巨制。他译完了《史记》前四部分,到《三王世家》为止。沙畹的《史记》法译本第一卷近半是他写的前言和引论,阐述自己对《史记》及其作者的研究。在前言里,他强调要考究《史记》完整的历史环境,说道:“只有结束此项任务,吾侪方能展现这一文学丰碑”。紧接下来的引论长达二百多页,包括“《史记》的作者”、“武帝年间”、“渊源”、“方法与评论”、“《史记》的境遇”等五章,以及一个“结论”,并附司马迁《报任安书》法译文、《班彪评司马迁》、《通鉴纲目与竹书纪年》和《史记》总目录。在“《史记》作者”一章,沙畹摆司马迁家谱,认定他是承继其父司马谈的遗志,遵循诸子百家学说撰写《史记》的。
撰写《史记》过程中,司马迁遭遇李陵事件受腐刑,他在《史记》外的《报任安书》里忿忿述及此祸殃。沙畹特地在《史记》译本引论部分附载《报任安书》,且抒己见:“司马迁首先诉说自己被定罪所受的屈枉,描述李陵投降匈奴和因此受累的情势。在信的最后部分,他表明所以没有自尽、不以死抗争的唯一情由,是想要完成已经开篇的《史记》,企望后世为自己生时所受凌辱昭雪。”在引论第二节“司马迁生平”里,沙畹提出司马迁受刑并非纯粹缘于李陵事件的论点,说:“司马迁遭祸早有一个更为致命的起因”。对此,他引用东汉卫宏《汉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沙畹依卫宏所言推断:“看来,司马迁是因为在《史记》中毁谤在位皇上和其父景帝惹怒武帝,又在李陵事件中坐举降匈奴者,终于遗患受腐刑,后来又冒死抒发忿恨。”沙畹以史为据,并不完全认同卫宏之说。但在他眼里,至少司马迁是个敢于谏诤君主的诚实史学家。
确实,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慷慨陈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在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天子淫威镇四方的封建时代,司马迁敢于据实言“武帝之过”而“犯上”,勇气甚为罕见。
董纯:您是怎样开始对《史记》法译本产生兴趣的?
沈大力:我旅居巴黎,多年找寻《史记》后一半《列传》的法语译文。在巴黎拉丁区“亲王街”友丰书局结识潘立辉先生后,我2013年得悉他在企划出版全套《史记》法文版,对之十分感兴趣。潘先生决定在沙畹已经翻译的五卷,以及法国高等研究院学术导师康德谟译的《荆燕世家第二十一》《齐悼惠王第二十二》,以及吴德明译的《司马相如列传》、阮珍欢和布里奇曼译的《扁鹊仓公列传》基础上,再请雅克·班岜诺教授续译完“七十列传”。
雅克·班岜诺是一位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尤其中国戏曲的资深学者,著作颇丰。他为人处世异常低调,最忌媒体炒作。但他却破例答应为巴黎《欧洲时报》写一篇谈自己翻译《史记》心得的文章,该文刊于《欧洲时报》2013年的《春节法文专刊》。班岜诺教授在文章里强调:“友丰书局首次用一种西方语言译出全套《史记》,乃是一个有勇气的壮举。”
董纯:您如何评价班岜诺教授的《列传》译文?
沈大力:无疑,跟沙畹一样,班岜诺教授也是受《史记》非凡价值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中所占地位的启迪,接受续译这部巨著的。他不辞劳瘁,最终在沙畹之后译完了《史记》卷帙浩繁的《列传》。我比较班岜诺教授的译文,觉得他既坚持严复倡导的“信”,又有创意。譬如,《史记》卷九十一的《黥布列传》题目,他没有将英布的绰号“黥布”音译“Qingbu”,而按法文称呼绰号的习惯,意译为“Buletatoué”,即“黥面人(英)布”,显示出此人曾经坐法黥面,展现其容貌特征。这一译法形神兼备,体现了翻译大师鸠摩罗什的“依实出华”原则。另外,我在蒙特利尔大学和艾克斯-马赛大学等讲学场合曾经指出,现存的法文版《道德经》题目“LeLivredelavoieetdelaVertu”为误译。因为中文的“道”并不是“道路”(lavoie)之意,而“德”应该是“道”之“德”。班岜诺教授将《道德经》译为“LeLivreduTaoetdesaver⁃tu”强调中文原意为“道的德”,忠实贴切。一字之立,可见译者学识。
目下,这套《史记》法文译本,在汉学全球传播上可谓“一枝独秀”,让广大读者看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全豹。这部《史记》法文全译本,无论从规模鸿大或内容丰瞻上,都是龙萨尔的《法兰西史诗》和包举一代的《圣西蒙回忆录》难以比拟的。然而,在眼下一个人人竞相争夺各类奖项的“名利场”中,我目睹两位主要完成这一业绩者,无论是主持《史记》繁重的出版业务,同时出版《春秋》《左传》和《礼记》法文版的潘立辉先生,还是继承沙畹遗业的《史记》法文译注者班岜诺教授,都无只言片语表露自己的贡献。显然,他们一心在世界上传播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觉得个人是微不足道的。
董纯:布里赛先生,据说您听到《史记》全套法译本出版,立即就去买来阅读了?
布里赛:今人能够了解汉武帝,以及起自黄帝、夏、商、周,直至汉朝的全部中国历史,归功于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史记》的作者堪比被西塞罗誉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司马迁是“中国的希罗多德”。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同他一样,是一位大旅行家,在历史著作中述说传闻和史实,呈示埃及、米底和波斯人的蛮族世界与希腊文明如何不同。同样,司马迁参观历史遗迹,记录地方轶闻,展现出汉朝时代的中国与其周边蛮夷世界之别。
司马迁总角之年饱读古文典籍,后师从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受学孔子后人习《古文尚书》。20岁时,他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后出使远及云南昆明。司马迁平生喜游,诚如大诗人李白所言:“游历即生活”。众所周知,远游之趣深植于中国文化的骨髓,被视为文化传承和文武治国之必须。父亲故世后,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兼办天文、历法、占卜、祭祀,并管理皇家图籍,记载当朝大事。太初元年,他成功定制《太初历》,代替由秦沿袭,已不适应当时国情的《颛顼历》。中国自此实行《汉历》,每年从1月开始,而不再以10月为元月。司马迁36岁上在父亲垂危时受命,继续编纂其涵盖中华民族一整个历史时期的鸿篇巨制。
董纯:据您所知,法国学术界怎样评价司马迁及其《史记》?
布里赛:在司马迁笔下,众多人物传记在《列传》里构成了《史记》中最丰富、最生动的部分。雅克·班岜诺称颂司马迁,说他“没有把历史局限于君王和战争范围,确是全世界第一位尝试全面论史的大学者”。同时,《史记》亦是一部文学杰作。女汉学家多米尼克·勒里埃弗尔评论说:“司马迁的《史记》行文精确,文献价值极高,为众所公认。尽管作者常以客观风格叙事,却浑然天成,生动活现史实。我们对中国这个时代能有如此全面的了解,完全归功于这位生性好奇、掌握充分材料、永不知疲倦的历史学者和作家。”
中国人对英雄的崇敬,使人联想起在司马迁一个多世纪后出生的普鲁塔克所著的《英杰比较列传》。法兰西学院院士雷纳·格鲁塞在其《中国及其艺术》一书中也高度评价《史记》:“对我们而言,这是一部真正的鸿篇巨制,作者将个人能掌控的时期表达得尤其科学,具有极高的价值。”
《史记》为中国后来列朝的编年史提供了一个模式。史官们都从司马迁的著作中汲取灵感,尤其是班固撰写的《汉书》。唐宋两朝的著作家们都采纳他的方法,仿效他的风格。这部巨著的影响还波及戏剧和小说,成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源泉。小说家们用其叙事艺术,烘托出栩栩如生的人物。
司马迁被视为中国的“史界鼻祖”。法国汉学家欧拉丽·斯坦什将《史记》誉为一部概括中国古代史的“杰作”,无与伦比。她指出,二十个世纪的历史因之得到辑录和编纂。结果是,现代历史学者们今朝有可能在一座举世无双的宝库里查到了解中国文明的史料。她归结说道:“它的存在显示出中国性格的一个特点:喜爱立案归档和认识书籍的价值。”
今天,巴黎友丰书局推出了九卷本《史记》全套法语译文,极为有助于法国读者更广泛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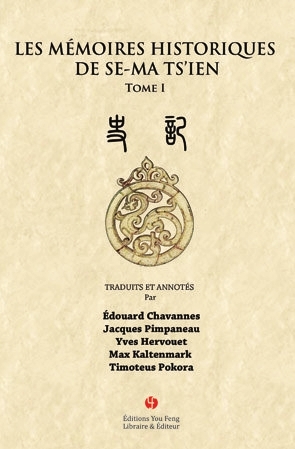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