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这是一个我们似乎与生俱来就能理解的概念。体育比赛中,我们既能看到,站在领奖台上的冠军为自己获得的荣誉洒下热泪;也能猜到,未能站上领奖台的其他人在聚光灯找不到的角落为自己失去的荣誉暗自神伤。体育比赛似乎讲究“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真到了竞技的时刻,却很少见到运动员为了友谊而放弃对“更高、更快、更强”的追求。这是因为,即使每位运动员都同样值得尊敬,但荣誉却只能给予最为优秀的选手。
体育中的竞争尚且如此激烈,那可想而知,政治中的竞争只能更甚——据说,政治的角斗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因此,在政治中讲求“友谊第一”便只能被看成笑话。但至于政治竞争所竞逐的对象究竟是什么,主流观点的看法则并非“荣誉”而是“利益”——是那“永远的利益”。据说,在政治的世界,“荣誉”恰恰是柄危险的剑。它或者会让人忘乎所以地沉浸于战争之中、为成就“伟人”这一荣誉而宁愿损害大多数人的和平;或者会让人因过度膨胀而乐于居于他人之上、而忘却了人和人之间某些更加根本的一致,从而威胁到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为此,美国著名思想史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甚至在他的经典作品《激情与利益》中梳理出了一条现代政治思想的脉络:为了政治的太平,现代政治思想家们不断试图用“利益”取代以对荣誉的热爱为首的“激情”,使“利益”成为新时代人们政治行动的动机。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论利益政治有怎样的弊端,它依然优于那种贵族式的、将荣誉置于首位的政治。
然而,当我们成功将“荣誉”从良好政治系统中分离出来的时候,政治生活就变得良好了吗?我们有时应当从简单的类比出发,然后叩问一下自己的心声:如果不论第一名还是最后一名都可以获得金牌,那么运动员还会有动力不断提高自己吗?如果我们赤裸裸地以金钱作为胜利者提高竞技能力的动力,那么你的心中会感到完全舒坦吗?进一步地,如果你所生活的社会根本不愿意为你所从事的运动付账买单、甚至将你视为异类,那么还有哪些动力能够促使你将你自己的运动坚持到底呢?更重要的是,如果社会中这些将你视为异类的人,实际是错呢?
如果在政治世界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便是莎伦·克劳斯的作品《自由主义和荣誉》所探讨的关键内容。由于重新反思了政治与荣誉之间的关系,《自由主义和荣誉》这部早在2002年即已面世的政治思想史作品,不但迄今仍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持续不断地为我们对荣誉问题这一伴随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提供着讨论的空间。
克劳斯毕业于哈佛大学政府系,是美国知名政治哲学史学者哈维·曼斯菲尔德的得意门生。写就本书时,克劳斯还只是一名博士毕业时间不长的助理教授。十余年后的今天,克劳斯已经成为了“常青藤”名校布朗大学的政治学系主任;在克劳斯来到了布朗大学之后,该校的政治理论研究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克劳斯试图在本书中告诉我们,在良好的政治体系之中,荣誉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恰恰相反,在某些时刻,只有对荣誉的热爱和追求,才能够挽救政治体系的腐化——这个时刻,便是“多数人暴政”的时刻。克劳斯指引我们去关注诸如黑人平权运动等美国历史上的重要历史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争取权利的黑人所面对的恰恰是不友好的社会;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被迫甘冒被种族主义者虐待乃至残杀的风险(也就是,被迫牺牲自己眼前的利益)而积极采取行动。他们的诉求,恰恰是和自由主义政治对权利平等的要求相一致的;但他们为了实现这些诉求而采取的行动,却得不到任何来自“利益”的激励。——这既暴露了将“利益”视为自由主义政治中最为根本的激励手段这一看法所具有的不足,也提示我们:其实我们还有着“荣誉”这一选项可选。
“荣誉”是什么?克劳斯告诉我们,它不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所强调的“德性”。“德性”有很多种,它或者要求人的品格臻于完美、或者要求人彻底将自己奉献给对其所处共同体的义务之中,而“荣誉”则只要求人在某些方面表现得突出即可、也并不要求人用对他人所负有的义务取代对自身的追求。“荣誉”也不是在现代政治思想传统中为康德所强调的“自主”,因为康德式的“自主”以人对自己的义务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而“荣誉”则完全不排斥外在的价值标准。对克劳斯来说,现代社会中的“荣誉”既是某种外在的法则(比如某个职业对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员所提出的职业道德要求),更是某种人格品质:它意味着个体希望在社会乃至自然的洪流之中掌控自己、并且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在根本上,作为人格品质,“荣誉”意味着个体的能动性:在困难面前,我相信我是个独立的人、我要掌控自己的命运、我能掌控自己的命运、而且我有勇气靠自己的行动掌控自己的命运。
将“荣誉”视为某种独立的、激励人去行动的机制,具有着重要的学理意义。克劳斯认为,当代政治思想对政治激励机制的研究,陷入了错误的二元对立之中:它或者是某种完全以自我为导向的机制(比如算计利益的理性选择、或者康德式的自我立法)、或者是某种完全利他的机制(比如对他人与对社会的义务)。然而,如我们前面已经展现的那样,完全指向自我的机制无法令个体在非常不利的状况之下勇于做出正确的行动;而完全利他的机制,在“没有永远的朋友”的政治中则根本靠不住。而“荣誉”则不然:一方面,荣誉的出发点是个体自己,它首先强调了个体对自己负有的责任、而不是对他人负有的义务;另一方面,荣誉却并非完全以自我为导向的,因为它将来自社会的价值标准当做评判荣誉的标准。这样一来,“荣誉”克服了这个二元对立的难题。
为了说清“荣誉”观念的内涵,克劳斯回归了现代政治变革的重要节点——法国大革命——之前。通过分析孟德斯鸠的荣誉观念,克劳斯抽离出了荣誉的核心要义——即使随着岁月的更迭,这些核心要义在对荣誉的反对中被埋藏了起来,它却依然岿然不动。随后,为了说清“荣誉”对现代政治的意义,克劳斯走向了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托克维尔敏锐地认识到,政治必然会从贵族政治走向平等政治;但他同时也更为敏锐地认识到,“荣誉”这一与贵族政治联系密切的概念,不但不应随着贵族政治的垮台而遭到一并抛弃、而且对维护良好的平等政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接下来,克劳斯深入到对美国政治思想与实践的反思,既为我们展现了“荣誉”所具有的局限性,也为我们揭示了“荣誉”这一看似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理念如何能够帮助人们成为具有能动性的抵抗者,而不仅仅是旧制度的维护者。
“荣誉”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生活在现代的政治制度之中,我们知道“利益”与“义务”对政治有着怎样的重要性。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加迫切地需要了解,“荣誉”这一看似陈腐而危险的概念如何能够补充“利益”与“义务”的不足,从而使得我们的政治制度变得更加平等与自由。克劳斯的《自由主义与荣誉》一书,因此是一本发人深思且有现实意义的严肃读物。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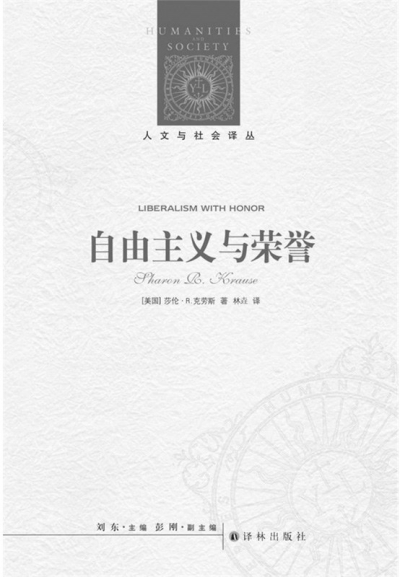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