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4月21日在巴基斯坦议会发表演讲时,引述了巴基斯坦诗人伊克巴尔上世纪30年代的诗句:“沉睡的中国人民正在觉醒,喜马拉雅山的山泉已开始沸腾”,来说明中巴两国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中,始终相互支持,相互信任。这诗句就像激越高亢的歌声,再一次跨越时空在中巴两国人民心中震响。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是巴基斯坦家喻户晓的政治家、哲学家与诗人。他于1877年11月9日出生在旁遮普一个商人家庭;在国内修完大学学业后,1905年赴欧,先后在英国与德国进修哲学与法律;1908年归国后在拉合尔国立学院教授哲学及英国文学,后弃教从事政治、哲学研究与文学创作。那时巴基斯坦还是英属印度殖民地的一部分,伊克巴尔在《国歌》一诗中这样赞美这古老的国家:“我们是它的夜莺而它是我们的花园/最高的是我们的山峰与天空相连/它是我们的哨兵与卫士/成千条河流在它的膝上嬉戏/它们使我们的花园比天堂还美丽/……希腊,埃及,罗马都已从地面上消失/可我们依然佩戴着它光辉的名称与标记”。然而他无比热爱的“花园”并不平静:“你的容貌使我哭泣/因为你的故事是一切故事中最可怖的/折花者在花园里未留下丝毫花朵的踪迹/折花者多么幸运,因为园丁们互相争斗不息……”(《苦难的图画》)。“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由于“园丁们”——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不合与争斗,让“折花者”——英国殖民者把“花”尽数折去。英国殖民者自然也利用与挑拨这种复杂的民族、宗教、种族乃至种姓的矛盾,以维持自己的统治。这让伊克巴尔痛心疾首。他除在《给旁遮普农民》等多首诗中呼吁各族人民摒弃民族与宗教纷争,团结一致,摆脱殖民统治,也在认真思考。1930年,他当选全印穆斯林联盟年会主席后,力主建立穆斯林独立国家,并多次赴伦敦出席英印谈判会议。只是他未能亲见这个愿望的实现,便于1938年4月21日病逝,但他的这一政治主张却成为巴基斯坦立国之本。印巴于1947年实现分治,1956年3月23日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终于宣告成立,实现了伊克巴尔未了的夙愿。作为哲学家,伊克巴尔有《伊斯兰宗教思想的重建》《自我的秘密》《波斯思想史》等专著。但他最大的成就还当属他毕生从事的诗歌创作。除本民族的乌尔都语外,他还精通波斯语,他用这两种语言创作了《驼队的铃声》《波斯雅歌》《杰伯列尔的羽翼》《还应该做什么》等10部诗集。印巴分治前,他被称作“印巴诗人”;分治后,他的故乡旁遮普划归巴基斯坦,他便成了地道的“巴基斯坦诗人”了。他的诗不仅在巴基斯坦,在南亚地区,包括印度、孟加拉、阿富汗、伊朗都有深远影响。
我们最初知道伊克巴尔是上世纪50年代在北大东语系求学时,那时遍及亚、非、拉美的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正风起云涌。为表示对他们的支持与增加各民族间的了解,系里各语科师生纷纷筹划将相关国家进步作品译成中文,乌尔都语师生拟定选目时,第一位就是伊克巴尔。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过邹荻帆、陈敬容译的《伊克巴尔诗选》;1977年为纪念伊克巴尔百年诞辰,又推出王家瑛译的另一选本的《伊克巴尔诗选》。而今重读,联系到几十年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他的诗自然又多了一层了解。伊克巴尔之所以被巴基斯坦人民尊为“民族的诗人”,是因为他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歌者”。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巴基斯坦等东方被压迫民族日益觉醒、奋起反抗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时代。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思想与独立意识。他把民族比作完整的躯体,而“音调铿锵的诗人”就是“民族的敏锐的眼睛”。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主张诗人“有责任鼓励人们面对一切现实问题”。他写诗,哪怕短短的仿效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体的四行诗,也都竭力将他对社会现实的锐敏体察、富有哲理的透彻分析,用灵动流畅的诗意表达出来。他的诗无一不是有筋骨,有力度,融合着整个民族的理想、信念,代表民族文化特色的佳构。
伊克巴尔不是“只须用面包和清水来满足”的鹪鹩和燕雀,他像自己笔下的鹰一样:“正义的战士在疆场拔出宝剑/旷野的风就来把它锻炼/……猛扑又退却,一边退却又再猛扑的热血奔腾”(《鹰》)。他在客居欧洲时,曾度过多少这样不眠的长夜:“你有什么苦痛在这寂寞的失眠夜/那寂静庄严的天宇,沉睡的大地/那月亮,那荒野,那些山峰峭壁/宇宙充满幸福的境地//从你的眼里流出的泪水/像发光的宝石,像星粒/你渴望着什么啊?我的心/大自然就是你的兄弟”(《孤独》)。长夜无眠,由残酷的社会现实,到浩浩天宇,他沉思着“上下求索”,从找寻大千世界万物变化的规律中,探求对人生与社会现实的认知。他没有被欧洲的繁华折服:“虽说科学技术的光辉笼罩着欧洲/实际上那里是没有生命之泉的黑窟/论建筑的美观、豪华、堂皇/巍峨的银行大楼耸立在教堂之上/表面上是交易,实际上却是赌博/一人得利,千百万人死亡……”(《在真主面前》)。他透过西欧华丽光鲜的外表,看清它所谓的“民主”:“在西方民主的背后/没有别的,只有皇帝的声音/专制魔王穿着民主的外套在舞蹈/而你把它当作自由的女神”(《西方的民主》)。他在伦敦收到儿子的信后,给他寄回一首诗,告诫他:“不要法兰西的灵巧的玻璃匠的礼品/让印度的自己的泥土塑造你的杯子、水瓶”……否则,像崇拜法国“玻璃制品”似的盲目迷信西方的“文明”,就会失去自我,“像干泥块的空壳,没有灵魂”(《被西欧弄昏头脑的人》)。同样,他还用“鲁拜”体写过一首《欧洲和叙利亚》:“叙利亚的国土给了西欧人一个先知/最纯洁的,最慈悲的,一视同仁的先知/西欧人报答给叙利亚的是/赌博和醇酒和一大群娼妓”——用更为犀利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戳穿欧洲“文明”的虚伪。诗中借用了流传在叙利亚的一则传说(即所谓“用典”):有上千年历史的大马士革东郊有一处名叫“库塔”的园林,阿拉伯文的原意是“浓荫覆盖的水草丰美之地”,茂林,清泉,春花,秋果,相传是当年人类先祖亚当、夏娃居住的“伊甸园”。当他们“偷食禁果”被上帝从那里逐出后,便一直“以田里谷物和蔬菜为食”,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他们育有一对子嗣:该隐与亚伯。亚伯即诗中所说“最纯洁”、“最慈悲”、平等待人、“一视同仁”的先知;而该隐却狭隘、自私,竟出于妒忌残忍地杀害了胞弟亚伯,犯下了《圣经》所载的“没有律法之先,罪已在世上”的第一宗命案。现今大马士革的卡辛山腰,尚有一“亚伯洞”,相传即当年的案发地。这首诗的要旨是:欧洲从叙利亚这片古老的国土上,汲取了有利于自身社会发展与繁荣的营养——文明与法理;而它所回报的却是资本主义发展与繁荣的衍生物——污秽与渣滓。虽只短短四句,像是信手拈来,却浸透着伊克巴尔这位政治家兼诗哲的锐敏、冷峻与睿智。联系到当今叙利亚乃至北非、中东的乱局,伊克巴尔的这首短诗也并不失其警示意义。
伊克巴尔就是这样一位“用雷电构筑窝巢”的雄鹰一样的时代歌者,不停息地在浩瀚无边的蓝空翱翔,时时关注各弱小民族的觉醒、奋起与抗争,不停息地唱着那激越高亢“越过大地飘向天际”的歌,给他们以支持、以鼓舞。上世纪30年代,意大利派兵入侵埃塞俄比亚,他愤怒地谴责:“欧洲的野心家不会知道/忿恨是怎样藏在埃塞俄比亚的尸身/准备要把腐朽的尸体瓜分//文化兴盛,道德下沉/我们的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竟以劫掠为生/——每条狼都在追寻着无力御侮的羊群//教堂的光辉尊荣遭到了不幸/因为罗马已经把它在市场上捣碎/哦,天父啊,锋利的脚爪才是真理”(《埃塞俄比亚》)。为了铲除那些将“利爪”奉为“真理”,“以劫掠为生”的凶恶狼,他甚至呼吁:“让人们的灵魂里发出新的火焰/号召全世界掀起一个新的革命!”(《鞑靼人的梦》)。也是上世纪30年代,伊克巴尔看到喜马拉雅山的另一侧,同巴基斯坦隔山相望的中国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如火如荼,他不禁热情洋溢地高唱起《侍酒歌》:“新时代,新天地/新的乐器奏出新乐曲/欧洲的秘密真相大白/欧洲的玻璃匠目瞪口呆/旧的政治无耻卑鄙/王公贵族大地厌弃/资本主义时代已经过去/魔术师变完戏法也已离去”。这开头就相当于中国古诗的“起兴”,接下来,便引出诗的主旨亦即习主席在巴基斯坦议会发表演讲时所引的诗句:“沉睡的中国人民正在觉醒/喜马拉雅山的山泉已开始沸腾/请给我插上爱的翅膀,让我飞舞/将我的泥胎变做萤火虫,让我飞舞/让理性从奴役下获得解放/让青年成为老年人的师长/再用那支箭射入人心/将人们心中的愿望唤醒/愿你的层天众星全保平安/愿地上夜间的祈祷者平安!”
“侍酒歌”与“酒歌”原是波斯古典诗词中的一种传统形式,诗人借主宾——劝饮者或索饮者的口,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愿。往往一盏在手,文思激荡,神驰天外,纵论古今,汪洋恣肆,灿若珠玑。著名波斯诗人贾拉鲁丁·莫拉维(1207—1273)、萨迪·设拉子依(1209—1292)、哈菲兹·设拉子依(1320—1339),都是运用这种形式的高手。如哈菲兹的《酒歌》:“请把酒给我,愿人们为你/把幸福与长寿的门儿开启/我只要把一只酒盏高擎手中/杯影中茫茫宇宙便历历分明/滥醉如泥才无意中道出真情隐意/人事不醒才脱口揭穿不宣之秘……”。对于像熟识母语乌尔都文一样熟识波斯文的伊克巴尔,波斯文化也像乌尔都文化一样融入他的血脉,运用这种形式自然同样得心应手。他常以“疯僧”、“丐僧”、“托钵僧”自喻,这首诗中他便以这种身份,以更高远的立意、更丰富的想象、更磅礴的气势和更浓郁的诗情唱出有别于先辈们在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欢宴中所唱的充满奢华与脂粉气的《侍酒歌》:“唉,侍酒!这是我丐僧的全部财富/凭借这些,我在托钵僧中最为富足/在我的商队里散尽这些财富/快散吧,让这财富得到自己的归宿”。他把“让理性从奴役下获得解放”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像“一只年老的苍鹫训教幼鹰”那般告诫青年:“生命的气息是什么?宝剑/呼谛是什么?是宝剑的利刃/呼谛就是生命的内在的奥秘/呼谛就是整个宇宙的觉醒/呼谛性喜幽思,醉狂是她的显现/她既是一滴清水,又是一片汪洋/无论是在光明中还是在黑暗里,她永远明亮/她诞生在你我之中,但却超乎你我之上/太初在她之后,永生在她之前/在她之前无界,在她之后无限/在时代的江河里漂泊游荡/经受住折磨她的惊涛骇浪/探索的道路经常曲折艰难/观察的眼光时刻变换/沉重的磐石在她手中轻而易举/高山在她的打击下落石如雨/她旅行的终点就是起点/她停留的秘密就在这里/光自月中来,火星因石燃/身在染缸中,洁身永不染/数量多少与她无关/高低前后更无牵连/太初伊始,她就卷入到斗争/坐胎成形,她在亚当的泥身中/犹如苍天在你的瞳仁里/呼谛的巢就在你的心间”。什么是“呼谛”?译者王家瑛先生说:“它是乌尔都语的音译,其原意是‘自我’,含有‘依靠自己力量’的意思,是伊克巴尔诗中一个主要哲学概念。”
伊斯兰教中除逊尼、什叶等主要教派外,还有一个叫苏菲的思想派别,他们认为重要的不在履行祈祷、朝觐等宗教仪式,而应仿效穆罕默德早年在希拉山洞潜修那样苦行净修,以期达到心灵与真主合一;主张真诚,正直,行善,济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中下层人民的愿望,在伊斯兰国家知识界与中下层人民中有广泛影响。伊克巴尔敬仰的波斯诗人萨迪·设拉子依,贾拉鲁丁·莫拉维等都是苏菲派诗人,他们的思想与宗教理念不能不对他产生重大影响。以“疯僧”、“丐僧”、“托钵僧”自喻的伊克巴尔在作品中一再提到的“呼谛”,就是倡导人们对命运、对宇宙万物的认知与把握,须强调自我、自知、自省、自励,而不要只注重表面的宗教礼仪:“何必去问智者:我的开端是什么/我所忧虑的我的结果又如何/还是把呼谛提高,使她走在个人命运之前”。并说:“一旦爱教会了人们自知/奴隶就能识破国王的奥秘”。也恰如这首《侍酒歌》结尾所说:“太初伊始,她就卷入到斗争/坐胎成形,她在亚当的泥身中/犹如苍天在你的瞳仁里/呼谛的巢就在你的心间”。伊克巴尔既善于写抒情诗,也善于写政治诗与哲理诗。他的抒情诗往带有鲜明的政治主张、浓厚的宗教理念与深邃的哲理思辨。他的这些艺术特色,都浓缩在这首《侍酒歌》中了。就是我们非穆斯林读者读起,不也同样会对诗中蕴含的哲理掩卷沉思吗?而且与前辈苏菲派诗人不同的是,即使涉及宗教理念,伊克巴尔也绝非宣扬逃避现实的遁世思想,而是旗帜鲜明地面对现实,没有丝毫的暧昧与迷茫,这更是难能可贵的。这首《侍酒歌》是伊克巴尔的代表作之一,情浓,“酒”醇,义厚,气势磅礴,一泻千里。这歌声不仅迅速地传遍印巴和南亚其他国家,而且疾风闪电般越过喜马拉雅的雪峰,把巴基斯坦人民的深厚的情谊传达给正在反帝反殖斗争中迅速觉醒的中国人民,给他们以支持、以激励。
1963年9月,我国著名诗人闻捷、袁鹰应邀访问巴基斯坦,并将他们访问期间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成一本精美的短诗集《花环》,其中《诗哲》一诗就是奉献给伊克巴尔的:“诗人伊克巴尔/呼唤巴基斯坦/蘸着满杯豪情/挥毫写下诗篇/催动人民觉醒/为着自由向前//圣哲伊克巴尔/呼唤巴基斯坦/喷出一腔热血/化作千古预言/指引人民前进/为着独立奋战……”21年后即1984年的春天,为庆祝中巴与巴中通航十周年、二十周年,著名军旅诗人纪鹏应邀访巴时,也同样去拉合尔拜谒了伊克巴尔墓。他以一名老军人的名义,对这位巴基斯坦著名的诗哲说:“中国人民自然也会记得/你那正义的呼喊和道义支援/在我们苦难深重的年代里/当我们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作战/欣喜地听到喀喇昆仑那边飞来的诗句/无比清晰地传到我们队伍耳边/于是,我们就把你的诗装进弹夹/扛起三八枪冲到杀敌的前沿……”中巴友谊源远流长,伊克巴尔这热情高亢的歌声正是这友谊的见证。自中巴两国正式建交后,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两国人民始终是休戚与共、肝胆相照、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的好伙伴、好邻居、好兄弟,我们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对此感触尤深。长期以来,两国在各领域开展的全方位互利合作,早已结出累累硕果。令我们格外兴奋的是,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为推进与落实“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率团出访时,首访国家就选定巴基斯坦。在中巴两国以2013年7月首次宣布的建设两囯经济走廊计划为龙骨,加强港口、能源、基础建设、产业合作、人文交流,构建全方位合作的新格局的庄严时刻,我们又听到伊克巴尔那“越过大地飘向天际”的歌声穿越时空,从喜马拉雅雪峰那边飞来,依旧那么激越高亢,响遏行云,鼓舞着、激励着中巴两国人民在新的征途上奋进……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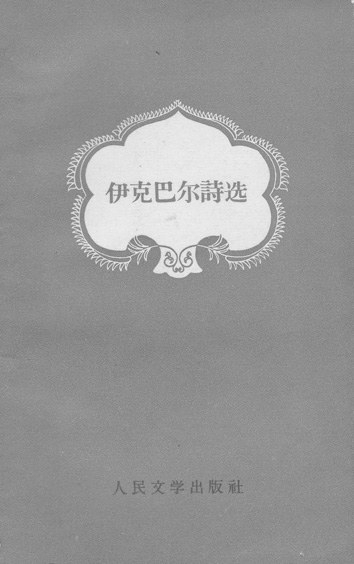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