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上海史渐成热点
对晚清民国上海史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较为人知者有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叶文心《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卢汉超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中国》、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魏斐德《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等,可以说在中国的城市史研究中,上海史处于绝对的优势位置,而对北京、成都、武汉、广州虽然也有一些知名的研究著作,但在规模、深度、影响力以及研究者的阵容方面都远远比不上对上海的研究。但这里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学术现象:上海史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晚清民国的城市史,而共和国时期上海的面目则相对模糊,这可能有史料、发表、研究的学术传统等各种因素的限制。
这些年来,对当代史脉络中的上海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包括建国初期、大饥荒时期、文革时期的上海都成为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等不同学科聚焦的对象,政治史、社会生活史乃至文化史都成为学者饶有兴趣的兴奋点,而在这个研究序列中,华东师范大学张济顺教授刚刚在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近世中国”丛书中出版的《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就是一本既具有开拓性,又带有典范性的作品。简而言之,这本积20余年之力而孜孜以求的学术作品,全面地展现了作者在当代上海史研究方面的兴趣、关怀与功力。全书的主体部分是五个研究个案,分别关注的是上海在建国初期的里弄整合、基层政治中的普选、文汇报的改造、圣约翰大学两个重要人物的生命际遇以及上海电影文化的前世今生等,就其大体而言,张济顺教授关心的主要是两个独特的群体:小市民与知识人(或者说文化资产阶级),前者的日常生活和私人领域是如何在政治改造的名义下被大幅度地改变,后者比如《文汇报》的徐铸成等、创办《西风》杂志的黄嘉德、黄嘉音兄弟作为民国上海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如何在新政权之中“洗心革面”的。
自然,如果作者仅仅是从政治或者说国家对日常生活和文化空间的置换,以及对个体性的压迫这个视角来展开其历史叙事,这个故事就会滑落到一个老生常谈的“压迫叙事”中,其打开当代上海史幽暗而复杂的面相的可能性就会严重被窄化。《远去的都市》最有价值的地方恰恰在于它挣脱了这种习以为常的历史叙事和研究视角,而在上海都市文化和底层社会的自主性方面着力,试图展现有着自身顽强的文化传统和市民生活习性的城市,在面对空前的政治压力时,它是如何通过各种方式来小心翼翼地呵护其日常生活的趣味和美感的。问题的关键是展现这种彼此交错、来回撕扯的政治与城市之间的复杂性,而《远去的都市》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揭示了在巨大的政治洪流之下、之外的那些隐秘的潜流、支流。对历史变动起实质性的支配作用的“执拗的低音”(王汎森语),也许才构成了我们认知当代历史中的上海最重要的秘密通道。
上海小市民阶层的观影趣味
民国上海的电影业是一面标志性的旗帜,而上海也是中国最早的电影业诞生地,培养了这座城市观看西方电影的日常生活习惯,而到了建国之后,这些来自好莱坞等处的西方电影,就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大毒草,变成可能侵蚀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的“精神鸦片”。依照张济顺教授的研究,当时的上海乃至中央政府想方设法将西方电影减缩到最低数量,而同时置换以从前苏联引入的电影,以及私营电影公司拍摄的作品,前者是娱乐文化,而后者更注重的是通过艺术的形式来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1950年10月,由夏衍亲自牵头的旧片审查委员会成立,计划用一年时间,“审查已映演与已入口之中外旧片”,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在落后群众的生活与思想中的影响”,并“配合进步影片的发行工作,使其转入绝对优势”。正如作者所言,中共新政权主导下的美国影片批判,由社会舆论空间转向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力空间,由道德的指责、文化和现代性的忧虑归于革命语境中的政治批判,在反帝、民族主义、阶级斗争等一系列革命话语内,好莱坞影迷也被污名化,成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个具象。
《远去的都市》指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上海小市民阶层对这种新电影并不感兴趣,而是去追逐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电影的“投影”的香港电影(抢票成为电影文化生活景观),港片《美人计》、《荣华梦》、《新婚第一夜》、《天伦情泪》、《野玫瑰》等能勾引起影迷们娱悦的记忆与想象,而当时的电影明星夏梦、石慧、陈思思等也成为青年一代的梦中情人。上海市民阶层试图通过有一定娱乐性成分的港片来找回已然陌生、却时常回旋心间的民国上海的风情与趣味。新中国才拉开帷幕,而对民国的怀旧之风已蓬然兴起。更有反讽意味的是,影迷们在那些政府大力宣传的革命红色电影如《永不消逝的电波》、《英雄虎胆》中,感兴趣或热衷于谈论的并非那些高大上的正面人物,而是那些“反面人物”。上海人记忆最深的是《英雄虎胆》中的女特务“阿兰小姐”,而不是深入虎穴的英雄曾泰,“阿兰小姐,来一个伦巴!”成为当年许多上海人茶余饭后谈论这部电影时脱口而出的一句台词。行笔至此,不禁想起笔者少年时代观看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最喜欢的人物似乎也不是一身正气的团长或傻愣愣的二排长,而是“静如处子、动若脱兔”的钻山豹以及性感迷人的四丫头。对更复杂、暧昧和混沌的历史人物的偏好难道是人性之中具有共通性的一部分?这自然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忧心忡忡,当时上海市宣传部门的调查报道显示:“从一般观众的反映及对香港片如此热衷的情况看,恐怕很少能从中真正取得教训,从而痛恨资本主义社会,热爱新社会。有的观众甚至把这种‘暴露’拿来当‘补药’吃;香港电影对青年的影响,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有些青年为电影中所描写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所迷惑、羡慕、向往,看不清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认为香港是天堂、是乐园。”
知识人的政治转向
裴宜理教授曾经在《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为方式》讨论过中国共产革命诉诸情感来进行人性改造的特质,高华教授也在《革命年代》里《“新人”的诞生》等文章中讨论过革命对人性的全新想象,接续这两位学界前辈的研究,我曾经发表过《重访中国革命:以德性为视角》一文,探讨的是中国共产革命从最初的道德真诚如何逐步发生异化的。从新政权对1950年代上海文化出版业和市民阶层的改造来看,前者所形成的具有独立和民间意味的文化形态,以及后者在各种政治运动之中仍旧顽强存留的生活趣味,都说明人性中天然蕴含的两极性(神性与魔性或者说神圣性与世俗性)即使在最极端的年代,也不可能完全被定点清除。这种韧性的存在,被作者称之为底层社会的自主性,以及晚清民国上海文化所形成的习性。这或许在今天已经成为人尽皆知的常识,可是在1950年代的中国上海,这种“自主性”或者“习性”却是革命改造尚未成功甚至失败的标志。
比如1950年代初期上海的《文汇报》在文宣系统的指示下三次改版,试图将自身改造成为符合政府要求的私营报纸,可是每次上级机关以及《文汇报》自身领导层都不满意。据作者研究,当时的领导机关认为,《文汇报》的编辑方针还是“强调‘市民路线’,强调‘趣味化’、‘人情味’,以‘四大连载’吸引读者,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庸俗趣味去影响读者”,“资本主义办报思想,曾严重地支配着《文汇报》每一个工作人员”,“今天还没有肃清”。《远去的都市》一书,将徐铸成、严宝礼等人在1950年代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处境、应对、思想变动和心情都细腻地呈现了出来,老交情与新上级、公义与私谊等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脉络,在政治文化的严丝合缝之中是如何隐秘运作的,也被深度地揭示了出来。正如作者所引述的作为党代表的陈虞孙对严宝礼的警示性的忠告所呈现的那样:“私人交情是从人民利益作基础的,如果你损害了人民利益为人民群众所唾弃,这所谓私交便失去了基础,就无私交可言。你过去对革命是有一些贡献的。因此,政府照顾你,人民尊重你。你现在已有了一定的声名和地位。但如果你在文汇事业上做了损害人民利益的事,不立即改过来而还要继续向错误的路上发展,那么你将在文汇事业上弄得身败名裂,谁也救不了你。”即此可见,在前革命政治年代,政治与人情是可以二水分流的,政治是血雨腥风撕破脸皮,而人情是静水流深雪中送炭,这从李鸿章在戊戌之后对梁启超的期许与宽慰,胡适、陈独秀与李大钊三人的聚散离合,甚至从国民政府中层官员陈克文对战后汪精卫眷属的照应都可以窥知一二。可是到了革命年代,这种人情被系统性地压抑和自我压抑,阶级话语成为主导型的政治思维,所谓亲不亲,阶级分,人情就成为政治的附庸,甚至可有可无的点缀。在晚清民国,私营报刊业主要依托主笔、经理等核心成员的资源、声望、眼光与人脉等来运作,而到了新政权初期,这些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这其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所谓民营报刊的代表性问题:民国时期的《文汇报》《大公报》等可以声称代表民间和人民的声音来批评国民政府,而到了人民政府的时代,党报刊本来就被定性为人民的报刊,《文汇报》等还能像原来那样声称吗?!这正如曾经是私营大报《大公报》名记者,后来成为上海市军管会文教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范长江在第一次新闻出版界座谈会上所言:“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有些私营的文化出版事业中,是曾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人民的,是应当称为‘民’营,或属于‘民间’的,但在人民政权下,政权的本身是代表人民的,这里只有公营和私营之分,不再是‘官方’与‘民间’的区别。”这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张济顺教授对出身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黄嘉德、黄嘉音兄弟的人生与事业专辟一章,将这对在民国时期创办《西风》杂志绍介美国文化和西方文明,而成功地塑造了上海的中产阶层的美学趣味的兄弟的悲剧性一生展露无遗。哥哥黄嘉德曾在圣约翰学习、任教近24年,从小在福建一个基督教家庭成长的他,最早的精神世界都是由基督教信仰所滋养的,而民国上海教会大学自由、多元和开放的气味,又滋养着他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战后中国的迷津之中,嘉德、嘉音创办的《西风》杂志刻意保持着一种去政治化的纯学术、纯文化立场,不卷入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论战之中,而立足于传播西方文明与观念。可是,在民国时期成为上海文化底色的“西方色彩”,到了1950年代初期的中国,却成为一种必须不断从思想版图和历史记忆深处清洗掉的污点,当初的传播者就成为“原罪”的承担者。嘉德谨言慎行,顺从了这种无比巨大的体制化和政治化的逻辑,将自己作为一个《西风》编辑和基督徒的过去贬损得一无是处来寻觅安身立命之所在。饶有意味的是,张济顺教授并不认为嘉德的转变仅仅是一种政治压力下的自我污损或明哲保身,她从嘉德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对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美国文化的娱乐化的批评,以及强烈的“中国认同”,尤其是嘉德自大学时代起对于基督教信仰的怀疑等各种历史人物的具体性出发,归结出“在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教育、学术被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1950年代,嘉德确实面临着有形无形的压力。但这并不表示嘉德的政治转向出于违心。他有真诚接受改造的愿望,在他的思想和精神世界里,确有与异化校园合拍的部分。”在杨奎松教授的专书《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对张东荪、王芸生和潘光旦的评述里也有类似的分析。简而言之,大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接纳,并非是政治巨压之下的服从或者阳奉阴违的表演,而是发自内心的认同,这与近代以来中国读书人对民族国家危机的切身感受、以及对一个自由、独立的祖国的想象有关,它未必是理性的自觉,而隐含着一种情感上的自愿成分。
里弄居民并非天然具有无产者的品质
更剧烈的变迁发生在上海的里弄所表征的底层社会。晚清民国所构成的上海是一个华洋杂处、三教九流都可以栖身的口岸城市,不同区域的外来移民带来了完全不同的语言、习俗、价值观与社群生活方式等,在一个资源高度稀缺而人口极为密集的大都市,生存竞争之激烈堪比霍布斯所谓的丛林社会。不过,上海的魅力或者说魔性也恰恰是从这种含混性或者“杂乱性”中间生长出来。混乱既是秩序和法则的敌人,同时也可能是创造力的情人。而在1950年代新政权的视野里,混乱象征着危险与威胁,而与之关联的底层社会则是必须被驯服的。张济顺教授指出,在异质文化交织和多种社会生态共存的里弄空间内,居民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多元。社会环境杂乱,邻里之间、居民与里弄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这种不确定密切相关的就是,1950年代初期的上海存在一个较大的非单位(非体制)人群,比如三轮车夫人群就是如此。
依照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论预设,这个人群天然就应该具备无产阶级的品质,在1950年代上海政府以居委会替代国民政府保甲制的过程中,这批底层的无产者相当一部分成功上位,成为居委会的各种负责人。但是,正如张济顺所指出的那样:“这个群体虽然是新政权可依靠的‘城市贫民’,但他们往往是行会、同乡、帮派三位一体的代表,甚至是恶势力的帮凶。”从作者引述的当时上海里弄工委办公室整理的材料来看,当时的里弄居民并没有政府所期待的无产者的品质,而是陷溺在日常生活中的赌博、磨洋工、婚外情、打架斗殴等各种境地之中,与无产阶级应有的社会形象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这就对阶级斗争的理论构成了挑战。张济顺教授下述这段评论可谓《远去的都市》核心论旨之一:“在1950年代上半期的上海里弄,中共新政权遭遇了大都市社会历史遗产与现实的严峻挑战。尽管新的执政者竭尽全力地与1949年之前的‘旧中国’与‘旧上海’做彻底的决裂,按照既定的意识形态重构自己的社会基础,但上海里弄社会的积淀之深、关系之复杂、利益之多元,远远超出新执政者最初的估计与想象。尤其是阶级理论与现实之间形成了持续的张力,理论上的依靠者——里弄空间中的非单位人实际往往靠不住:阶级路线也不那么畅通无阻,最终要被消灭者,尽管政治上名誉扫地,却从新民主主义《共同纲领》与统战中得到优待,仍居于社会生活的上层,与新主政者若即若离。”叶文心在《上海繁华》中也提出了同样的一个问题:新上海与旧上海之间是彻底的断裂关系,还是藕断丝连的彼此交错关系?其实质也就是,晚清民国所形成的上海文化与市民社会,在1950年代究竟是被系统地置换和重组了,还是其精神实质以另一种形式顽强地延续着?我想,这是张济顺教授全书最关切的议题:面对革命政治文化的体制化压力,上海地方文化和民间社会是被动地服从,还是其实在消极地抗争,或者隐蔽地自我延续?
诚然,对上海底层社会的改造,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回应经历过一系列战乱与失序的市民群体对新秩序的渴求,而居委会主办的居民读报组、青年政治学习班、妇女儿童识字班以及夜校等各类政治教育组织,对于提高居民的文化素养和政治意识,也存在不容抹煞的积极作用。我们在裴宜理所描述的1920年代初期安源煤矿工人罢工的组织过程里,就可以管窥到共产革命的文化政治色彩。张济顺教授指出:“对于‘翻身解放’的渴望与‘当家作主’的憧憬极大地激发起底层社会参与政治的热情。这种来自里弄社会的能动回应,不仅体现了中共执政的国家目标与社会愿景之相互匹配,而且表征着中国革命的正当性正在转化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一方面是革命的正当性转化为执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是治理的有效性在强化执政的正当性,两者互为奥援,形成了1950年代上海治理与改造上的奇迹。依照陈毅在解放军入城三年之后的宣称就是:“上海已由一个依赖帝国主义经济而生存的重要城市,改变为不依赖帝国主义而独立发展的城市;已由一个为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服务的城市,变成为人民、为生产服务的城市了。上海已大大清除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遗留下来的污毒,开始走上正常而健康的发展道路。”抛开这种论述里的意识形态不论,陈毅所谈的确实是涉及到从晚清民国上海到共和国时期上海的一个结构性的功能转换,也就是上海从一个消费主导性的大都市,向一个生产主导型的大城市转变。在这种转型过程之中,依照上海学者周武的研究,原来支撑上海文化的三驾马车(都市文化、欧美文化和革命文化)就被拦腰斩断,只留下革命文化,而在塑造新秩序的过程之中,被认为藏污纳垢的上海底层社会首当其冲,里弄民众被充分地动员起来做检举工作,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天罗地网。正如张济顺教授所指出的那样:“遍及里弄与深入邻里家庭的大规模检举、告密与大义灭亲之举是政府大力提倡、鼓励的结果,理所当然地受到执政者充分的肯定。不仅如此,检举揭发行为在里弄整顿之后延续,成为国家掌控基层社会的长效机制。”人性之恶成为推动城市基层治理的帮手,但释放出来的魔鬼要重新收回到潘多拉魔盒就没那么容易,这种政治控制方式造成的历史阴影至今仍旧笼罩着中国社会。
读《远去的都市》最感慨的是作者面对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时那一份“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一方面,是试图理解新政权的文化运作和基层政治的历史逻辑,并正视这种治理方式给百废待兴的中国带来的新气象与新秩序;另一方面,是探测到在政治与社会历史深处的脉动,这既有底层社会的历史惯性,也有上海作为一个海纳百川的多元文化空间的自主性。这两者之间构成的彼此交缠又相互冲抵的关系网络,就成为张济顺教授建构她的“1950年代上海”的逻辑起点与基本架构。而更让普通读者着迷的是,作为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新式小学上海梅溪学堂创办人张焕纶的后人(自安徽来沪的少年胡适曾在此校求学一年),张济顺教授可谓出身书香门第,这使得她在讨论圣约翰大学的黄氏兄弟、徐铸成、严宝礼主持的《文汇报》等触及文化生活的主题时鞭辟入里游刃有余,而基于对中国革命的普通参与者以及上海作为中国最具有市民文化气味的城市的深刻理解,《远去的都市》同时也对普通人的生活(包括里弄改造与选举、观看电影等)在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中的变化给予了充分的阐述。因此可以说,《远去的都市》是一本兼具文化贵族视角与平民情怀的史学著作,它对作者的意义绝非仅仅是一本学术著作而已,正如作者在“致谢”中所言:“作为一个上海老城厢张家的后代,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1950年代的上海对我来说绝不是一段冷冰冰的历史。”它是作者向曾经生活在上海这方土地上的市民、亲人和历史致敬的方式之一,它也是一本鉴往知今照亮未来的“上海之书”。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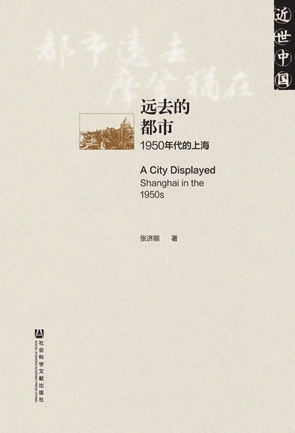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