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上月,《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一书由九州出版社正式出版。发生于1949年底的苏联伯力城细菌战犯审判,与纽伦堡审判(1945-1946)和东京审判(1946-1948)在时间和逻辑上具有紧密关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系列战犯审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审判尤其针对东京审判严重遗漏的日军细菌战罪行,进行了集中而公开的审理,不仅首次全面揭示了日军第731、第100等特种部队令人发指、但又极为隐秘的细菌战和活体实验罪行,更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公开审判,为战后国际刑事司法领域的细菌战争审判开辟先河,具有标志性意义。
这场审判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强力主导下,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了日军当年进行活体试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罪行,并判处山田乙三、梶冢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柄泽十三夫、西俊英、尾上正男、佐藤俊二、平樱全作、三友一男、菊地则光、久留岛祐司等12名被告2-25年的禁闭刑期,在国际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自1949年12月25日,随着苏联滨海军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前日本军人准备和使用细菌战武器”的罪行,便极大吸引了世界媒体的目光。而在12月30日做出庄严判决后,围绕这场审判发生的故事并未完结。本文谨从以下三个方面略作揭示。
尴尬的美国
二战结束后,在获取731等细菌战部队实验和情报资料、掌控相关责任人员方面,美、苏之间存在隐形竞争关系。这一点,早为当时敏锐的媒体记者揣摩清楚。1946年初,《纽约时报》《太平洋星条旗报》《赤旗报》等媒体纷纷对日军在中国东北的细菌武器实验,以及原细菌战队员回日后的潜藏情况进行披露。但与美国关系最为密切的《纽约时报》《太平洋星条旗报》这方面的报道很快便受到“遏制”,乃至1947—1948年间——也就是东京审判进行期间——对细菌战的问题一直保持沉默。有的学者研究发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的28名日本战犯中,半数以上与细菌战罪行存在关联,甚至直接参与其中;负责起诉的检察官中也至少有6人明知日本的细菌战罪行,却对此保持了沉默,因而很怀疑“这中间有一个保持沉默的真正的阴谋”。([美]谢尔顿·H·哈里斯:《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5页)很明显,当时有能力策划和操控这场阴谋的,只能是事实上主导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麦克阿瑟将军及其背后的美国政府。
面对美国政府以免于起诉换取日军细菌战情报的隐秘计划,中国和苏联政府虽曾尝试对抗,但显然都不成功。1946年8月中国南京市地方检察院曾将调查所得日本“多摩”部队的细菌战材料提交东京军事法庭,但在一些人为操纵下,并没引起特别注意,尤其不见有后续追诉行动。苏联政府在侦缉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的过程中,也明显落后美国特工的节奏,节节失利。虽曾押送两名日本细菌战犯到东京接受审讯,欲将日军细菌战、活体实验等罪行加以坐实,但最终也没能突破阻力,使细菌战犯审判列入东京审判的议程。
有鉴于此,苏联政府一改东京审判时的被动情势,在伯力城审判中对美国的阴谋进行了近乎直白的揭露。比如在“国家公诉人演词”里面特别提及,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曾收到过南京市法院检察官书面报告,“这一充分揭破日本当权集团方面在试验细菌武器时用活人来进行万恶实验的材料,交给了美国主要控告人肯南。但大概是有什么重要人物力求妨碍揭破日本军阀骇人听闻的罪行,所以关于‘多摩’部队活动以及关于石井部队内所作同样试验的文件,终于没有提交给国际法庭”(本书第360页)。这里谈到“重要人物”时故作含混,却又直接指明该项材料曾经交给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长的美国人肯南(现译作季南,Joseph Keen-an),将强烈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美国。可见,苏联通过这场伯力城审判,不仅在于全面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更在于攻击美国表里不一的行径,兼发泄东京审判过程中所积蓄起来的怨气,欲图扳回一城。此外,苏联在伯力城审判进行过程中,不仅采用公开审判形式,准许一些民众到场参观,更借用塔斯社等国家媒体向全世界发布相关消息。而在审判完成后,又很快将审判资料汇编成书,并翻译中、日、英、德等多国文字,全面揭露日本细菌战罪行。
面对伯力城审判所揭露的日本细菌战、活体试验等方面的累累罪行,美国政府其实是最尴尬的,因为他们不仅无法利用业已掌控在手的原731、100等部队人员(如石井四郎、北野政次郎等)站出来公开予以反驳——其实也无法反驳;更无法否认在东京审判期间,曾经接到中国和苏联关于日本细菌战罪行报告的事实。窘境之下,美国政府只能开动宣传机器,重点揭批苏联伯力城审判的法律程序和实体瑕疵,尤其特别强调这完全是冷战对手——苏联政府所操控的一场政治审判,或政治表演;因而在逻辑上,这场审判所揭示的内容绝不可信。其实,在苏联的伯力城审判前后,这便是美国政府一贯的反宣传策略。
在“冷战”敌对状态下,尤其在特别强调客观证据的美国法律文化背景下,这种政治反宣传策略居然获得了巨大成功,以致美国民众数十年间对于日本细菌战罪行懵无所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一位美国记者偶然在美马里兰州的底特里克营军事档案馆里发现了大量当年731部队的细菌实验原始材料,并撰文进行报道,由此揭破美国当年与日本细菌战犯进行秘密交易的内幕。面对这批数量庞大的日军细菌战原始材料,美国政府再冠冕堂皇的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其后,随着美国政府相关档案逐步解密,人们更是发现:美国当时以极低的金钱成本便从石井四郎等人手中获取了这批罪恶资料,数位昔日当事者都承认这是一件十分划得来的“交易”(Deal)。美国政府获取这批日本细菌战资料的成本也许是极低廉的,然从较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美国政府所真正失去的,却是一个超级大国一贯标榜的道义形象。
中国的反应
中国方面对于伯力城审判的态度根由,可以追溯至抗战胜利前后。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曾经耀武扬威的关东军很快瓦解。仅仅5天后(即8月14日),日本天皇便宣布无条件投降。面对如此快速的投降节奏,一方面,日本关东军纷纷放弃抵抗,缴械投降,苏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另一方面,不管是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边区政府,在如何接收东北的问题上均无充分准备。国民政府方面的因应举措尤属乖张,蒋介石因对原东北军将领存有戒心,指派对于东北事务十分隔膜的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营主任,并由张嘉璈协助,负责接收东北和对苏谈判事宜。但熊式辉、张嘉璈等人很快发现,苏方对于中国东北不仅有过多的利益诉求,更有甚者,表面上答应由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实际上百般拖延甚至阻挠国民政府军政人员的进驻,明里暗里将一些地方“移交”给共产党的地方武装。
自国共双方言,对于东北的战略争夺,在抗战结束前便已开始。日本投降、苏联占领中国东北后,更是加紧了你争我夺,甚至兵戎相见。战后东北这种独特的临战状况,不仅发生于苏军占领时期;苏军撤退后,更是愈演愈烈。直至1948年底辽沈战役结束,方以共军的绝对胜利告一段落。在苏军占领时期,一方面大批日军战俘早为苏军俘获,完全在其掌控之下;另一方面,日军731、100等特种细菌战部队所在的哈尔滨、长春等地被苏军占据,久不撤退。所以,不管是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军队,即便当时对日军的细菌战罪行有所了解,若欲进行调查取证,事实上皆有所不能。而在苏军撤退后,国共双方更是汲汲于内战中决雌雄,无暇顾及日本细菌战、活体实验等罪行调查,虽然令人感到遗憾,但在当时势所难免。
再从时间上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方告成立,12月25日苏联方面即开始在伯力城正式庭审细菌战犯。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新政权尚且立足未稳,若因其未能参加这场历史审判而苛责之,显然也有失公允。从事实上看,毛泽东于1949年12月至次年2月访问苏联,也就是在此期间,苏联进行了伯力城审判。由此可以推知,对于这场历史性细菌战审判,中国的新生政权显然是知情者;但具体知情到何种程度,是否有所参与,目前由于文献不足,无从悬揣。我们知道的是,伯力城审判期间,中国最主要的官方报纸——《新华日报》,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报道,并往往花费大量篇幅予以赞扬,甚至请曾经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方法官梅汝璈出面撰文,借以表达中国人民对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极大愤慨。不言而喻,这些报道本身即代表了当时中国政府的积极反应。客观上,通过这些报道宣传,不仅将昔日侵华日军的细菌战罪行传遍中华大地,激起亿万人民的公愤,更将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细菌战争的态度向全世界作了郑重宣示。
另外,同样是在毛泽东访苏期间,苏方主动提出解送一批日本战犯到中国,交由中国政府审判。1950年7月19日,苏联将969名日本战犯正式移交中国,关押于新成立的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然而,此时中朝边境的战火愈烧愈烈,新中国政府转而投入抗美援朝战争当中,原计划不久即将举行的战犯审判则被耽搁下来。及至朝鲜战争结束,195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在辽宁沈阳和山西太原两地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先后对武步六藏、古海忠之、斋藤美夫等45名在押战犯(包括羁押于太原战犯管理所者及伪满官员)提起公诉,由此拉开新中国公开审判战犯的序幕。
这一系列战犯审判活动明显受到伯力城细菌战审判的深刻影响。仅以其中关于日本战犯的审判为例:首先,所审判的战犯绝大部分来自当年苏军在中国东北俘获的日本战俘。且在审判时机、审判对象选择上,与苏联的伯力城审判存在逻辑关联,同属战后系列日本战犯审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伯力城审判成为中国战犯审判的样板,据当时担任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的袁光将军回忆,中国的战犯审判就是仿照苏联伯力城审判而进行的。再次,苏联伯力城审判关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调查和审判记录,作为证据材料,甚至被直接应用到中国对于另一名细菌战犯(榊原秀夫)的审判当中,足以说明在两场审判间具有密切的逻辑和事实关联。
不过中国对于苏联老大哥的既成模式也有突破。例如沈阳特别军事法庭第一场审判的战犯人数共28名,超过伯力城审判战犯数量的一倍还多,而与日本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起诉的战犯数量完全一致,侧面体现出中国战犯审判之“独具匠心”。又如在苏联伯力城审判结束时,参照苏联当时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告知各被告有权在72小时内向苏联最高法院军法处提出抗告。当然,抗告之后的结果仍是维持原判。这种完全形式化赋予被告的抗告权,在中国的战犯审判过程中则无一言提及,只是在判决书中明确告知各位被告,特别军事法庭的一审判决即为终审判决。揆其缘由,略有三点:其一,当时中国没有制定和颁布专门的刑事诉讼法律,也就无法援引参照;其二,可能更为主要的是,当时中国对于战犯的改造极为成功,绝大多数战犯在正式审判前对昔日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即已深刻悔罪,洗心革面;其三,中国对于战犯的遴选以及刑罚判决皆极宽大,各位被告均当庭表示认罪伏法,甚至有人主动请求法官从重判决。因而,也就无须在形式上徒然增加一个“抗告”程序。
再者,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待遇明显不同于苏联的苦役折磨,而是在生活上给予优待照顾。这种做法不仅体现了“以德服人”的中华传统美德,更是当时主政者周恩来总理“以德报怨”政策的典型注解。后来的事实表明,中国的战犯改造虽然花费成本无数,但对战犯的心灵改造取得巨大成功,远远超出苏联的冷酷铁血政策。上千名经过中国改造的日本战犯归国后,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始,便在促进日本民间社会反省战争历史、推动中日和平交往等方面一直起到积极的建设作用。及至近年,这些人虽然多数垂垂老矣,甚至先后辞世,但在中国细菌战和慰安妇受害者赴日索赔等活动中仍是不可忽视的外援力量。
战犯的结局
对于伯力城审判12名日本战犯的人生结局,有必要略作交代。以往因为研究不足、材料有限,国内很多人不知道这些战犯的最终下场,甚至有的媒体以讹传讹。比如有的网站曾介绍说,日本关东军末任司令长官山田乙三大将在伯力审判后,于1950年7月由苏联移交中国,最终释放回日本。其实,这根本是无稽之谈。
此前笔者有幸读到昔日伯力城受审战犯三友一男的回忆录《细菌战の罪》(泰流社,1987年),其中不仅详细记载了他在东北从军和被苏军俘虏的经过,还特别记录了当年伯力城审判的经历,以及数年之后与其他战犯一道自苏联归国的过程。根据该人所记,1949年底接到伯力城审判的判决书后,被告们曾向苏联最高法院军法处进行抗告,最终不出意料地被驳回,仍然维持了原判。
尽管苏联政府做出如此裁决,但随后并没有将各位细菌战犯送回劳改营禁闭,而是将他们连同其他未受审的日本军士共约200人,沿着铁路,从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城)押送至伊万诺沃市郊外的一个乡村,羁押在那里的第四十八将官收容所。伊万诺沃是苏联著名的纺织产地,十月革命后,苏联将该市郊外帝俄时代遗留下来的地主农庄加以利用,改为劳动者休养所;二战结束后,则改作“将官收容所”,用于“收容”一些军衔较高的战犯。
据三友一男回忆,在第四十八将官收容所期间,他们的生活待遇有明显改善,不仅摆脱了原来的劳役折磨,活动较为自由,而且该收容所设施比较齐全,甚至还可吟诗作文、娱乐消遣。来至此地不久,原本判刑较轻的菊地则光(2年)和久留岛祐司(3年)二人因为服刑期满,先后被释放回国;而在1952年夏,高桥隆笃(25年)罹患脑溢血,横死在收容所里。
自1953年后,日本与苏联不断进行交涉,促其遣返被俘人员。经过多次艰难交涉,1956年取得重大进展,羁押日俘被大规模遣返。山田乙三大将因为年事较高,于当年6月9日即获遣返。余下7名伯力城受审战犯(梶冢隆二、川岛清、佐藤俊二、西俊英、柄泽十三夫、尾上正男、平樱全作、三友一男)原定当年12月26日一同遣返回国。然而不知何故,当年11月末,柄泽十三夫在洗澡间内自缢身亡。结果,12月26日只有梶冢隆二、川岛清等6名细菌战犯与其他日俘一起,先是乘坐火车返回伯力城,再改乘日本专门派来迎接的兴安丸号商船回国。三天后,在京都的舞鹤港登陆。至此,昔日在伯力城受审的12名日本细菌战犯除高桥隆笃和柄泽十三夫客死异乡外,其余10人均被苏联直接遣返,得以在故乡岛国了其残生。
另在三友一男的回忆文字里,我们可以明显感到,他对苏联在西伯利亚劳役折磨日本战俘之举严重不满。对于伯力城审判,他则特别强调,在苏联主导下的这场审判俨然是战胜者对于战败者的裁判,很难说是公平的。不仅如此,对于伯力城审判所揭露的日本731部队、100部队的细菌战罪行,他也表示了异议,认为夸张过度,有失本真。相比之下,当年经过中国战犯管理所改造的千余名日本战犯,则不仅对中国优待俘虏政策和极为宽容的判决结果感同再造;更主要的,他们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有了认识,对昔日犯下的滔天罪行均表示深刻忏悔,真正“从灵魂深处发生革命”。因此,从长远的历史眼光看,中国的战犯改造政策不无过人之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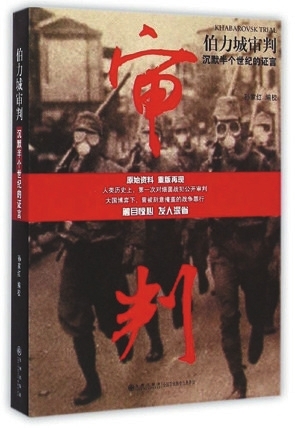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