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伍德·安德森在1933年出版《林中之死》中讲了十余则故事,字里行间毫不掩饰那种或许已有点不合时宜的信仰:关于希望,关于呼应,关于对称。
20世纪早期,工业文明全面取代传统文明,秩序溃乱巨变、心灵惶惶骚动,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不确定性。为了跟上时代,思想和语言也发生了神奇变化。前者挣脱宗教的庇佑,力图窥知生命真相;后者则在文辞内涵与叙述技巧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和个人性。在这个背景下,美国中短篇小说进入了佳作迭出的神奇年代。1925年《伟大的盖茨比》,1930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这些人类叙述史上的永恒杰作接踵问世,合力为我们描绘出光怪陆离的新世纪真相:意义的消解和结构的无序——“道理”同上帝一样,没能陪伴人类迈过现代之坎;启程之初,它们便已横遭祛魅、魂飞魄散。
如此一来,1933年出版《林中之死》的舍伍德·安德森,便显得颇为奇特和勇敢了。这部短篇小说集中,他讲了十余则故事,字里行间毫不掩饰那种或许已有点不合时宜的信仰:关于希望,关于呼应,关于对称。
安德森的这种勇气,或许与他比菲茨杰拉德和福克纳们早生了大约五分之一个世纪有关。在这额外的20年里,一个人恰好赶得上汲取19世纪晚期的古典均衡之余韵,借此奠定在纷乱的现代世相中仍然保持某种坚定的底气。
开篇故事《林中之死》,老太婆养鸡养猪,侍候变成坏人的丈夫和儿子,“每天的每时每刻……都在喂养什么”。完全失败的一生让她对一切见怪不怪、麻木不仁。这样一个故事,本身足以焕发出合格现代小说的光彩。不过安德森的神来之笔在于,在自然主义的进程之末,他又添了一个不矫情却华彩的结尾。老太婆赶集回家,体力不支,中途倒地死去。伴随她左右的饥饿狗群百无聊赖,迅速恢复了部分野性,绕着圈子跑动起来。“在冬夜的月光之下”,一圈又一圈奔跑的狗群,让这个故事背后,始终默默无闻的自然突然凸显。它完美和谐、永恒强大;因为死亡而消散了人类气息的老太婆尸体,也因为裸露背部半埋在雪地中而显得光滑美丽、宛若少女。借助现代语言的隐喻和视角的奇特转换,我们被提醒以人类始终拥有的别样生命可能。这,仅仅是安德森一意孤行营造的幻象,还是富含着温暖慰藉的人生真相?
这个惊喜之后,安德森在《她在这里——她在冲凉》中,讲述了一位因为妻子出轨而痛苦万状的丈夫。安德森选择意识流笔法让男人慢慢流露出疼痛,像荒漠中汩汩涌现的宝贵泉水,证明世上依然有“真情”存在。以这种并不时髦的写作态度,安德森一清二楚地表达出对人类情感的支持。他这样做,是把自己暴露为了一个该遭嘲弄的过时老派人,还是说其实是在为我们做出超越一切时代表象追踪真实人性的表率?
美与恶之并行不悖,也是安德森擅长构建的一种对称。《偶见南方》中,出现了一位满溢着地母气息的莎莉姨妈,她用神一样的慈悲,给予痛苦者以立刻生效的无言慰藉。安德森告诉我们,她一生像摩尔·弗兰德斯一样在罪恶中穿行,但是恶无损她的美,反倒开拓了她的眼界,成就了她的胸怀。在最绝望的时刻,她的美散发出来,阻挡世界走向凄凉惨淡的末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缺乏《恶之花》一样沉陷到腐败最深处的勇气,还是因为对于事物之间因果相扣的笃定关系依然存有信心?
这部短篇小说集,称得上安德森的盛年成熟之作,毫不含糊的现代文笔散发出一位浸淫于生活多年的成年人的思考。安德森是这样一位作家:在他身上,旧时代和新时代融为一体,万象崩乱与毅然决然的坚持齐飞。这些形式质朴却志向高远的文字,你无论信或不信都无法绕过;它们帮助20世纪初的美国小说,乃至帮助今天的我们,增加了一个独特宽阔的视角。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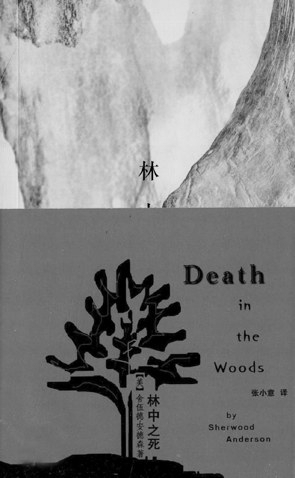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