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 ■刘兵
□13年来,通常我们在这个栏目中不谈我们自己的书,这当然是为了避嫌。不过后来在朋友的劝说之下,对于我们主编的书曾偶尔网开一面——自己主编的书总是比较熟悉,推荐和评论一番,对于读者了解其书毕竟也不无益处。这次的《剑桥科学史》第五卷,情形也是类似的。此书你我和杨舰是所谓“主译”,其实主要都是年轻学者们辛勤翻译的,我们几个主要是做了一些组织工作。所以在这里谈一谈这一卷,我想还是合适的。
以前我们在这个栏目谈过《剑桥科学史》先出的第七卷(2008年)和第四卷(2010年)。第七卷是“现代社会科学”,当时我们还对《剑桥科学史》关于“科学”的定义如此之宽着实感叹了一回。第四卷是“18世纪科学”,现在这个第五卷是“近代物理科学与数学科学”,都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学史。第五卷论述的时间范围,大体在18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在我的认识中,这个年代的科学可以认为大体尚在纯真年代——最简单朴素的标准,就是科学尚未像如今这样爱钱。
这一卷分成6个部分,凡33章,分别出自37位西方学者之手。对于这种成于众手的编撰方式,我一直心存敬畏,但考虑到这样一部多学科、跨专业的科学通史巨著,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了。
■先来回应一下你关于众手编撰方式的想法。我倒并不认为这是无可奈何之事。如果说,在萨顿时代那些科学史大师们还有独自撰写一部巨型科学通史的宏愿的话(但其实连萨顿本人也并未真正完成,只写到1400年),在如今,这样的愿望几乎已经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了,尤其是在编著一部真正学术性的而非通俗读本或教材时。差不多已经是学术界相对公认权威的各种多卷本的“剑桥……史”系列,也都是采用这种多人集体撰写的方式。其实这与历史学(当然也包括科学史)发展到今天这种分支颇细、研究日渐专深的程度密切相关。只有邀请对其撰写的内容及时期有专门研究的人来撰写,才能真正保障较高学术性和权威性,当然,主编(或主编们),还是要对书中的内容、结构,以及对撰稿人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判断和决策。
此外,我对于《剑桥科学史》第五卷印象较深的地方,还在于这卷原版出版于13年前的著作,在内容结构上表现出来的对于科学及科学史的非常前沿性的理解。比起以前形式上近似(当然在篇幅上要略小)的著作来说,这本断代学科史性质的著作中,涉及到内史之外的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章节和内容,比重上要大得多的多。例如,它涉及到公共文化,科学方法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物理学与性别,科学普及,科学与文学、科学的场所、设备与交流(语言),科学、技术与战争,科学、意识形态与国家,甚至涉及物理学与医学,以及全球环境变化与科学史等等。过去很难想象,在这样一部关于物理科学和数学科学的科学史著作中,会将这样多远远超出内史范围的内容纳入其中。
□不少讲科学史的人都喜欢谈论从上个世纪开始的“大科学”时代,意思是科学已经不再是科学家个人的小作坊形式的活动了,它变成必须由多人甚至大规模合作的活动。仿此而言,或许可以说,我们也已经进入了“大学术”时代,大型学术著作也经常依赖多人合作才能编撰完成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分歧也许只是审美意义上的:我们实际上都接受了这一现实——要不我们也不会亲自参与到这种形式的学术工作中去了。
关于《剑桥科学史》的这一卷,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恰恰也是它非常浓烈的“外史”风格。作者们非常关注科学与社会、政治、军事、文化乃至时尚等等方面的关系。首先,许多大小章节的标题就强烈提示了这种关系,比如“1800年以后物理学的公共文化”、“19世纪和20世纪物理学与西方宗教的交会”、“文学与现代物理学”、“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与新物理学”、“雅利安物理学与纳粹意识形态”……更为令人惊奇的是,在全书33章208节中,有许多章节里甚至完全没有任何“内史”的内容。
非专业读者完全不必被这一卷《剑桥科学史》的名头吓得敬而远之,因为书中充满着非常有趣的内容,甚至八卦都有一席之地。例如,1835年纽约《太阳报》那场非常有趣的关于约翰·赫歇耳(JohnHerschel,1792~1871)用望远镜发现了月亮居民的骗局,居然也在第4章“科学家与他们的公众:19世纪的科学普及”中被提到了。而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中国读者通常熟悉的科学史著作中,都是要被无情“过滤”掉的。
■这背后的原因,以及带来的影响和后果,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你所说的“大学术”,其实在科学史这门学科中,也只是在这种大型通史的特殊情形下才会出现。而在一般情况下,在科学史的常规研究中,通常还是按照那种人文学科的传统,以学者个人为主体进行的研究。而这也反过来表明了,为什么“通史”这种体裁,已经不大作为常见的“研究”形式了。但反观我们这里,我们会发现更奇特的现象:一些“通史”,反倒经常为个人所写,并被作为学术业绩考核可接受的研究形式;而与此同时,更多的本来应由学者个人为主体进行的科学史研究,反而经常以必须多人合作的“大学术”课题的方式才能获得承认和得到资助。这似乎又是一种我们与国际不接轨的研究方式。
至于你说到的“外史”风格的浓烈,我还是以为这是历史观念的变化所导致的。也是另一种国内国外不同的景象。虽然这些年里,外史在国内已经在理论上获得了某些认同,但相比之下,国内的研究者们在内心深处对于内史的看重和认同,还是要远比国外更为明显得多。试想一下,如果某人面向非科学史专业的学生以这样的方式讲一门科学史导论课,在我们的通常的评价系统中,会面临什么样的可能性呢?
我甚至有一个猜想,我觉得这样超出我们通常所能接受的程度的浓烈外史风格,也许正表现出在国际上科学史这门学科的研究和普及,正在更大的程度上摆脱这门学科初期所带有的某种强科学主义色彩,同时也更加重了其人文主义的色彩。你说呢?
□你的这个猜想,我非常赞同。
事实上,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科学史界的“外史倾向”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与此同时,法国的“新文化史”之类的学术潮流,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如果这些可以视为某种“国际之轨”的话,那么我们国内的某些接轨行动开始得也很早,甚至和“新文化史”堪称不约而同。但是,就总体而言,这种“接轨”在国内只是一小部分人的行动,许多老一代和新一代学者都仍然继承着传统的“内史”风格。当然,我们完全可以因为这两种风格至少在客观上形成了“必要的张力”而乐见它们的共存。
而如果我们将目光稍微放远一点,就不难发现,在20世纪上半叶,具有现代形式的科学史研究在中国开始出现时,它其实和清代乾嘉学派考据之学的传统大有渊源,甚至可以说就是脱胎于后者的。这种隐藏着的“精神血统”,很容易将研究引向传统的“内史”路径。而相比之下,“外史”风格却显得和这种传统有点格格不入,或者显得有点不够“脚踏实地”了。另一方面,就大体而言,“强科学主义”通常总是缺乏人文关怀的,而“外史”要关注的社会、文化背景,往往有着更多的人文内容。所以,一部在“强科学主义”纲领引导下的科学史,往往就只剩下那点“内史”的编年史和实证内容了。
你上面提到,如果一个学者以《剑桥科学史》第五卷的风格来讲授科学史课程,他在我们这里会面临什么样的评价?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想。以我从业三十余年的经历,我猜想他至少会面临“拉拉杂杂,牵扯枝蔓太多”、“对科学概念缺乏明确界定”、“这到底是科学史还是社会学”之类的非议。甚至还可能对作者的“史学功底”产生疑问,进而质疑作者撰写这样一部科学通史著作的“资格”。
■ 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对于历史(科学史)的功能、价值、“研究功底”,以及教学目标等的不同理解,可以带来完全不同的科学史的教育选择。实际上,近几年来,在我教授的几门近似的科学史课程中,我所选择的方式,恰恰就已经有些像你所说的那种“拉拉杂杂,牵扯枝蔓太多”的风格了。但至少对于科学概念的界定,还是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只不过是突破了原有的那种朴素、简单、传统、狭义的科学定义而已。
其实从这个问题,可以延伸到我们为什么要进行科学史教学的讨论。如果说受众是非专业的科学史研究者,如果面对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讲授科学史可以传达更多关于历史上科学的更全面的信息而非只是专门的历史上的科学的具体知识,那难道不是会让科学史的教学更有意义吗?这也正像在科学传播中,也存在有类似的争议:是坚持传统的对科学具体科学知识的普及,还是以更广阔的视野去传播更加全面、复杂的科学的形象、功能、内容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等。
至于你说到的“清代乾嘉学派考据之学的传统”与“内史”传统的关系问题,正好我近来刚发表了一篇题为“考据与科学史——一些科学编史学的思考”的文章,其中也正是要分析讨论相关的问题。简单地说,我认为,在承认考据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极有特色并值得发扬继承的研究方法的前提之下,我们也不能不承认,那种过分关注考据,关注史料,并以之替代整体的史学研究,已经不是当下国际史学主流的研究范式,而且这样的研究传统也带来了对于国内科学史科发展的限制。
□我的体会是,文献考据和实证、传统的纯内史等等,作为科学史研究者的基本功是不容忽视的,但对于其他受众而言,仅仅依赖这些基本功而作出的论述,和外史风格所体现的广阔视野相比,在思想性、启发性方面有明显的不足。而一种更富思想性或更富批判意识的科学史论述,无论是对于专业的科学史研究者,还是对于一般受众,都将是更有教益的。
如果按照这种非常理想的标准来看,《剑桥科学史》第五卷似乎还稍有欠缺。虽然作者们富有人文关怀的论述已经和“强科学主义”拉开了距离,但他们毕竟还没有能够自觉地将自己的论述置于“反科学主义”的纲领之下——这当然有一点苛求了。总的来说,这一卷不失为别开生面、富有新意的科学史论述,有兴趣了解科学史的读者,乃至专业的科学史研究者,都值得一读。
■在最后的总结中你倒似乎比我更激进一些,因为考虑到科学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惯性以及它与科学传播这样的学科的差别,我觉得《剑桥科学史》能够做到现在这样的程度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反过来想,如果不是有着这样权威身份的支撑,写出这样设计章节内容的科学史,还不知道要受到业内传统倾向的人士多少无情批评呢!
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一卷确实给我们以某些重要的启示和示范。甚至不限于这一卷,我记得以前我们曾谈过另外两卷《剑桥科学史》,其中也同样有着与传统类型的科学史非常不同的选题特点。这恰恰说明了,科学史研究同样应该并且可以是迅速发展的,发展不只体现在传统类型的内容在数量上的扩展,更体现在研究者观念上的更新。
除了对于科学史的研究的意义之外,这种充满新意的科学史论述,对于转化为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的重要而且可靠的资料基础,也将是非常好用的呢!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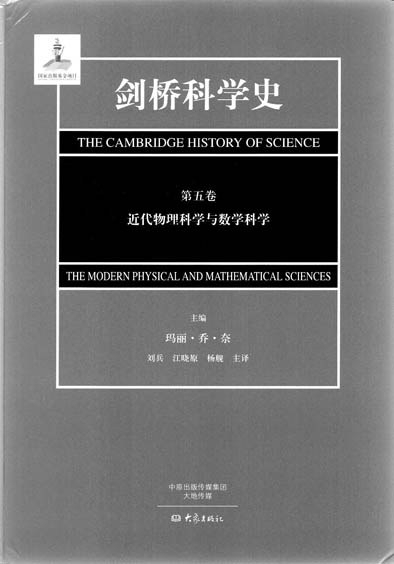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