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孙剑艺担纲和主撰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称谓分期研究——社会语言学新探》(下称《新探》),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全书100余万字,收称谓词语2070多个,可谓皇皇大作。葛本仪先生在序言中所说,“这是一部有关汉语词汇学、称谓学和社会语言学等方面的具有开创意义的很有价值的著述”,可见《新探》的价值是多方面的。然《新探》最突出的意义价值还是体现在称谓研究方面,它是一部汉语称谓学建设的重要著作。
一、开拓创新,开辟汉语称谓学的跨学科研究
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即“小学”,包括音韵、文字和训诂。现代语言学兴起以后,语言学研究的内容范围逐步得到拓宽,但是仍然带有传统语言学的印痕,比如强调语言本体研究,轻视语言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等。《新探》突破了语言本体研究观念的束缚。它立足于汉语词汇学,以社会称谓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把语言研究和社会学、历史学研究紧密结合,基本形成了“二十世纪社会称谓聚合”。透过这个层次分明的称谓聚合,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对于社会称谓的重新组合利用,是作者对于整个二十世纪“四两拨千斤”似的把握,是作者从称谓出发,经过百年历史又回到称谓研究的巧妙构思。把握、描画一个民族的世纪面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深入浅出地引导读者理解百年民族史更是困难重重,尤其是像中国二十世纪这样混乱的历史。然而《新探》做到了,不仅语言研究者能从中有所启发,即使是普通读者读起来也不会有阅读“语言本体研究”的艰涩吃力。作者的眼光是独到的,他选中了二十世纪作为称谓研究的基地。这段历史波诡云谲,伴随历史事件和新兴事物出现了大量新称谓。在《新探》里,这些已固化于史册且已淡出人们视野和记忆的称谓词语,被作者重新赋予了生命,被从故纸堆里请出来再造历史场景,引导我们走进鲜活的历史现场。因此,《新探》不仅是称谓研究专著或社会语言学专著,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汉语称谓研究的新范式,为汉语称谓体系性研究提供了多重借鉴意义。
(一)具体历史时段的称谓研究可以自成聚合。每个历史时段中的称谓都处于一个独特的言语环境,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认识和研究对象。比如《新探》所指向的“二十世纪”、“社会变迁”等,这个言语环境有足够的时长——从清末到改革开放一百多年,足够丰富的社会现象——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等几乎所有社会侧面,社会称谓资料十分丰富,因此把二十世纪社会称谓聚合作为研究对象是合理的。足够丰富的词汇,足够宏阔的社会背景以及合理的研究方式,足以支撑起这一称谓聚合。全方位梳理中华文化系统中一百年的社会称谓,这是第一次,作者借此建立了一个社会称谓研究的框架或曰套路,而未来“汉语称谓学”的学科建设的相关部分必然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二)《新探》的研究范式是开放式的,以它为基础能够产生很多副产品。像《新探》这样浩大的称谓研究工程,拥有如此丰富的称谓资料,它能给我们的启示不仅仅是称谓与历史的结合这么简单,在词汇、民俗、历史研究的内容上,甚至研究方式上,也给我们留下了创新思考的空间和可能。其中有些称谓如“左派”“匪徒”“总统”等,在这一百余年的历史中反复出现,构词成分相同但意义和社会背景不同,探究此类称谓的历史变迁无疑是有意义的。再如《新探》一书中出现了大量的“~户”类称谓,归纳起来,又可以形成新的研究对象。另外,单就研究的形式而言,《新探》之后,还可以形成“二十世纪社会称谓词典”之类的副产品,其研究的价值绝不亚于专书词语词典。
(三)《新探》既提供了学科交叉研究的范本,又提醒我们开拓称谓研究的学术视野。把语言本体意义上的称谓词语研究和其他学科研究结合起来,拓宽称谓研究的范畴,如社会学、历史学、人口学、民俗学,甚至教育学、心理学等等。这种基于学科交叉的研究,取材的范围、方法以及结论的形成等等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比如关于“称谓”的定义这个基本问题,《新探》的作者就有新的探索:《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定义是:“人们由于亲属和别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身分、职业等而得来的名称,如父亲、师傅、厂长等。”在大量材料综合与归纳思考的基础上,作者给“称谓”下了这样的定义:“称谓就是反映人和人际关系以及人的身份、职业、阶级、阶层、社团和群体等的普通名词。”比较而言,后者比前者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作者强调的是,从本质上讲,“称谓”是“以人为本”的,称谓研究不可就语言论语言,就词语论词语,研究的眼光应该放得更远一些,视野应该放得更宽一些。以教育领域为例,其中有很多称谓值得研究,如“差生”“高考状元”“尖子生”以及恢复高考初期产生、现已退出使用的“老三届”等等。《新探》注重“称谓”以研究普通名词为主的学术定位,同时也关注某些社会性极强的组织、团体名等专有名词,尤其是其简称。比如“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等简称固须关注,且在应用中它们又转化为个体称谓,如“两个红军”“三名八路军”等;但要讲清其来龙去脉就必须从其全称“中国工农红军”“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这类专名讲起;同样讲“国军”就不能不讲全称专名“国民革命军”。这正是原则性和变通性的统一,非如此就不足以体现该课题“社会语言学”的特点。
(四)称谓研究要注重语言事实描写。中国传统语文研究的重要特征是研究事实,重视实证,在材料中寻找语言规律。我们以吕叔湘先生为例,他的汉语语法研究特别重视和提倡语言事实描写,他认为解决语法问题的途径,“首先在于对实际用法多做调查,而且这种研究方法极其重要,事实摆得不够,道理也就难于说明。”吕先生的这种治学方法很值得重视。“重视和提倡语言事实的描写”不仅是解决语法问题的途径,也是各种语言研究的重要方法。称谓是交际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称谓理论就包含在活生生的语言事实之中,研究称谓必须首先关注其实际应用的语言事实。汉语称谓研究的历史虽然长,但是称谓理论体系并未建立,至今汉语称谓研究仍以专书称谓、方言称谓等为主要研究内容,以词典等为主要成果形式,所以目前的汉语称谓研究必然更加注重称谓事实的统计和描述。《新探》以称谓为媒介,实现了语言研究和社会变迁史的结合,称谓、界定、例证同时呈现,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行文活泼,可读性很强。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每个词目下都用简明的文字说明了它们的主要意义,并标明词类,一词兼几类的也都分项标明。用法都通过例句说明。这种收词方法和释例都是创新的做法”。在重视语言事实描写和构筑全书创作模式上,《新探》与《现代汉语八百词》有相似之处。朱德熙先生在1982年6月24日“香山语法会议”上的讲话更有指导意义,他说:“离开事实的理论,是空的理论,没有用。”“不去研究事实,所以没有什么新的见解。事实是根本,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就什么也做不出来。我们去研究事实,新的东西和新的想法就会出来,离开事实就不可能。”
(五)《新探》充分体现了语言研究的实用性。称谓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和情感基因的集中代表之一,称谓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民族特色。上文谈到称谓研究必须大量占有语言事实,这些事实是汉语语境下的称谓事实;从这些事实里我们可以发现称谓演变的规律,这些规律也是属于汉语的。民族性也好,汉语语境也好,汉语称谓研究首先是为汉语服务,为中国人的语文生活服务;研究方法是重考证,重实用。我们不能否认纯粹书斋式研究的价值,不能否认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好处,但是发扬传统语言研究的实用精神,让研究从近乎语言游戏的名词“倒脚”中解脱出来,给读者一个看待历史的新角度,没错儿!正如吕叔湘先生在香山语法会议上所说:“总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研究最后还是拿出去给人用的。”《新探》深深植根于巨变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以重大历史拐点、关键人物和历史事件为考察研究对象,依赖其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轨迹,论从史出,重实证,重材料,一切信而有征,让不懂语言研究的人也能够读得下去读得懂,充分发挥了语言研究服务于人的作用。
学术研究总是创新的,只有创新的才是有价值的,对于汉语词汇研究和汉语称谓的深刻理解,给了作者创新的见识和勇气,《新探》则给我们提供了新思考的可能。对于汉语称谓学研究体系的形成,《新探》是一本具有原创性和建设性的重要著作。
二、承前启后,推动建立汉语称谓学研究体系
汉语称谓众多且繁复,非其他任何语言可比,这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发展沉积的结果,是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称谓之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是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锁钥”之一,是汉语研究和中国文化研究中值得重视的课题。认真整理研究汉语称谓,尤其是建立成体系的汉语称谓学,对于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整理浩若烟海的古籍,丰富现代汉语词汇,都有重要作用。前人早就意识到了称谓研究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有很多重要研究著作和专论文章。
但是综观古今文献,汉语称谓研究一直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形成固定的研究群体;称谓理论的滞后,更是阻碍了汉语称谓学独立研究体系的形成。吉发涵先生是著名的称谓研究专家,他曾经论及名字之学的演进情况。从学科分类上,名字训诂之学是传统训诂学的一个分支,无疑更是汉语称谓学的一个部分,因此他的议论或可给我们以启发。他认为,从《说文解字》以名与字关系阐释字的本义,至清代王引之作《春秋名字解诂》,“名字训诂学”真正成了一门独立的学问。然而这门学问的发展道路很是曲折,甚至“至今百年以来,这一渊源有自的传统学问,更是愈加无人问津了”。但王引之毕竟起了关键性的带动作用,清季俞樾、胡元玉、王萱龄、陶方琦、黄侃以及现代于省吾、周法高等学者们,又有一些后续成果。不过这些成果还都是局限在春秋、周秦时代名字训诂实例的补充,直至2003年吉常宏、吉发涵128万字的巨著《古人名字解诂》问世,名字训诂之学才有了一个新的高峰,重新焕发出绚烂的光彩。
由名字训诂之学我们可以看到汉语称谓研究发展的艰难,在整个文化史上呈现出时隐时现的特征。自从《尔雅》将亲属称谓单独列为一篇“释亲”,嗣后的《小尔雅》《广雅》等雅类著作续有补充。北周卢辩有《称谓》五卷,见载于《隋书·经籍志》,可惜已佚。唐刘知几《史通》有“称谓”一篇,从史的角度专论各类帝王君主称号。直至清代,才有了梁章钜《称谓录》这样集大成般汇释亲属称谓、社会称谓的里程碑式著作,嗣后则久乏可陈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汉语称谓辞典陆续出版,其中《汉语称谓大词典》350多万字,收词三万余条,无论在规模上、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上,均超越以往辞书,《光明日报》2005年1月25日马丽《汉语称谓研究十年》谓之“称谓词典编纂史上的里程碑”。90年代是汉语称谓研究的一个小高峰,出现了多部称谓研究专著。如林美容的《汉语亲属称谓的结构分析》(1990),袁庭栋的《古人称谓漫谈》(1994),夏先培的《<左传>交际称谓研究》(1999),等等。进入新世纪以来,称谓研究的单篇文章逐渐多起来,同时出现了一批研究称谓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称谓研究的热潮正在形成。
综观以上各种研究成果,专书称谓研究多,亲属称谓研究多,社会称谓的专门研究不多,建立系统性的“称谓史”和理论性的“称谓学”更是任重道远。《新探》主撰孙剑艺教授就“称谓研究的体系性”问题表达了这样的思考和忧虑:“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是汉语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而称谓和称谓史的研究更是弱中之弱。……新时期的称谓现象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就……但由于种种原因,对汉语称谓的总体理论探讨和称谓史的系统研究,却显出苍白和匮乏的迹象,至今尚无一部‘称谓学’或‘称谓史’著作面世;至于结合社会历史的演变对汉语社会称谓变革进行的探讨,虽不乏精彩个案研究的单篇论文,但缺乏相对集中而系统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原创性思考和建设性精神,作者紧扣“社会称谓”,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申报了国家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经过长期奋战,终于推出《新探》这部巨著。
《新探》的研究不是零打碎敲式的,而是对一个世纪社会称谓的体系化研究。或许正是这样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对象,让作者深刻地体会到了“汉语称谓研究体系”和“汉语称谓学”的缺失,以及这种缺失对于已经成就斐然的汉语称谓研究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遗憾。在汉语称谓研究的历史上,提及“称谓学”或“称谓史”者当不止一人一处,但是能够站在“研究体系建设”的高度认识这个问题,并明确提出“称谓学”“称谓史”概念的,《新探》及其作者可以算是“第一个”!这种认识将促使汉语称谓研究由“自发”更加坚定地走向“自觉”,而且必将有力推动“汉语称谓学”和“汉语称谓”研究体系的建立。“社会称谓”是称谓家族中的一大分支,集中研究某时段社会称谓,《新探》是“第一家”。因此《新探》在称谓研究史环节上无疑是一新的里程碑式作品,对将来“汉语称谓学”的学科理论和体系的构筑,有着举足轻重的参照和借鉴作用。同时《新探》开了一个新路子,积累了新经验,培育了研究新人,以此为基础,相信会做出更新奉献。
三、十年一剑,以“笨功夫”治学
“知人论世”是传统的读书论人的重要方法,意思是要知其文其人,还需了解他的身世经历。主撰孙剑艺教授师从著名语言学家殷焕先先生,殷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校外导师是王力先生,《汉语称谓大词典》的编者吉常宏先生也是王力的学生。孙剑艺教授当年研究生毕业留校后即投入了吉先生领导的词典编纂工作,吉先生成为他工作上的老师,所以孙剑艺教授对于吉先生执弟子之礼,并时时就教,深得赞许。这次《新探》出版,吉先生即欣然撰序,予以支持和鼓励。吉先生是著名语言学家,也是著名的汉语称谓研究专家,先后出版了《中国人的名字别号》《汉语称谓大词典》和《古人名字解诂》等重要的称谓研究专著。孙剑艺教授跟随吉先生先后参加了《汉语大词典简编》和《汉语称谓大词典》的编纂工作,经过工作打磨和经验积累,由汉语音韵学和词汇训诂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完成《汉语称谓大词典》之后,他进一步开拓汉语称谓研究领域,创新称谓研究方法,把称谓研究与社会变迁结合起来,成功申报了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二十世纪社会变迁与社会称谓研究”。葛本仪先生在序言中这样称赞他的人品和治学精神:“观往知来,知他绝不会草率从事,定能克服一切困难,以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取得成功。果不其然,历经了十数载苦功,一部规模宏大的巨著《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称谓分期研究——社会语言学新探》终于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虽然如此,作者却说他下的都是“笨”功夫。在《汉语称谓大词典》的整个编纂过程中,吉先生称赞他道:“在这项工作中,从看书选词、制作卡片,到词条的编写,清样校改,无一不是兢兢业业,刻苦认真,一丝不苟。此外,他还负责全书的审音工作。事实证明,一切皆准确无误。”语言研究尤其是汉语词汇研究考证,最需要的就是一丝不苟的“笨”功夫。
学术研究必须是认真的,搞清一个问题可能会花费很长时间,做一个大课题项目更是如此。梳理二十世纪社会称谓脉络需要投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期间历尽艰难而甘苦自知。作者清楚地知道称谓研究的重要性和学术价值,在对于汉语称谓学研究体系未成表示遗憾的同时,更没有忘记努力,他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把称谓学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但是正如钱穆所说:“当知祖师开山,不是件容易事。”“此人则抱大志愿,下大决心,不计年月,单独地在此住下来。……把这无人烟的荒山绝境彻底改换了。这是所谓的开山。”尚没有形成研究体系的汉语称谓学就是这座“荒山”,《新探》作者虽不是“开山祖师”,但他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一直在这座“荒山”上默默地下着“笨功夫”。该书《前记》和《绪论》都是2009年冬为报送出版社稿和教育部结题时所撰写,距离设计立项已十个年头,作者说,“倘欲藉此应酬职称评定及计算年度工作量之类,岂非‘黄瓜菜早凉了’?故斯乃笨人之举,非巧人之所为也”。而《后记》是2013年冬该书将正式出版时写就,作者又下了整整四年“笨”功夫,前后达14年之久!《新探》所表现出来的“笨拙”,是对当下某些人急功近利的学术心态,以及服务于职称和应付课题等不良风气的有力回应。学术研究不能成为应付某个项目和课题的附庸,否则,所谓学术研究的价值支撑点又选在哪里呢?在今天这样浮躁的学术环境下,能够不计声名利益,板凳宁坐十年冷,正是值得我们赞叹的。
一部重要著作的价值总是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和世人的评说。据笔者所知,该书在撰写的过程中已经受到了不少的质疑。这些质疑主要集中在一点——超出了语言本体研究云云!质疑总是难免的,质疑和争论是学术进步的推动力。中国的语言研究不能停留在“小学”上,不能固步自封,要在传统学问的基础上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借鉴世界前沿理论和方法。当然,如果我们把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奉若神明,那肯定也不符合辩证法。因此,不论国内国外,所有的学术研究都要注意继承与创新的结合,兼采各种理论之长,注重理论研究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何况,该书创作原则本来就不是局限于语言本体研究,而是“从汉语本体研究出发,结合社会生活和社会变迁来观察和探讨社会称谓在特定时期的意义及其发展变化,力求在学科渗透和沟通方面进行某些拓展”。《新探》很好地做到了这些,作者的汉语称谓研究是有理有据、底气十足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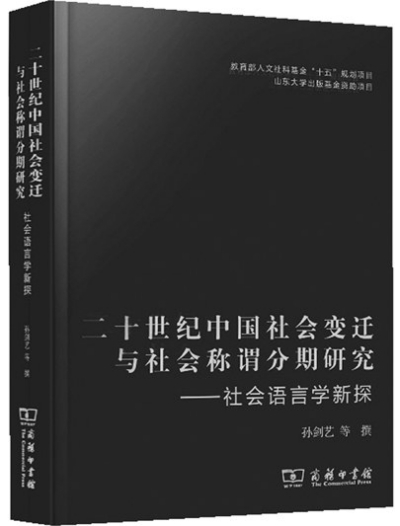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