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先生赛先生登陆中国之初,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国人,文盲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的确需要现代知识的普及;在号称经历了现代文明洗礼积年的当下,镇日痴迷于奔竞追赶的国人,扫盲虽然依旧是重要任务,但受教育人群确乎起码在统计学意义上在人口中据有了相当比例,却仍然需要对譬如科学这样的现代文明利器,进行知识上的认识或曰再认识。文盲充斥的时期,作为扫荡蒙昧的新知,科学的意义在于催动现代化的进程,而当下之于科学的再认识,根本则在于辨别这个催动的利害。
如同五四时期的一贯风格,科学的观念在落地本土伊始,出现的面目便是纯粹正能量的,也就是说,科学是超级良性的。这样的认知,如果套用曾经的时代语汇予以定性,便是唯心主义的观念。在主流思维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看来,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并不存在超越的例外。这里不妨借用徐友渔先生的陈述:从微观角度看,肯定科学价值的新派人士往往是热情有余而素养不足,当他们以科学为武器反对迷信和无知时,他们的口号和姿态似乎可以概括为这样:“我们什么都不迷信,我们只迷信科学”,这当然是与科学精神不符的、自相矛盾的态度(《认识和肯定科学的价值》)。其实,即便按照科学的观点,科学也是一个需要不断进步因而也就是永远不够完善的开放体系,因而它本身便存在缺欠和盲区。所以,上述对科学的偏执认知,应该说反而正是不够科学的。于是,在纵情享受了工业革命的盛宴之后,思考一下被这桌大餐强势裹挟下的死穴,就显得十分必要。因而,田松先生这本名为《警惕科学》的小册子就特具意义。
对科学提出警惕,这口号听起来难免让大多数人不适,却绝非危言耸听。田松留意到,本土媒体是在2000年之后才小心翼翼地采用了科学是双刃剑的说法。正如田松所说,一旦我们接受了“双刃剑”这个说法,在逻辑上,我们就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科学及其技术给人类带来的麻烦远远大于给我们带来的便利,所以总的来说,科学及其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是负面的(页13)。
尽管双刃剑的说法足以从传统文化的老庄哲学之祸福辩证中找到人文支撑,但也需要承认,将科学归结为负面,终究是不合时宜的,或者说是有些超前的。换句话说,警惕科学这样的警省,虽然提出得正当其时,但在大众乃至智识阶层以及主流话语体系看来,尺度不免稍嫌过大。当然,如果联系到此前主流话语体系拉动的大众之于科学的偏执观念,这样的过正,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哲学与科学史博士,田松提出的警惕,虽然果然有理论层面的建构,譬如将经验依据和历史依据排在科学依据之前,更要紧的是,他所有论证,都是从具体出发的,譬如,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喝牛那种动物的奶,我们就是不需要蛋白质,以及中医为什么要有科学依据,都纷纷成为他立论的题目。
当食品问题从卫生层面升格到安全层面,对喝牛奶和吃蛋白质提出追问便是必须的。田松的某些观点,譬如,科学的技术首先满足的不是人的需求,而是资本增值的需求;在工业文明的框架下,科学及其技术已经从神学的婢女,堕落成了资本的帮凶;被张华夏教授指出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页87、122),因而无疑具有理论上的说服力。巧合的是,科学和资本主义正好是现代社会最普遍看重的两个信条。不过,作为食品的消费者,即便明知资本才是诸如喝牛奶有益健康之类所谓科学宣传的终极受益者,却也未必可能因此而改变其被裹挟之下的奶品诉求,甚至关于乳糖耐受的科普恶补,也略显乏力,虽然它真的具有学理上的依据:
牛奶的主要成分是乳糖。幼小的哺乳动物的肠道分泌乳糖酶,分解乳糖为单糖。成年动物,包括除高加索人种外的多数人类体内乳糖酶的活性大大降低。故饮用乳类可产生腹泻、腹胀等症状,称为乳糖不耐症(页56)。
这种不耐症虽然会带来身体的不适,但却不妨有不惮烦的科学化解,譬如,配合谷物同吃,少量多次,喝酸奶,加一片乳糖酶或含乳糖酶的奶粉,种种(页62—63)。这些化解也许会令人产生为何偏要这么麻烦地喝牛奶的置疑,但在大众看来,终究是既来之则安之的补救,显得十分体贴。
真正能够醍醐灌顶般提供唤醒支持的,还是同样远远超越田松自己脆弱想象力的事实:
奶牛为什么会产奶呢?因为她生小牛了。奶牛为什么会不断地产奶呢?因为她不断地生小牛。奶牛为什么不断地生小牛呢?因为她不断地怀孕。奶牛为什么不断地怀孕呢?因为她不断地被人工授精(页68—69)。
如果这些不够“牛道”的程序还不足以给力,那么下面的陈述是否更具“杀伤力”:
……所以不能让她们病,不能让她们死;所以要不断地给她们注射疫苗,注射抗生素。为了保持奶的产量,还要注射激素,注射催奶剂。同时,奶牛的饲料中也必然包含着化肥、农药以及各种添加剂。在奶牛的体内,不知道被人灌进去多少莫名其妙的化工产品。而这些化工产品,大多数是牛这种动物的身体从未接受过的,牛不知道怎么分解它们,它们必然会分布到奶牛的奶液中(页71)。
这样的工业流程算得上惊心动魄,理当富有相当的启迪乃至震撼意义,但有趣的是,奶品的消费,在经历了三聚氰氨的洗礼后,依然呈现着旺盛的势头,个别杀掉奶牛的案例,不过是境外奶品进入导致的行业调整,与食品卫生和安全反而不搭界,大众甚至对科学意义上的相关纠错也予以忽略,似乎甘心整体上成为食品工业的小白鼠(页103)。这只好再次证明了,一种强势的不免具有巫术色彩的所谓科学宣传,真的可以深入人心,轻易撼动不得。
不过,就本土而言,对于长时段的集体的历史依据,也即我们曾经拥有的稳定的饮食文化,是否曾有食用牛奶的传统,也许并不方便做出决断性的判断。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中国养牛史”条下,专门提到了牛乳及其制品,不妨引述如下:
牛乳及其制品,一向是草原地区各族人民的主食。乳古称湩,秦汉时已由塞外传入。到南北朝时期,已遍及北方农村,《齐民要术》就详细记载了农民挤牛乳和制造乳酪的方法。乳制品在古代通称为酪,也很快推广到南北各地,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时在今甘、青、川诸省以及庐州(今合肥市)也已有此产品。此后,江南如湖州、苏州等地农民也养乳牛,挤乳作酪,并制成乳饼及酥油为商品。直至西洋乳牛输入以前,中国南北不少城市早有牛乳供应,采取的是赶黄牛上门挤乳出售的方法。20世纪初期开始,才从欧美引入乳牛品种,饲养在各大城市,供应乳品。至于牛的肉用,虽在1000多年前已出现近乎肉牛型的优秀牛种,但限于特定的经济条件,加以佛教的影响,一直未获发展。
关于乳牛引入的时间,同书“奶牛”条下则说: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西方国家育成专门化奶牛品种后,不久被引入中国。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又先后从国外引进黑白花牛、爱尔夏牛、更赛牛和娟姗牛等。大多饲养于各大城市,但以后仅剩黑白花牛一个品种。经用黑白花牛与中国黄牛杂交,并对其后代进行长期选育,已培育成中国黑白花奶牛品种。
这样看来,尽管对乳牛引入的时间确认尚存不同说法,但牛乳及其制品的本土食用,原是有历史依据的。不过上述记载并不方便证明其为具有广泛意义的传统,推断起来,似乎更像是民族文化融合之下的食鲜,起码不具有游牧民族那样必需品的意义,自然也同样不意味着当下喝牛奶的case就有了天赋的饮食基因,因而田松所谓中国汉民族中的大多数也没有食用牛奶的传统(页42),未必不可以成立。而且,传统养殖业与现代意义上的食品工业,终究是归属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于警惕科学的思考,不存在反证关系。
刘华杰先生说,科学主义是我们的缺省配置。这话无疑目光犀利,因为的确是当下的现实写照,同时也提示,这种系统默认的模式,实在是强制预设的。正如田松所说,在更多的时候,科学这个词被用作形容词,指正确的、高明的、有效的、经过证明的、具有权威的等等极富披靡效应的意义(页17)。
同样如田松所指出的,当代人对科学的信仰,是建立在对牛顿物理学的信仰之上的。我们相信,牛顿物理学已经给出了超越地域、超越文化的关于物质世界的普遍性的知识(页90—91)。姑且不必讨论这世界上是否存在一个能够超于地域和文化的科学,起码可以确认的是,科学终竟只是解释世界的一种观点和体系,哪怕它是最大限度的接近世界本质的观点和体系,但它依然并非惟一。这个世界无论是客观实在还是由客观实在生发而来的理论体系,只有保持多样性才会有可持续的共生空间,即便有些多样性在所谓人本的观念看来不乏负面,但大自然的奥秘,即便以科学的眼光看来,也是难以穷尽的,在它面前,包括科学在内的任何人类的体系,都是渺小的,望尘莫及的。
诚然,在对无限度尤其是有意识放大科学能量的观念予以纠偏的同时,也必须承认科学对现代文明所贡献的正面意义,对于现代生活,科学几乎是不可挣脱的,而这个不可挣脱,只要人类真的聪明,其实是可以控制在一个相对的利大于弊的范围之内,也即是可以尽可能保持正能量的,起码它是足以部分改善人类生活的辅助系统。只是这个禀赋正能量的辅助系统,必须有个需要24小时伺服的控制阀或者警示牌,不可放纵当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本小册子隶属于“科学人文书系”。这果然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视角,起码就田松的这本书而言,理由简直是现成的:传统文化中倡导的中庸,其实对任何缺乏节制的放纵都持有警惕。不过说句未必题外的话,从人文的角度检讨科学,也许会被不屑为门外谈。但这样的检讨却未必没有参考的意义。况且,如果科学与人文真的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势同两立,那么科学其实也就不方便对人文之于科学的检讨予以置评了,因为置评便意味着门外。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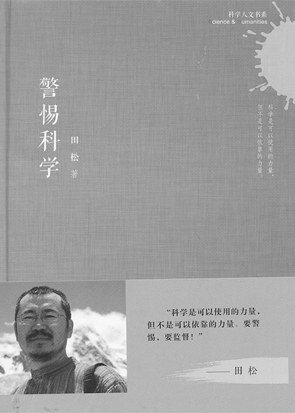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