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社会生物学下的儒家思想》(Socio-biologicalImplicationsofConfucianism)一书是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潘光旦先生的英文文集。潘光旦先生于学术研究上涉猎甚广,建树甚丰,在民族学、谱牒学、性学和教育学等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文集以潘光旦在1923年到1935年之间创作的社会生物学、民族学方面的学术简论文章为主,深入介绍了现代中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系统思考,通过这样的思考,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民族危机、现代化主题交织下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文集所收文章皆为潘光旦先生用英文亲撰,用其弟子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先生之于国学有其家学渊源的,他自动受到严格的庭训,加上他一生的自学不倦,造诣过人。……在他同代的学者中,在国学的造诣上超过潘先生的固然不少,但同时兼通西学者则屈指难计。……据说他英语之熟练,发音之准确,隔室不能辨其为华人。返国后,他曾在上海执教,又兼任著名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周报》的编辑。他所写的社论,传诵一时。文采风流,中西并茂,用在他的身上实非过誉。”
文集的出版有赖潘光旦先生后人历时数十年,搜集整理了这些年代久远、散见于国内外刊物的英文文章。而外研社·施普林格“中华学术文库”(英文丛书)收录该著,由两社联合推出海外英文版,则不仅有利于中外学术文化交流,更能让外国读者了解中国现代社会学、民族学的奠基与发展脉络,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从而进一步理解当代中国。该书同时入选2011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在《社会生物学下的儒家思想》海外版出版之际,本刊特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吕文浩博士为此撰写的导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新篇章,在此前后若干年,伴随着中国现代大学系科制度的逐渐建立和完善,以及一批留学回国的青年学人的努力,中国现代学术开始建立和发展,部分学科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其中在优生学、社会学以及性心理学等学科领域,潘光旦是一位非常活跃而且有突出成绩的学者。作于1922年夏的《冯小青考》是潘光旦学术生涯中第一篇比较重要的作品,至1965年“文革”前夕基本完成翻译的达尔文巨著《人类的由来》则标志着潘光旦学术生涯的结束。在此前后长达四十余年的时间里,潘光旦以其博学睿智,孜孜矻矻,努力探求中华民族的强种优生之道,写下了许多流传至今、为人称道的作品。所幸大部分著述经精心搜集整理,汇集为14卷本、640万言的《潘光旦文集》,为后人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可资信赖的版本。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14卷本《潘光旦文集》并未收录潘光旦为数不少的、文采斐然的英文著述。虽然文集编者在第11卷的末尾以“存目”的方式将这些英文文章的篇名和出处加以详细的列举,但这些年代久远、散见国内外刊物上的英文文章查找起来仍然极不方便,在2011年英文《中国评论周报》(TheChinaCritic)全部影印出版之前就更是如此。文集出版十几年来,鲜见学术界重视并利用这批英文资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现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决定将潘光旦英文文集《社会生物学下的儒家思想》纳入“中华学术文库”系列予以出版,使更多的读者能够欣赏前辈学人的英文著述,并对其学术造诣和精神世界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可谓功德无量。
关于潘光旦当年英文的写作水平,学术界流传有多种说法。其同代人和朋友刘英士在抗战时期的一篇文章中称他为“能写漂亮英文的潘君”;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据说他英语之熟练,发音之准确,隔室不能辨其为华人。返国后,他曾在上海执教,又兼著名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周报》的编辑。他所写的社论,传诵一时。文采风流,中西并茂,用在他的身上实非过誉”;20世纪30年代清华社会学系的学生王勉(笔名鲲西)曾回忆说:“潘先生英文造诣极深,在上海时和林语堂、全增嘏、吴经熊等都是《中国评论周报》(TheChinaCritic)的特约撰稿人。有一件事现在人知者不多,孙文遗嘱有多种英译本,其中认为译得最好的即是出于潘师之手,遗嘱首句余致力云云,译文用字精炼典雅,读过的人都能记得。”这次借着写导言之机,我阅读了文集大部分篇章,对潘光旦的英文写作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最突出的印象是词汇丰富,用字精练典雅。孙文遗嘱的翻译确实如王勉先生所言,读后令人印象深刻,几可成诵,而1925年最初翻译时潘光旦只有26岁,1927年修订翻译时也只有28岁。
文集的编者几十年来做了很大的努力,尽可能搜集潘光旦的所有英文著述,因而遗珠之憾并不多。据我所知,若干篇什得来非常不易,如潘光旦大学四年级时发表在美国《优生新闻》(Eugeni⁃calNews)上的文章,以及抗战时期为美国人讲授中国人宗教信仰的文章,刊登的杂志流传不广,在国内各图书馆难觅踪迹,这次能够加以收录,实属幸运。另外,对于潘光旦发表于《中国评论周报》上的文章,编者也颇费了一番功夫,参照潘光旦的中英文著述,努力从笔名中辨识潘光旦的作品,其中的辛劳,非外人能加以体会。这里再说说上文所说的“遗珠之憾”。如上文费孝通所说,潘光旦曾为《中国评论周报》写过一些“传诵一时”的社论,但因该栏目全未署名,哪些出于潘光旦的手笔已经无从辨识了;又如抗战时期中国民主同盟常与英美驻昆明领事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向他们散发民盟中央和省支部的文件、宣言、通电和其他宣传材料,这些材料有的需要译成英文,这个任务多半由潘光旦同志完成,因为他的英文和写作水平都很高,颇能胜任”(《纪念潘光旦教授和曾昭抡教授逝世20周年的发言》潘大逵部分),可惜这部分英文文章一时也无法查找了;再如1947年潘光旦和费孝通曾应太平洋国际学会之约从事“中国士大夫”研究,也有部分稿件完成(参见潘光旦日记1947年8月10日条),可惜至今未能找到。
这些英文著述,可以使我们对潘光旦学术思想成长过程认识得更加准确和真切。如1923年潘光旦尚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上大学四年级时,即在美国的学术刊物《优生新闻》上发表了长文Eugen⁃icsandChina:APreliminarySur⁃veyoftheBackground,对中华民族的种族特征及其某些影响深远的社会制度与优生学的关系作了初步的考察,此文的部分内容后来被改写为中文论文《西化东渐及中国之优生问题》在国内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为此还引起了生物学者周建人的批评讨论。但需要提及的是,由于读者对象的不同,这两篇文章在论述角度、引证材料上都有很多差异,并不是直接的翻译。潘光旦在1923年11月份发表这篇文章时刚到美国学习1年零3个月时间,为时颇为短暂。这不仅说明他的英文造诣和西学知识根底相当扎实,能够迅速吸收课堂知识并利用科学文献从事研究工作,而且还说明他很可能出国留学前在清华学校对优生学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和思考,否则以短短的一年多时间的积累是很难写出如此成熟的文章的。1952年潘光旦在检讨文章中说美国老师一向很欣赏他的功课和英文写作,“先生宣读学生的短篇佳作,我的往往是第一篇,长的佳作还要替我向专门期刊介绍揭登。”1923年11月发表于《优生新闻》上的这篇长文,恐怕就是潘光旦此处未具体说明的“长的佳作”。又如一般认为潘光旦学术思想的精华是人文思想,较早且较完整的论述是1934年发表的论文《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和短评《迷信者不迷》,在1932年的《悼金井羊先生》一文中,潘光旦曾对与其交往密切的友人金井羊关于中国儒家人本主义思想的见解有所介绍,现在我们在潘光旦的英文著述里,却能够看到其人文思想形成的更多细节。1933年在评论母校达特茅斯学院教授哈维(Ed⁃winD.Harvey)关于中国人宗教信仰的社会学著作《中国心灵》(TheMindofChina)时,他认为作者过于注重神鬼崇拜之类的宗教实践,没有能够给予儒家人文思想以应有的地位。而在他看来,“儒家不是反宗教的,但其宗教不加掩饰地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确切地说是拟人的(anthropomorphic)和以人为中心的(anthropocentric)”,“神为人所造,是人造品,它们能够被塑造出来适应人的意图”。他又发挥了儒家“祭神如神在”的精神来阐释中国人对神的崇敬,但指出这种人文思想始终对神保持着清醒的敬而远之的态度,以免为其所役使。在神对人的祈求不能很好地回应时,神甚至有被义愤的民众砸毁的危险。简言之,这种态度意味着崇敬神、祈求神的人掌握着神的命运。这里,潘光旦对于美国学者中国宗教观的批评和对于儒家思想的阐释,已经相当明晰地呈现了1934年两篇论儒家人文思想文章的基本精神,以英文anthropo⁃morphic和anthropocentric两个词语概括儒家人文思想的特征,简洁而有力,令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胡适在1929年卷的《中国基督教年鉴》上发表了一篇英文文章《今日中国的文化冲突》(ConflictofCultures),在谈及对西方文化应充分接受时使用了两个词汇,whole-heartedly和wholesale,这两个词汇语意有所差别而胡适却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英文造诣深厚的潘光旦很敏感地抓住了胡适的这个语意混淆,在1930年2月写的一篇书评里不仅对两者加以区分,而且还提出另外两种态度:半心半意地接受全部的西方文明(be half-hearted inacceptance of the whol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以及一心一意地接受西方文明的某些部分(be whole-hearted in ac⁃cepting portio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或一心一意地、有选择地采纳(whole-hearted selective adop⁃tion)。潘光旦更为欣赏的是最后一种态度,即一心一意地、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胡适在1935年6月发表的《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里承认潘光旦的批评有道理,将“全盘西化”的提法改为“充分世界化”。英文《中国评论周报》面向的主要是海内外西方人,以及少数精通英文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更广大的中国读者圈里长期以来流传不广,因此少为人知。但胡适却是该刊的经常读者,潘光旦在一篇书评文章中仅仅用了一部分篇幅和他讨论问题,他也注意到了,而且读后印象非常深刻。潘光旦对胡适的批评讨论因《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的提及而广为传扬。两位知识精英以英文为工具,讨论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应采取的态度,留下了一段佳话。潘光旦的这篇书评就收录在这本潘光旦英文文集里,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了。
创刊于1928年5月的《中国评论周报》是潘光旦发表英文文章的主要园地。作为中国人主办的、在海外世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周刊,《中国评论周报》的主要编辑是清华出身的一批归国留学生,他们在文化观上采取了以西方标准评判中国、又以中国标准比较西方的双重文化比较态度。有学者指出:“他们同西化派的相同之处在于,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社会,中国文化的某些内核需要以西方文化补充、改造之,但他们反对文化采取移植性的形式,强调文化主要是创造、调适,而不是一味模仿。他们同东方文化派的共同点在于,强调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消化、吸收问题,重视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树立中国本位意识和主体意识的重要性。不过,他们不似东方文化派那样幻想用中国文化去拯救、拔超西方文化,而清晰地认识到中国文化在多元文化世界中处于文化混乱、文化失衡的不利状态。”(邓丽兰:《略论〈中国评论周报〉(TheChinaCritic)的文化价值取向——以胡适、赛珍珠、林语堂引发的中西文化论争为中心》)这个特点在潘光旦身上也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来了,他在许多篇英文书评中对西方学者的观点都是既有吸收又有批评,吸收也罢,批评也罢,都是为了在保持主体性的基础上从事中国文化的重建。以潘光旦为代表的这批中西兼长的学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一方面他们以自己的西学知识努力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另一方面他们以新的视角重新阐释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既促进中国文化自身的再生,又以英文介绍给西方世界。
潘光旦兼任《中国评论周报》编辑时期是他在学术上多线作战并斩获丰富的时期,同时他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交往、合作也颇为频密。潘光旦自由主义政治观念的形成与他受到朋友圈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后来他之所以能在抗战时期实际参与民主运动,也可以说是在这时就已经撒下种子了。但是综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潘光旦发表的所有中英文著述,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当时很少谈及政治,至多触及一些政治的边缘话题;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文化、社会、优生等问题的学术探讨上,在这些学术研究的字里行间洋溢着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在《中国评论周报》上,潘光旦发表文章体裁最多的是书评,占据了其英文著述的大半篇幅;这些介绍、评论英文著作的书评,都刊登在他本人所主持的“书评”栏目里。潘光旦的书评,往往如他的老朋友梁实秋所言,是在“评”之外还发表一点自己的心得,自成一篇独立文章,是“不仅是‘书评’的‘书评’”。因此,这些书评成为我们了解潘光旦阅读活动以及思想形成过程的极好途径。
总而言之,潘光旦英文文集对于我们全面深入理解潘光旦学术思想的历程,以及追寻《中国评论周报》周围那群以重建中国文化、沟通中西文化为使命的学者的精神世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尽管80多年前的英文表达习惯已经使今天的读者感到有些陌生了,但我们仍然可以穿过历史的云烟,去欣赏前辈学者那种词汇丰富、表达典雅精炼的英文,从而获得某种美的享受。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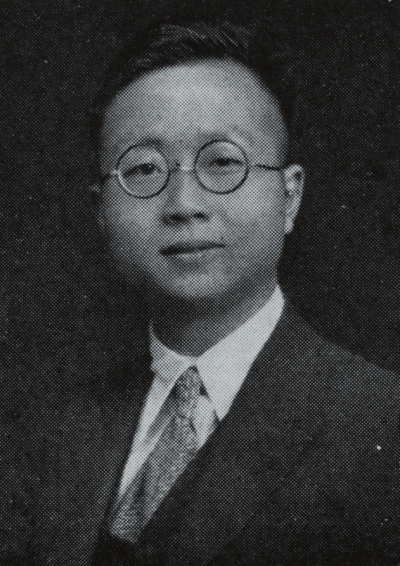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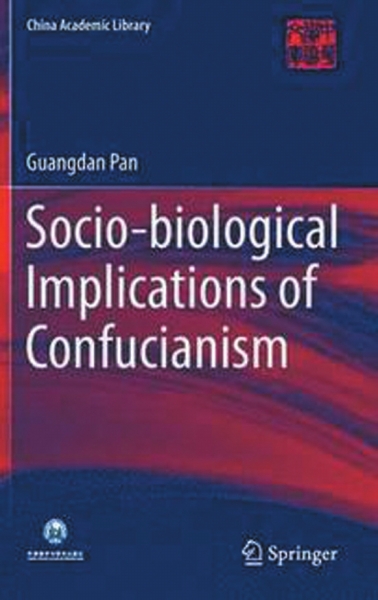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